摘要:案件社會結構理論能夠對認罪認罰案件的處理進行解釋。認罪認罰案件中被告人和被害人各自的社會符號以及雙方之間關系距離的遠近、辯護律師是否參與其中及其自身具備的特征、處理案件的主體等因素共同塑造著認罪認罰案件的社會結構。案件的社會結構通過不同場域共同作用于司法場域這一核心,對法律的選擇適用和運作過程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各類非法律因素以隱性的方式在認罪認罰案件的處理中發揮著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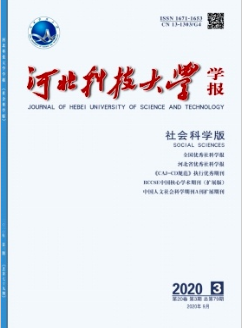
本文源自河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0(03):59-64.《河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季刊)創刊于2001年,是河北科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編輯出版的綜合性社會科學研究刊物。該刊是在我校主辦的《高等教育研究》辦刊20周年的基礎上,于2001年創刊,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季刊。
法律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與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單純依靠法律文本并不能直接解釋或者預示某一具體案件的實踐運作情況。換言之,“法律條文本身決定不了案件。每個案件都有其相應的社會特征,而正是這些特征決定了案件的處理”[1](P114)。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被告人自愿承認有罪并接受處罰的前提下,通過簡化或者省略部分訴訟程序,提升了案件的處理效率,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訴訟地位以及合法權益得到保障,案件的妥善處理惠及多方主體,對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具有積極意義。理論界和實務界從不同視角就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進行了諸多研究,但基本上都是對該制度本身展開的論述,尚未有從社會學角度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進行研究的成果出現。本文試運用美國布萊克教授的案件社會結構理論對認罪認罰案件進行綜合分析,以期揭示隱含的諸多社會因素在其中的影響力和作用方式,為實踐中更好地把握這些因素以及運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有所裨益。
一、案件社會結構的基本要素
作為純粹社會學的創始人,美國理論社會學家布萊克教授將社會學應用于法律領域,認為純粹法社會學的核心在于案件的幾何排列———案件的社會結構,也就是法律案件在社會空間中所處的位置和方向。他以社會學為切入點,對案件的社會結構進行分析,以“法律量”的概念來描述影響案件結構的各種因素。根據布萊克的界定,法律量是指施加于個人或者群體的政府權威的數量。[1](P6)法律量并不是恒定的,它隨著具體案件中誰控告誰、處理案件的法官是誰等因素而發生變化,并隨著這些人的等級、與社會生活的一體化程度、他們之間的親近程度、他們的習俗、組織成員資格等不同而變化。[2](P4)案件的社會結構對于案件具有預測作用,不管法律的條文和證據是什么,也不管論證的邏輯是如何陳述的,要想理解案件是如何處理的,必須研究案件的社會結構。[1](P104)案件的社會結構主要包括以下要素。
(一)糾紛雙方的主體角色及其關系
案件社會結構的第一個方面是誰控告誰,即糾紛雙方分別是誰,由于案件一旦發生糾紛雙方即為確定,因而主體角色是常量。糾紛雙方所處的社會階層和承擔的社會角色等都會對案件的社會結構產生一定的作用,因而是影響案件如何處理的重要因素。這些當事人的社會特征并不會自主地發揮作用,只有這些社會特征被案件的處理者所知道時,才會對法律處理的結果產生影響。[1](P69)有研究者通過對盜竊罪進行實證研究后得出結論:被告人的性別、年齡、籍貫、職業和學歷等社會結構因素對量刑的輕重確實產生了影響,而且有些影響還相當顯著。[3](P57)可見,糾紛雙方的社會特征對于預測案件如何處理具有重要意義,這包括定罪和量刑兩個方面。
在糾紛雙方的角色定位中,不僅要關注雙方各自的社會特征,還應當注意他們之間的親密程度,布萊克將這種親密程度稱之為“關系距離”,關系距離預示并說明了法律的量。總體上,人們之間的關系越緊密,介入他們之間事務的法律就越少。[1](P9)在其他條件不變時,沖突雙方的關系距離越近,一方訴諸法律解決糾紛的可能性越小,反之,關系距離越遠甚至達到了完全陌生的程度,一方求助于法律處理沖突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兩個其他方面相同的案件中,如果知道雙方之間的社會距離,就能夠預測哪一個會引起更多的法律量,即便對此不是完全確定,但預測結果的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法律的量與關系距離具有直接關系。[1](P10)在很多情況下的確如此,如在近親屬、朋友等熟人關系之間發生的盜竊、詐騙、故意傷害等案件,被害人很可能不會主動報案,即便案件進入訴訟程序,案件的處理方式和結果也很可能會不同于那些發生在陌生人之間的案件。在司法實踐中,法院鑒于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間存在近親屬關系,從而對被告人酌定從輕處罰的案例也屢見不鮮,這體現了糾紛雙方之間的關系距離對案件結果的影響。
(二)支持當事人的不同因素
案件社會結構的第二個方面是誰支配誰,即對立雙方的支持者分別有誰,這是一個變量。這種因素的影響力度取決于支持者參與的程度。[1](P10)律師作為一方的支持者,在案件處理過程中的作用顯著,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案件的社會結構,如果被告人聘請了辯護律師,而且該辯護律師的業務水平越高、有效參與訴訟程序的程度越高,那么辯護律師對案件的把握則越全面和越深入,就越有助于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除了律師參與之外,其他的主體參與因素也會對案件的社會結構產生影響,其中社會輿論就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有些案件由于受社會輿論的影響而在量刑上有所輕重。如引發廣泛關注的“于歡故意傷害案”就折射出社會輿論的力量,社會輿論在一定程度上以隱性的方式影響著司法機關對案件的處理,該案最終由一審判處無期徒刑改為二審判處有期徒刑五年。雖然刑事裁判不應受到社會輿論等非法律因素的左右,但不可否認,在信息化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案件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一些非法律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影響,這也進一步說明了法律與社會之間具有緊密的聯系,畢竟法律是處于社會之中的。
(三)處理案件的第三方效應
案件社會結構的第三個方面是第三方效應,“這是案件社會結構的另一個組成部分:盡管社會學的研究更多地關注對立的雙方,而不是第三者(或支持者),但是什么人處理案件也會影響到案件的處理方式”。[1](P12)某一案件具體由誰來處理是不確定的,因而這一因素也是變量。法官是最典型的第三方主體,在具體案件中作出獨立裁判,但法官自身也會具有一些社會特征。正如學者所指出的,如果把法官置于社會大系統的動態運行中考察,就會發現法官并不是純粹的法律意義上的裁判者,而實際上是一個復雜的角色叢。[4](P271)法官的這種角色叢涵蓋了諸多的影響因素,如法官的性別、性格、年齡、個人經歷、業務能力等,這些因素或多或少會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處理案件時的心證和判斷,從而對案件的社會結構和案件的處理結果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縱觀案件社會結構的三個方面,在常量(糾紛雙方是誰)確定的情況下,后面的兩個變量(支持者是誰和誰來處理案件)中任何一個變量發生變化,都可能影響到具體案件中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選擇,從而影響案件的處理結果。法律文本并不能直接表明案件是如何處理的,而案件的社會結構能夠幫助預測和解釋案件的處理,這體現了案件各方的社會特征、關系距離以及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
二、認罪認罰案件的社會結構分析
布萊克認為被告人的認罪是一種法律的自我實施,即一種自我定罪。“它是法律的增量———一種自我施加的嚴厲懲罰形式,補充和強化了其他方面的法律實施。特別是它使被告罪犯化,為其打上罪犯的烙印,使其喪失法律資格,它也加速案件的處理并結案。”[5](P68)他還進一步指出,如果法律的自我實施(即被告人的認罪)與一般的法律運作行為遵循相同原則的話,那么認罪就會反映出案件的社會結構。在認罪認罰案件中,案件的社會結構可以揭示為何能對被告人進行從寬處理以及如何進行從寬處理。
(一)認罪認罰案件中的當事人因素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73條第2款規定,在審查起訴階段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檢察院應當聽取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有關意見,并記錄在案。《刑事訴訟法》第223條規定的不適用速裁程序的情形,其中一項是被告人與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沒有就附帶民事訴訟賠償等事項達成調解或者和解協議。《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但沒有退贓退賠、賠償損失,未能與被害方達成調解或者和解協議的,從寬時應當予以酌減。可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獲得從寬處罰和從寬處罰的幅度,與其認罪、認罰、悔罪的表現以及被害人所持態度具有很強的關聯性。由于糾紛雙方之間的親密程度會影響案件的社會結構,對于自愿認罪認罰的被告人往往會通過提升與被害人一方的親密程度來獲得利于己方的處理。被告人為了獲得從寬處理,愿意悔罪、認罪、認罰,通過關注被害人的社會角色特征、積極賠償被害人和取得被害人的諒解,以拉近雙方之間的關系距離,進而獲得從寬處罰的機會,這就在無形之中改變了認罪認罰案件的社會結構。
布萊克認為,當被告人可以預測到法律對其會更嚴厲時,如侵犯的是社會地位較高者或是陌生人,被告人更經常認罪;而當被告人可以預測法律對其會更為寬大時,如侵犯的是社會地位較低者或是親密者,被告人更經常不認罪,所以,對抗性也會發生變化,它隨著法律和其他社會控制形式的減少而增加,反之亦然。[5](P72)對于美國的社會階層狀況和刑事司法實踐而言,布萊克的這一論斷也許是可以成立的,但對于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來說卻并非如此。認罪認罰的被告人能夠認識到自愿認罪認罰可以獲得從寬處罰,基于可以獲得法律對其從寬處罰的預測,被告人會主動選擇認罪認罰,而非更不認罪。
看待當事人具有的社會符號和衡量當事人的社會地位具有不同的維度,如接受教育的程度、擁有財富的多少、受社會尊重的程度、所從事的職業等都是影響這些的因素。從案件的社會結構角度來看,當事人因素與案件能否得以從寬處理具有一定的聯系。在引發廣泛熱議的“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中,關于余金平的身份成為該案的爭議點之一。一審法院認為,余金平作為一名紀檢干部本應嚴格要求自己,其明知酒后不能駕車,但仍酒后駕車,且在發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判處緩刑不足以懲戒犯罪,對公訴機關建議判處緩刑的量刑建議不予采納。二審法院合議庭經評議認為,余金平的紀檢干部身份與其交通肇事犯罪行為本身確實不存在因果關系,但該特殊身份卻系評估應否對其適用緩刑的重要考量因素,余金平作為紀檢工作人員本應比普通公民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更加模范遵守法律法規,將余金平系紀檢干部作為對其不適用緩刑的理由之一并無不當。1從該案中法官的態度可以明顯看出,被告人的社會身份對法官判案的確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二)認罪認罰案件中的律師
案件的社會結構不僅受被告人和被害人各自的社會符號以及雙方之間關系距離遠近的影響,還與是否有律師等支持者的參與相關。“與控辯雙方的社會特征一樣,律師、證人、公開其偏向立場的感興趣的旁觀者等支持者及其社會特征具有同樣的影響模式。”[1](P10)被告人是否聘請律師以及律師的業務水平高低、律師自身具備的特征等都能夠對案件的處理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案件的社會結構還可以指引律師如何去挑選案件以及預測案件的處理。在認罪認罰案件中,律師作為被告人的支持者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刑事訴訟法》第174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同意量刑建議和程序適用的,應當在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在場的情況下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在司法實踐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非完全了解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于疑罪從無和無罪推定等原則也不熟知,對檢察官掌握的證據情況不甚了解,因而無法基于對證據的全面認知慎重作出是否認罪認罰的決定。相比之下,在那些聘請律師的認罪認罰案件中,律師會綜合全案情況對案件事實和證據進行全面分析,從而選擇最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策略與檢察官進行量刑協商,為其爭取從寬的量刑建議。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36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法律援助機構沒有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的,由值班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程序選擇建議、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對案件處理提出意見等法律幫助。《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還指出,值班律師可以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值班律師可以查閱案卷材料、了解案情等。但從司法實踐來看,認罪認罰案件中的律師辯護與值班律師幫助存在顯著不同,尤其是值班律師不具有辯護人身份而無法充分發揮其作用,對于案件的精力投入遠不及辯護律師。換言之,辯護律師與值班律師在案件中的參與程度不同,這也導致不同的認罪認罰案件中社會結構的不同。
律師對認罪認罰案件的社會結構的影響還可能體現在另一方面,如對立雙方的律師之間可能認識,基于先前的這種認識關系,通過縮小陌生人以及其他社會上敵對的人之間的社會距離,進而增加了對立雙方進行談判與和解的可能性。[1](P11)在同一地域內,不僅律師之間可能存在一定的交集,律師與檢察官、法官之間也可能屢有接觸。2這就為被告人與被害人之間的賠償、和解、諒解以及認罪認罰量刑建議、具結書的簽署等提供了有利條件,拉近了不同主體之間的關系距離,從而影響著認罪認罰案件的社會結構。布萊克認為一個對社會學知識一無所知的律師是沒有競爭力的。如果律師僅僅局限在法律文本層面分析案件,忽略與之緊密相關的各種社會因素的作用,那么很難預測案件是如何處理的。所以,律師通過試圖調整案件的社會結構,使得案件的走向盡可能有利于所代理的當事人,此般操作甚至能夠影響司法裁判者對案件事實的認定以及法律規范的具體適用。“作為場域職業行動者的律師通過其自身所擁有的各種不同形態的資本,與場域其他資本進行爭奪、交換、置換等,分割、蠶食、爭奪案件事實的確認與法律規范的適用方面的話語權,進而影響案件的最終裁決結果,以有利于自己及其所辯護或代理的一方當事人,就必然成了律師的一種具有職業特點的行為。”[4](P278)在有律師參與的認罪認罰案件中,律師會綜合運用各種資源與檢察官就量刑問題進行協商,通過影響案件的社會結構以最大限度地為當事人爭取從寬處罰。
在認罪認罰案件中,除了律師作為支持者參與之外,被告人的近親屬也對案件的社會結構具有影響,這主要體現在當被告人無力賠償被害人時,被告人的近親屬代其賠償以獲得被害人的諒解,這也拉近了當事人之間的關系距離,增加了和解、諒解的可能性。
(三)認罪認罰案件中的檢察官和法官
檢察官代表國家進行公訴,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其背后有強大的國家力量作為支撐,這是刑事案件能夠得到順利處理的有力保障。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檢察官的作用得到進一步凸顯,甚至發揮著主導作用,其重要話語權體現為提出對被追訴人從寬處理的量刑建議。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01條的規定,法院作出判決時,一般應當采納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由此可見,檢察院的量刑建議被采納是常態,具有良好的可預期性。被追訴人選擇自愿認罪認罰,積極與檢察官就量刑問題進行協商,較之不認罪認罰的案件縮短了檢察官的辦案期限,降低了刑事證明的難度,也節省了大量的司法成本,這就使得被追訴人與控訴機關的關系由“對抗”轉向了“合作”,這種關系變化在無形之中拉近了雙方之間的關系距離,也影響著認罪認罰案件的社會結構。
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對法官也有積極影響,一方面,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緩解了法官的辦案壓力,提升了案件的處理效率,使法官從原本耗時費力的舉證、質證環節中解脫出來,因而能夠獲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帶來的效率價值;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能夠避免法官辦錯案,因為一旦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法官在庭審環節就將原來審查案件事實的重點轉化為審査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具結書內容的真實性、合法性。從這個角度來看,法官處理認罪認罰的案件相對容易,更愿選擇那些對被告人有利的法律規范,原則上會接受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對被告人進行從寬處罰。此外,在認罪認罰案件中,法官的個人經歷、業務水平、價值觀念等都會潛移默化地對案件的社會結構產生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對案件的處理。畢竟“法官就特定案件在案件事實的認定和法律規范的選擇方面所做出的裁判結果,實際上是多重角色規范較量、博弈的結果”,“法官非司法者的一些角色因素自然就會摻和到司法者的角色因素當中,并在司法者角色的基礎上,以一個綜合性的角色進入司法場域”[4](P272)。法官并不是在枉法裁判,而是案件的處理常常受到法律外因素的影響,法官的判決是社會結構的產物。[6](P82)
三、認罪認罰案件社會結構的作用場域
法院是處理案件的最后一道關口,每一個認罪認罰案件的社會結構歸根到底是通過對司法裁判權的影響來發揮作用。認罪認罰的被告人能否獲得從寬處罰以及從寬處罰的幅度,最終要經過法官裁判才能確定。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中的場域概念是指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構型,“根據場域概念進行思考就是從關系的角度進行思考”[7](P133-134)。司法場域是其中的一個子場域,與社會其他場域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聯關系,“刑法運作的司法場域是在與權力和社會的關聯中建構起來的”[8](P177-180)。案件的社會結構是具體案件處理過程中所涉及的不同訴訟主體的社會關系狀況。[9](P114)這些社會關系狀況最終通過進入司法場域來實現影響裁判的目的,可以說,司法場域是認罪認罰案件的社會結構發揮作用的空間。法官在司法場域中的裁判行為并非單純依照法律文本進行,還涉及裁判規范的選擇和對案件事實的認定,這個過程中摻雜著諸多非法律因素對司法場域的干預。“實際上,將某一個法律規則適用于一個特定的案件是一些相互沖突的權利之間的相遇,法官必須在這些權利之間進行選擇。”[10](P512)
案件的社會結構能夠解釋案件是如何處理的,也能夠說明不同案件甚至在某些案情和證據都較為相似的案件中,為何處理結果仍然會存在不同,案件社會結構的這種功能是法律文本無法具備的。案件的社會結構因素的變化能夠解釋法律領域中的各種差別,法律條文本身并不能對這些差別進行解釋。[1](P28)每個案件的案件結構變量不同,由此形成的裁判規范不可能一樣。[4](P85-86)在認罪認罰案件中,由于被告人與被害人各自的社會符號以及他們之間關系距離的遠近、是否有辯護律師參與其中以及自身具備的特征、處理案件的法官和檢察官等因素,都會導致裁判規范的不同和案件社會結構的差異。當法律條文被應用于具體案件時,法律的樣態會呈現出動態化,而且會受諸多法外因素的影響。但是,由于有罪刑法定原則的約束,決定了這些因素的影響是有限的,即便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對其從寬處罰的幅度也會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
需要指出的是,布萊克提出的影響案件社會結構的諸多因素及其程度并非可以完全與中國的實踐情況相匹配,尤其是社會異質性特征。即便如此,在研究認罪認罰案件時,案件的社會結構理論依然提供了社會學的研究視角,這對理解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具體實踐具有一定的意義。正如有研究者認為的,從社會結構異質性影響案件結果的差異程度方面來說,雖然中國的法官裁判沒有美國那樣存在明顯差異,但當事人社會結構導致的訴訟力量強弱對裁判產生影響是可見的。[6](P85)面對并重視這種案件的社會結構,對案件社會結構的幾個方面的相互關系及其影響力進行有效分析,可以達到對案件預測和理解之目的。[11](P62)尤其對于被告人而言,可以通過自愿認罪認罰、積極賠償被害人、委托辯護人等方式,對認罪認罰案件的社會結構產生一定的影響,盡量創造獲得從寬處罰的有利條件。
四、結語
案件的社會結構可以預測和解釋案件的處理,單純依靠法律文本解釋不了案件是如何處理的,通過研究案件的社會結構可以分析法律的運作行為。每個案件都是社會地位和關系的復雜結構,這一結構對于理解在法律技術特征上彼此相同的案件的法律變異是關鍵的。[1](P6)認罪認罰案件中被告人和被害人各自的社會符號是確定的,被告人通過自愿認罪認罰,積極賠償被害人取得其諒解,接受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并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這便拉近了與被害人、檢察官之間的關系距離。辯護律師或值班律師的參與是支持被告人的力量,處理案件的法官也從繁瑣的訴訟程序中有所解脫,這些因素共同塑造著認罪認罰案件的社會結構,從而基本上能夠預見被告人會獲得從寬處罰。在具體實踐中,認罪認罰案件的社會結構通過不同場域共同作用于司法場域這一核心,對法律的選擇適用和運作過程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不容忽視與案件緊密相關的各類非法律因素,它們以一種非顯性的方式在案件的處理中發揮作用。
參考文獻:
[1][美]唐納德·布萊克.社會學視野中的司法(中英文對照)[M].郭星華,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美]唐納德·布萊克.法律的運作行為[M].唐越,蘇力,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
[3]胡昌明.社會結構因素對量刑影響的實證分析——以盜竊罪為例的案件社會學研究[J].法律適用,2011,(3).
[4]張心向.在遵從與超越之間——社會學視域下刑法裁判規范實踐建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5][美]唐納德·布萊克.正義的純粹社會學[M].徐昕,田璐,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6]吳英姿.法官角色與司法行為[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
[7][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M].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8]張心向.在規范與事實之間——社會學視域下的刑法運作實踐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9]姚小林.司法社會學引論[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4.
[10][法]皮埃爾·布迪厄.法律的力量——邁向司法場域的社會學[J].強世功,譯.北大法律評論,1999,(2).
[11]李瑜青,等.法律社會學經典論著評述[M].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6.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