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云南邊境是我國拐賣人口犯罪頻發地區。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經濟發展、婚嫁習俗等帶來的高利益驅動,使得該地出現了強大的人口販賣市場。對該地區拐賣人口犯罪的控制,應當從解剖該地的人口拐賣犯罪特征展開,結合跨國拐賣人口犯罪的國際視野,從前期、中期、后期三個階段,按照“防范—打擊—救助”的遞進邏輯進行犯罪控制,從不同層次、不同角度積極開展防拐、反拐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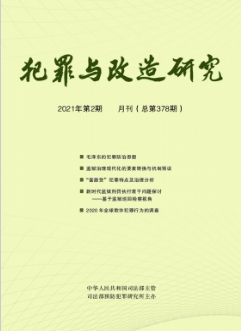
本文源自陳瑤, 犯罪與改造研究 發表時間:2021-06-29
關鍵詞:人口 販運 犯罪 控制
一、云南邊境拐賣人口犯罪現狀
拐賣人口犯罪作為一種社會巨蠹,我國對其一貫十分重視且嚴厲打擊。新中國成立后,經過十幾年的積極治理,拐賣人口犯罪似乎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隨后,經歷了改革開放,社會經濟發展,案件偵辦能力提升,數據顯示,拐賣人口犯罪又卷土重來,發案率呈上升趨勢,犯罪分子一度十分猖獗。
自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伴隨著聲勢浩大的“嚴打”刑事政策,拐賣人口犯罪活動應聲收斂,發案率逐步回落。到 20 世紀 90 年代,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社會生活貧富差距的拉大,使得拐賣人口犯罪發案率迅速回升,且由于這一階段的拐賣人口犯罪開始呈現新形式新特點,案件偵破難度高,拐賣案件黑數較大。從近幾年的情況看,拐賣婦女兒童發案基數不低,犯罪惡性和影響范圍呈現擴張趨勢,全國反拐、打拐形勢依然不容樂觀。特別是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人員流動較為頻繁,給跨國拐賣人口犯罪打通了門戶,該類案件也逐步從幕后現身臺前。
我國云南邊境一線正位于大湄公河次流域之內,全省共有 8 個邊境州市的 25 個邊境縣 ( 市 ),緬甸、老撾、越南均有省 ( 邦 )、縣 ( 市、鎮 ) 與其接壤。云南省作為邊疆大省,是我國向西南開放的主要橋頭堡。聯通多國的突出地理位置,使得這一區域成為研究國內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尤其是研究跨國拐賣人口犯罪的前沿陣地。中國境內婦女通過這條隱性的“中轉站”被拐去周邊鄰國,東南亞婦女也經由這條“黑色通道”進入中國,并轉至香港、澳門等。與東南亞多國接壤的天然地理屬性使得云南邊境的拐賣婦女兒童案件高發,已然成為我國打擊跨國販賣人口犯罪的重中之重。
近年來,公安部高度重視跨國拐賣人口犯罪案件,己經先后在云南省建立了多個打擊跨國拐賣執法合作聯絡辦公室,云南省各地也開展了一系列集中打拐行動,全省打擊拐賣人口犯罪工作成績領軍全國。然而,由于拐賣人口犯罪本身的復雜性,加上不同國家地區之間反拐機制的迥然,以及近年來該犯罪行為的異化和系統性升級,使得對拐賣人口的犯罪控制難度進一步加大。
二、云南邊境拐賣人口犯罪特征
通過對大湄公河次區域云南邊境拐賣人口犯罪情況的收集整理和數據資料分析,筆者發現該區域跨國拐賣人口犯罪有以下顯著特點 :
(一)犯罪流向——星狀發散型
拐賣人口犯罪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大多數販運活動的地理范圍是有限的,往往是在某一固定的大地理區域中形成較為規律的犯罪流動。從總體犯罪流向上來看,在云南邊境一線,對于本國人口的拐入大于拐出。也就是說在我國云南邊境一帶,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大多來自于周邊的其他國家,如緬甸、老撾、越南,中國則是作為被拐賣人口的接收國而存在的。若以中國作為研究該區域跨國拐賣人口犯罪的中心點來看的話,可以發現該區的犯罪流向大致呈現出一種以中國云南省為中心,以緬甸、越南、泰國、柬埔寨、老撾等五國為不規則外環的星狀發散性特征。
再進一步將該區域的拐賣人口流向從細劃分,可以看出泰國既是販運人口來源地國又是目的地國,甚至成為這一星狀人口拐賣帶中最大的拐賣人口集散地。被拐人口會從這里被運往馬來西亞、巴林、新加坡、澳大利亞甚至俄羅斯、土耳其等國。而在此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國家,如柬埔寨、緬甸、越南、老撾則主要是被拐人口的來源國。云南邊境一線的被拐受害者多是來源于這幾個國家。雖然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越南均是云南邊境一帶的人口拐出國,但拐出人口的量級分布明顯不均。數據顯示滇西中緬邊境地區拐賣犯罪最為嚴重,僅在 2007 年至 2012 年間,云南立案的 395 起跨國拐賣案件中,334 起均為涉及中緬的拐賣案件。除了是周圍國家拐賣人口的主要流入地,云南也是相當一部分國內拐賣人口的流出地。近些年,除了單向的人口拐賣,更是開始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即拐賣人口互流。泰國、越南、柬捕寨、中國等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跨國拐賣人口互流,甚至有數據表明在大湄公河次區域云南邊境一線有超過 85% 的受害者被在不同國家間來回販運。
(二)犯罪主體——復雜性
首先,拐賣人口犯罪很少是單獨作案,犯罪分子往往是鏈式作業團隊。拐賣人口犯罪團伙在組織體系、人員分工上有著程序建構,其作案能力和危害程度相較于個體作案的人販強出很多。最高法發布的關于拐賣兒童犯罪案件的典型案例中,2012 年的“李某英拐賣兒童案”和 2015 年的“孫某山拐賣兒童案”,均是團伙作案,涉案人員四散分布但又聯系緊密,相互依存,從信息源到購買鏈信息共享,人口買賣“供需”網不斷擴大,買賣雙方“交易”成功率一路攀升,在短時間內即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拐賣犯罪生態,導致買賣地拐賣兒童案件高發,社會危害性極大。
其次,云南邊境的拐賣人口犯罪多為境內外相互勾結實施活動,其國際化趨勢更加凸顯。據云南省德宏州芒市公安機關 2001 年至 2015 年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在其破獲的 39 起跨國拐賣婦女兒童案件中,85% 都是境內外人員勾結作案。2002 年的公安部“木棉花”打擊拐賣越南婦女專項行動、2011 年的安哥拉特大跨國拐騙中國婦女賣淫案、 2015 年的“8·17”特大拐賣緬籍婦女案中,境內外犯罪分子的勾結串通尤為明顯,公安部都是通過雙邊打拐合作機制,聯合各地警力追捕犯罪嫌疑人,才將這批跨國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集團搗毀。
再次,少數民族犯罪分子在該地的占比尤為突出。從地理位置上看,云南邊境一線國家大都是多民族混合雜居,當地人口中少數民族人口比重較其他地區要大。而且一些少數民族是邊境線兩邊所共有的少數民族,雖然國籍有所不同,但是卻有著共同的民族語言、風俗習慣和人文環境。比如中越邊境拐賣婦女兒童案件數量的居高不下,一個主要原因就在于兩地有著同樣的民族即苗族、哈尼族,兩地的人口互流很少有文化和生活上的差異。少數民族犯罪分子通曉當地語言文化、大大提高了作案的成功率。
最后,女性犯罪分子不斷增加。據 2018 年全球人口販運報告顯示:東亞及太平洋地區的國家連續報道大量女性罪犯的情況,雖然女性罪犯的比例似乎略有下降,但它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比例之一。在云南地區的跨國拐賣婦女案件中,這些婦女多為本地居民,熟悉邊境情況,或者自身就是從拐賣的受害者轉為加害者,她們進行拐賣人口容易使犯罪對象產生信任心理和精神依賴。
(三)犯罪對象——針對婦女兒童
在 2019 年發布的全球人口販運報告書中,詳細說明了全球人口販運的犯罪對象分布。數據顯示,在 2019 年被發現的人口拐賣受害者中,成年女性占比近一半,婦女和女童總占比甚至超過 70%。這種現象不是某一年所獨有的,而是長期以來人口販運的顯著特點,即全世界發現的人口販運受害者大多數都是女性,人口販子的目標主要是成年女性和女童。這種特點在云南邊境也得到了突出體現。云南省公安刑偵部門、云南公安局域網業務信息系統統計的 2005 年 -2015 年拐賣婦女和兒童犯罪立案占比中,63% 為拐賣婦女犯罪,37% 為拐賣兒童犯罪。
(四)剝削類型——性剝削為主,多種剝削形式并存
拐賣人口犯罪的剝削類型大致可以分為性剝削、強迫勞動、乞討、摘取器官或其他方式。從 2019 年發布的全球人口販運報告中可以看出,全球發現的人口拐賣犯罪受害者 83% 都是被販運從事性服務。近些年來拐賣人口犯罪目的更加復雜化,性剝削以外的剝削占比逐年提高。2007 年發生在山西運城、晉城、榆次、晉中、臨汾等地多個縣市的震驚全國的一大批“黑磚窯”案件就是其中的典型。犯罪分子不滿足于利用被拐賣婦女兒童進行性交易這一單一目的,而是變本加厲地將被害人視為“工具”,強迫勞動,組織殘疾人、兒童乞討、進行器官交易等,無所不用其極地從被害人身上榨取經濟利益。
在云南邊境,強迫勞動、組織殘疾人、兒童乞討、進行器官交易仍然是相對少見的類型,性剝削是最主要的剝削類型。但是相對于原來被販賣婦女被賣為人妻的傳統形式,如今收買婦女兒童的犯罪目的和性質更加惡劣。強迫、組織、容留婦女賣淫的犯罪分子與人口販子們相互勾結,將被拐的女性、兒童分門別類,賣給桑拿房、洗浴中心、賓館酒店、 KTV 等進行非法勾當的娛樂場所,逐步發展成“拐騙—賣出—買人—賣淫”的流水線作業的犯罪模式。
三、云南邊境跨國拐賣人口犯罪成因分析
(一)地區經濟發展差異
經濟發展對于人口拐賣犯罪來說是十分重要的誘因,由于云南邊境的部分鄰國經濟發展水平十分不平衡。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早在 2017 年,中國人均 GDP 已遠超泰國、越南、柬埔寨、老撾、緬甸等周邊鄰國。而云南省經過多年的經濟發展,其交通條件相比過去來說己經大為改善,連接東南亞各國的陸路、水路、航空、能源、信息等“能源大通道”已初具規模,因此對于周邊國家來說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在本國就業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為了改善生活狀況,與云南省接壤的這些國家的婦女紛紛選擇在中國結婚或在中國尋找就業機會。在這個過程中,女性最容易被拐賣。經濟的落后、貧窮,使邊境地區的人口流動愈加泛濫,許多人迫切希望找到一份能掙更多錢的工作,或者希望嫁到經濟較為富裕地區擺脫貧窮。這樣的生活需求給了拐賣人口犯罪分子可乘之機,這也是中國云南成為拐賣人口犯罪的買入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巨大的買方市場
首先,“性產業”培育了國際拐賣婦女的買方市場。主動從事色情業的人員相對較少,而繁榮的色情業又需要更多的女性,供需的矛盾使得買方需要從鄰近的地區尋找人員填補空缺。在云南邊境,由于色情行業的暗流涌動,就會出現大量組織和容留外國婦女從事色情服務的需求。正是這種情況的存在,色情服務者供不應求,以性剝削為目的的人口拐賣案件迅速增多,女孩們被賣到泰國等東南亞國家成為雛妓變成了一種常態。
其次,婚嫁習俗刺激了買方市場。在云南邊境許多經濟落后的國家、地區,達到婚育年齡的男青年無妻可娶的情況較為普遍,“買一個老婆”成為最高效快捷的辦法。性別比失衡問題在一定歷史環境內長期存在,拐賣人口犯罪也隨之暗流涌動,婚姻交易的需求刺激了人口交易市場的存在。
最后,豐厚獲利推動了買方市場擴張。拐賣人口犯罪一直是“無本萬利”的黑色行當,無需付出體力、腦力勞動,行為人就可以獲得高額回報,利欲熏心讓越來越多人鋌而走險,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各類主體的不同需求,各方利益的追逐,人口買方市場愈加膨脹,求大于供的現實催生更多的犯罪分子,也致使越來越多人成為人口販賣的受害者。
(三)法律的缺陷與矛盾
關于人口拐賣法律規定之間的矛盾,在云南邊境各國關于拐賣人口犯罪的犯罪控制上面,體現得尤為突出。在中國現行的法律體系下,打擊跨國拐賣人口犯罪的內容在各個部門法中都有所規定,但相關規定之間并不協調,且這些法律與中國加入的相關國際公約也無法融合。例如,拐賣的對象是否應局限于婦女兒童?近年來拐賣成年男性進行勞動力剝削的案件也在增多,2007 年發生在山西的系列“黑磚窯案件”就給了我們警示和思考。成年男性、雙性人、變性人等不管是從法理上還是實際工作需要,都應該被納入我國拐賣人口犯罪所侵害的對象。當然,不僅本國公民是被拐賣對象,外國公民也成為拐賣人口犯罪的侵害目標,對他們應該如何去保護?還有,行為人出賣親生子女的,是否需要在定罪量刑時區分情況做不同處理,在量刑上予以考量,這些都是亟待在立法上給出回答的問題。
四、跨國拐賣人口犯罪的管控對策
(一)完善控制跨國拐賣人口犯罪的法律體系
截至 2017 年,全球已有 60 多個國家和地區通過了以反人口拐賣為主要目的的法律,湄公河次區域的泰國、緬甸、柬埔寨三個國家制定了專門的反拐賣人口法。所以,《反跨國拐賣人口法》的制定就十分具有現實意義。統一的法律不僅可以協調現有的、較為分散的關于打擊跨國人口販賣的法律規定,修正已加入的反跨國人口販運的國際公約不一致之處,還能將已形成的反跨國人口販運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機制法律化,對未來的跨國拐賣人口犯罪控制具有深遠意義。
(二)強化打擊跨國拐賣人口犯罪工作機制
1. 修補“破窗”——提升反拐意識。1980 年代后期至 1990 年代,云南省廣南縣農村曾經形成了一個舉世聞名的“拐親賣親”村。村民受制于當地環境而謀生困難,便走進了生孩子—賣孩子—生孩子的怪圈。這就反映出意識一旦發生畸變,犯罪就有了賴以滋生的肥沃土壤。試想如果第一個“生娃賣”的犯罪分子就得到了懲治,如果對村民們的思想及時地進行了糾正,就相當于把破掉的那扇“窗子”修好,后續的惡性循環也很難會發生。提高反拐意識,就是修補拐賣人口犯罪這扇“破窗”的一個必要手段。在拐入區開展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教育,轉變買入群體陳舊觀念,在拐出區普及反對拐賣人口犯罪法律知識,提高潛在被害人群的辨別和防范意識,增強他們的自我保護能力。
2. 源頭管控——強化邊境管理。地理位置作為既定事實無法改變就要管理好邊境人口非法流動。我國西南地區非法移民,必須要從源頭上著手,嚴查邊境口岸,嚴控非法便道。針對這個問題,公安機關要在日常工作中及時更新、跟進本地新增人口與失蹤人口,牢牢掌握轄區流動人口情況,做到“鄉不漏村、村不漏戶、戶不漏人”。同時毫不放松重點人口管理和流動人口管理等基礎性工作,將涉外情報據點建設工作下沉至各個地區。對“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通婚”的三非群體嚴格清理整治,有計劃地開展邊境管理工作。
3. 建立打擊拐賣人口犯罪數據庫。鑒于打擊跨國拐賣人口犯罪的聯動性,和目前網絡偵查工作的有效性,拐賣人口犯罪數據的信息收集共享對于打擊云南邊境一線拐賣人口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2009 年 4 月 9 日,我國已建成全世界首個“打拐 DNA 信息庫”,利用信息技術和科技成果推進打拐、反拐工作。此后,這項工程還需要不斷深入推進,并逐步在次區域,特別是邊境重點地區(縣、市)設立打拐信息數據分支機構 , 形成統一的反拐情報組織體系。
4. 打防結合,多方聯動。拐賣人口犯罪應當堅持“打防結合,多方聯動”,有關部門積極配合,進行綜合治理。公安、民政、計生等部門嚴格責任,踐行暫住人口、流動人口登記、婚姻登記、收養登記等各項制度規定,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組織要發揮積極宣傳教育工作,將防范、打擊、管理、教育措施一體推進,堵塞漏洞,不留死角,嚴防死守戶口管理工作。
另外,社會控制的有效運作還要依靠非政府組織的支持。控制跨國拐賣人口犯罪中,非政府組織在向受害人提供協助、進行普法宣傳教育、提供搜救線索信息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國內“寶貝回家”等網絡平臺參與反拐工作的成效有目共睹。民間尋親團體和義工的努力為反拐、打拐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助力。在大湄公河次區域云南邊境司法資源相對緊缺、跨國犯罪日益猖獗的情況下,加強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拓展民間渠道、實現警民聯合是勢在必行的。
同時還要注意運用多種手段,提高打擊拐賣人口犯罪工作的有效性。2000 年,公安部根據當時的拐賣人口犯罪情況,開展了“網上打拐”行動,把人販子和被拐賣婦女兒童的信息錄入網上查詢系統,使各地公安機關可以實現信息共享。公安部還推出了“拐賣兒童案件偵辦責任制”“兒童失蹤快速查找機制”“來歷不明兒童摸排機制”“一長三包制”等針對性強的有力舉措和工作機制。云南省也根據當地情況建立了反對拐賣婦女兒童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協調督辦各地、各部門反拐工作。這種利用信息網絡等前沿手段,結合拐賣犯罪的具體特點和實際規律,明確重點、落實責任的打擊手段,都是我們將來建成高效、快速、準確“打拐”機制的工作方向。
5. 完善拐賣人口犯罪受害者的事后救濟。販賣人口的社會危害性大,花樣不斷翻新,又難以在短時間徹底根除,所以對拐賣人口犯罪受害人更需要有合理的安頓措施。根據拐賣人口犯罪的犯罪特征,結合以往各國的實踐 , 拐賣人口犯罪的受害者往往也會被視為犯罪者或是偷運的移民 , 受到拐入地的法律制裁,這對于他們來說,無疑是二次傷害。因此,健全完善拐賣人口犯罪受害者的救助機制,為被解救的被害者提供必要專業心理輔導、職業規劃,為生計困難的被害者提供生活幫扶和就業安置,使受害者及時消除心理陰影,獲得身心康復 , 引導其重返社會,從犯罪控制的角度而言 , 也是促進其與執法機構順利配合,能夠有效避免人口犯罪的受害者再次被拐或轉為犯罪的加害者。
(三)開展國際刑事司法合作
經濟全球化和世界一體化進程下,開展地域合作成了控制跨國犯罪包括跨國拐賣人口犯罪的必由之路。近年來,在公安部和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的直接指導下,云南省已經建立起了打擊跨國拐賣人口犯罪的執法合作聯絡站,組織中越兩國公安機關開展定期或不定期的邊境聯合考察,通過聯合辦案,拓展偵查人員的工作思路,提高打拐工作效能。除此之外,警務合作綠色通道和國際反拐基金組織的建立,情報信息交流共享工作的開展,經常性對話制度的保持、聯合專項行動的不斷推進也是打擊邊境拐賣人口犯罪的應有之義。開展國際刑事司法合作,不僅在調動國際資源,采取全面的戰略決策來解決跨國拐賣人口犯罪問題上,而且對于我國與西南邊境各鄰國在處理跨國拐賣人口犯罪時所涉及的實際操作上都有很大裨益。
拐賣人口犯罪不僅是在我國以及云南邊境一帶的發展中國家,而且在全球范圍內很多國家犯罪態勢也很嚴峻。在這種形勢下,我國對拐賣人口犯罪的打擊不容松懈,只有從立法、司法、執法等方面通力合作、綜合施策,才能有效減少犯罪,提高對拐賣人口犯罪的管控效能。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