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美術(shù)是中國文化的母體藝術(shù), 是民族精神凝聚力和親和力的載體, 民間美術(shù)的民族性與世界性并不是一個新的問題, 但其對于我們發(fā)展自己的民族性藝術(shù)有一定的指導意義。關(guān)于兩者的界定也是相對的, 兩者相互交流、相互影響, 應該是辯證統(tǒng)一的關(guān)系, 從民間美術(shù)的民族性中挖掘藝術(shù)的世界性, 也從藝術(shù)的世界性中尋求民間美術(shù)的民族性, 最終形成民間美術(shù)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相互促進、相互發(fā)展的關(guān)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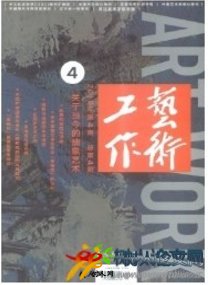
《美苑》已改名《藝術(shù)工作》(雙月刊)創(chuàng)刊于1980年,由魯迅美術(shù)學院主辦。堅持獨立的學術(shù)品格與藝術(shù)標準,設(shè)立專稿、創(chuàng)作評介、藝術(shù)史研究、教學研究、設(shè)計平臺、外國美術(shù)等欄目,在深入思考藝術(shù)創(chuàng)作與理論問題的同時,及時報導當代美術(shù)活動、發(fā)布最新美術(shù)作品、介紹國外美術(shù)信息,努力推動藝術(shù)創(chuàng)作與理論的建設(shè)與發(fā)展。
常常聽到這樣一種評論, 我們的現(xiàn)代民間美術(shù)是“屬于東方的、中國的、現(xiàn)代的”, 認為藝術(shù)“越具有民族性, 就越具有世界性”。這種評論是公允的, 無可非議的。但與此同時, 我們也應注意到這樣一種現(xiàn)象:越來越多的民間藝術(shù)品———尤其是現(xiàn)代民間繪畫———在技法上互相借鑒。除去作品賴以產(chǎn)生的生活內(nèi)涵之外, 在形式上往往出現(xiàn)某些共同的東西, 有些作品受到前衛(wèi)美術(shù)的影響, 甚至連立體主義的影子也飄忽其中。這種情況是喜是憂?應當提倡還是應當反對?民間美術(shù)的民族性與世界性問題值得我們做進一步的探討。
一、社會物質(zhì)關(guān)系影響民間美術(shù)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
任何具有現(xiàn)代文明的民族, 都有它原始蒙昧的歷史階段。當時該民族的社會物質(zhì)關(guān)系即經(jīng)濟基礎(chǔ)孕育產(chǎn)生了本民族的文化藝術(shù)———當然包括民間美術(shù)。我們中華民族或亞洲、歐洲等各民族的原始美術(shù)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中國自漢朝末年出現(xiàn)宮廷畫師之前, 所有的美術(shù)品, 包括巖畫、石雕、宗教壁畫在內(nèi), 應當說全是出自民間畫師之手。即使有了專業(yè)的宮廷畫師和其他的專業(yè)畫家以后, 民間美術(shù)也以其特有的方式流行于社會生活的底層。經(jīng)過幾千年的繼承和發(fā)展, 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東方的、中華民族的民間美術(shù)傳統(tǒng), 而中華民族是五十多個民族的總匯, 每一個民族, 又有著本民族的藝術(shù)源流。由于地理位置、歷史背景、文化淵源和社會習俗等等的差異, 每一個民族的美術(shù)又具有自己獨特的藝術(shù)特質(zhì), 粗獷強勁的、渾厚堅實的、清麗靈秀的, 異彩紛呈, 各臻其妙。這是令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會感到無比自豪的!
對于我們中華民族的民間美術(shù)的性質(zhì)、特點和規(guī)律, 我們應當責無旁貸地去挖掘, 去認識, 去總結(jié), 去繼承, 去發(fā)展, 使之更強有力地影響我們的現(xiàn)代民間美術(shù)創(chuàng)作。
二、民間美術(shù)的民族性與世界性融合與發(fā)展的必要性
藝術(shù)的民族性是指“運用本民族的獨特藝術(shù)形式、藝術(shù)手法來反映現(xiàn)實生活, 使文藝作品有民族氣派和民族風格。”[1]具有民族性特點的藝術(shù)作品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藝術(shù)傳統(tǒng)及審美意識, 采用傳統(tǒng)藝術(shù)形式創(chuàng)作, 主要表現(xiàn)本民族人民群眾的生活、思想感情、愿望和藝術(shù)審美情趣。藝術(shù)的世界性主張擺脫桎梏、解放思想、拋棄民族文化傳統(tǒng), 是一種超階級的勢力擴充[2]。“古為今用, 洋為中用”, 這前一句講的是繼承本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 后一句講的就是吸收外國的藝術(shù)營養(yǎng)。既然交流是客觀存在的, 那么, 吸收則是理所當然的。關(guān)于藝術(shù)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guān)系有以下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藝術(shù)的世界性超越民族性。由于時代的前進, 文化藝術(shù)同經(jīng)濟一樣會在相互借鑒的基礎(chǔ)上趨于統(tǒng)一, 形成具有同一特點的超越民族性的世界性藝術(shù)潮流, 這種具有世界意義的國際化藝術(shù)將成為今后世界藝術(shù)發(fā)展的主流。第二種觀點認為藝術(shù)的世界性同樣具有民族性。這種觀點認為隨著藝術(shù)的發(fā)展, 以及人們對藝術(shù)民族性認識的深入, 只有在積極吸收外來文化的基礎(chǔ)上, 不斷發(fā)展民族藝術(shù), 才能使藝術(shù)作品具有真正的民族性。
現(xiàn)代社會生產(chǎn)力的巨大發(fā)展越來越迅速地縮小了社會在物質(zhì)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空間距離。現(xiàn)代交通的發(fā)達, 使人們可以朝亞而暮歐;而現(xiàn)代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卻不斷使精神領(lǐng)域的東西陌路相逢, 朝疏而暮親。文化藝術(shù)方面的交流, 當然是現(xiàn)代社會信息交流的中心內(nèi)容之一。這種交流首先表現(xiàn)在接受和欣賞的范圍內(nèi)。西方富豪的別墅中, 一枚東方的民間藝術(shù)品置身于諸多華貴陳設(shè)之中, 常常是獨具風韻, 令人垂青。中國民間的老大娘憑一把剪刀, 在眾多藝術(shù)家的睽睽眾目之下, 引出傾倒四座的震驚。許多外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農(nóng)村, 購買農(nóng)民生產(chǎn)出來的剪紙、刺繡、繪畫或雕刻等民間藝術(shù)品, 從事收藏或研究[3]。另一方面, 西方的許多藝術(shù)品在中國也越來越擴大了讀者群和欣賞面。非洲民間美術(shù)到中國美術(shù)館來展出, 參觀者趨之若鶩, 其中更不乏捧著本子臨摹的人, 這是經(jīng)常可以目擊的鏡頭。
三、民間美術(shù)民族性與世界性如何融合創(chuàng)新發(fā)展
當一件外地、外民族的民間美術(shù)品被另一位不同地域或不同民族的民間美術(shù)家通過欣賞而引起審美共鳴時, 他便會有意無意地接受其中的某些藝術(shù)信息, 接著便會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出來, 逐漸將這些藝術(shù)信息變成自己的藝術(shù)營養(yǎng)。這本是無可厚非的事情。在國內(nèi)兄弟民族之間是如此, 在國際間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也是如此。尤其是進入網(wǎng)絡(luò)時代經(jīng)常強調(diào)一體化、全球化的今天, 這種交流與趨同現(xiàn)象更是不可避免的。這一新的世界性的趨勢, “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 使一切國家的生產(chǎn)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guān)自守狀態(tài),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zhì)的生產(chǎn)已如此, 精神的生產(chǎn)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chǎn)品成了公共的財產(chǎn)。”[4]
當代民間美術(shù)受到世界性文化的沖擊是不可避免的, 這種藝術(shù)方面的交流, 就像洶涌飛騰的巨浪, 必將沖決一切妄想阻遏它的閘門, 匯入世界藝術(shù)的海洋之中, 當然民族藝術(shù)的傳播、影響與其產(chǎn)生、發(fā)展一樣, 有個客觀的橫向與縱向的深入擅變過程, 其確定性是其民族性, 是不可替代的, 其不確定性是指在被其他民族所理解、接受的過程中所呈現(xiàn)的復雜多樣的文化變異、再造[4]。所以筆者認為民間美術(shù)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優(yōu)化選擇, 是在中華文化背景下, 堅持民族性和國際性的對接、融合、創(chuàng)新, 在世界藝術(shù)的大舞臺上, 民族性才有意義, 離開這個舞臺不僅其藝術(shù)的民族性將失去光彩, 藝術(shù)的世界性也不復存在[5]。自改革開放以來, 民間美術(shù)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匠心獨運、追求創(chuàng)新”的思想使得很多民間藝術(shù)家追求藝術(shù)畫作與世界繪畫趨勢的融合, 當然在現(xiàn)階段, 民間美術(shù)要想走向世界, 必須要處理好繼承傳統(tǒng)與追求創(chuàng)新的關(guān)系, 認識到促進民間美術(shù)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的必要性, 在保持民間美術(shù)鮮明民族特性的同時積極探求與世界接軌的方式方法。
現(xiàn)代的媒體傳播, 更是便捷而準確地促成了東西方美術(shù)品 (包括民間美術(shù)作品) 的相互交流。交流還表現(xiàn)在更高的層次, 那就是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文學藝術(shù)總是有各自民族的傳統(tǒng)淵源, 但又是不斷地在與其他民族的互相影響中發(fā)展的, 民間美術(shù)也是如此。即以我國現(xiàn)代民間繪畫而論, 全國被文化部命名的60多個現(xiàn)代民間繪畫之鄉(xiāng), 分布全國各地。在全國性展覽上一看, 從生活內(nèi)容即作品取材上看, 地方性、民族傳統(tǒng)性較為明顯, 而就表現(xiàn)手法來看, 我們不得不承認, 越來越難以區(qū)分西北高原與江南水鄉(xiāng)的差異, 云貴山區(qū)與東北平原的差異。當然, 仔細研究鑒別, 差異還是存在的, 但大勢趨同卻是毋庸諱言的事實。而且看得出來, 越是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 越具有趨同的廣度與深度。
當然, 那種認為“老祖宗”的東西一點也不能變的抱殘守缺態(tài)度, 在今天看來是很可笑的。如今, 人們的物質(zhì)生活領(lǐng)域中已經(jīng)越來越多地滲入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信息。社會物質(zhì)生活發(fā)生的各種變化, 一定會反映到作為上層建筑的精神文化領(lǐng)域中來, 作為精神文化產(chǎn)品之一的現(xiàn)代民間美術(shù), 也必然要潛移默化地融匯著這些變異的信息, 并且反映到具體的創(chuàng)作活動中去, 使作品從內(nèi)容到形式逐漸地產(chǎn)生某種嬗變, 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
不可否認的是,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中國加入“WTO”, 我們在學習西方科學技術(shù)的同時, 也受到了西方現(xiàn)代文化的沖擊, 在諸如音樂、影視等方面沖擊尤烈。那種不顧國情, 無視傳統(tǒng), 盲目效仿西方文藝流派的做法, 則是在落后狀態(tài)下民族自卑心理的表現(xiàn)。“這種態(tài)度, 除了反映出對于東方傳統(tǒng)的無知, 同時還包含著一種誤解, 即將經(jīng)濟和物質(zhì)技術(shù)上的進步和藝術(shù)發(fā)展水平混同為一了。”[6]而這種錯誤即使在西方也是早就被批判過的。
在民間美術(shù)領(lǐng)域中, 我國有著幾千年古老藝術(shù)傳統(tǒng), 其中, 不乏優(yōu)秀部分, 有些甚至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華, 成了我們的國粹。許多民間傳統(tǒng)的絕技絕藝現(xiàn)在被開發(fā), 與現(xiàn)代工藝美術(shù)相結(jié)合, 使古老的民間技藝得以開放出燦爛的現(xiàn)代藝術(shù)之花, 其作品成為國家的瑰寶, 在國際交流中產(chǎn)生巨大的文化感召力。所以, 現(xiàn)代民間美術(shù)一定要認識自己的祖宗, 學習并繼承傳統(tǒng), 要讓我們的現(xiàn)代民間美術(shù)打上一個明顯而清晰的中華民族的烙印。作為民族的精神, 民族的品質(zhì), 民族的風格, “這一烙印”是絕不可少的。但這絕不是說, 民間美術(shù)可以拒絕外民族和外國的東西。世界在發(fā)展, 人類在進步, 應該說, 作為人類精神生活產(chǎn)品之一的民間美術(shù), 也在發(fā)展, 也在進步, 不可能老是停滯在某個階段上。在文化藝術(shù)的發(fā)展中, 中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長短。在珍視我們自己優(yōu)秀傳統(tǒng)的同時, 我們也應同時看到并承認外國、外民族的高明之處、優(yōu)秀之處。只要不是固步自封的“國粹主義”者, 就應當采取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我們接受外國的長處, 會使我們自己的東西有一個躍進。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jié)合, 用來改進和發(fā)揚中國的東西, 創(chuàng)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7]
從現(xiàn)代民間美術(shù)這個名稱出發(fā), 首先, 它要求是民間美術(shù), 不是學院派的、專業(yè)的美術(shù), 除了民間的生活內(nèi)容以外, 還要有民間的藝術(shù)形式。其次是現(xiàn)代的, 不是仿古的。這個“現(xiàn)代”怎么體現(xiàn)呢?除了現(xiàn)代的生活內(nèi)容, 重要的是要有現(xiàn)代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 這就大有文章可做了。現(xiàn)代的東西不是個別人主觀臆造出來的, 而是通過縱向橫向的藝術(shù)信息的交流, 經(jīng)過與本地民間藝術(shù)語言的交融、消化, 逐漸產(chǎn)生出既是中國的、傳統(tǒng)的、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民間的、現(xiàn)代的藝術(shù)語言。這是一個復雜的過程, 只有經(jīng)過這個過程而產(chǎn)生出來的產(chǎn)品, 才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那種“中國獨特的新東西。”[8]任何泥古不化、閉門造車或崇洋媚外、生吞活剝的態(tài)度, 都是辦不好這件事的。
四、結(jié)語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我們學習、吸收的目的是為了不斷發(fā)展我國的民間美術(shù), 是為了不斷創(chuàng)造出具有我們民族特色的獨特的新東西, 而不是任何其他的目的。民間美術(shù)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 將來會不會被雜化、同化, 我想, 任何事物的發(fā)展都將遵循它自身的規(guī)律, 物質(zhì)生產(chǎn)如此, 精神生產(chǎn)也是如此, 只要觀點正確, 途徑正確, 而不是人為地扭曲它, 這種杞憂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我們有理由相信, 我們中華民族的民間美術(shù), 一定會在世界性的經(jīng)濟和文化之間交流中, 不斷地、日甚一日地顯現(xiàn)出我們本民族的英雄本色。
參考文獻
[1]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1979:1432.
[2]舒新城.辭海[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6:1184.
[3]劉芳.室內(nèi)陳設(shè)設(shè)計與實訓[M].長沙:中南大學出版社, 2009:107.
[4]杜寒風.對藝術(shù)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思考[J].民族藝術(shù), 1998 (1) :30-34.
[5]胡守海.藝術(shù)民族性與世界性[J].美術(shù)篇, 2001 (5) :47-48.
[6]李新生.美術(shù)概論[M].鄭州:大象出版社, 2014:231.
[7]夏杏真.共和國重大文化事件紀程[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3:93.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