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屋詩人吳芳吉1920年至1925年在長沙任教,適逢湖南“自治運動”以及新文化運動在湖南發酵。通過追溯屈子遺風,提倡近代以黃興、蔡鍔為代表的湘人氣骨,吳芳吉嘗試著從湖湘文化傳統和精神中尋找補救中國現實積弊的傳統資源。同時,反思激進政治運動、創辦《湘君》雜志等活動,也反映出其以“溫柔敦厚”詩教匡正人心、改良文化的努力,并最終以詩文的形式呈現出來,構成了吳芳吉個人對于現代湖南乃至中國社會的觀察與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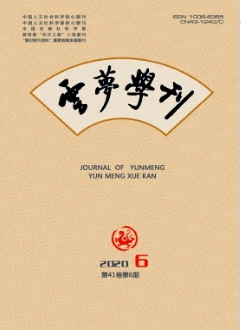
本文源自云夢學刊,2020,41(06):116-124.《云夢學刊》雜志,于1980年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正式創刊,CN:43-1240/C,本刊在國內外有廣泛的覆蓋面,題材新穎,信息量大、時效性強的特點,其中主要欄目有:哲學研究、政治學研究、語言文學研究等.《云夢學刊》雜志以時代性、學術性、探索性為辦刊宗旨,注重刊物的學術水平和社會影響,在《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和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等保持了較高的轉摘和轉載率,多次被評為全國百強社科學報、全國優秀社科學報、全國地方高校名刊、“湖南省優秀理論期刊”。
吳芳吉(1896—1932),字碧柳,號白屋吳生,世稱白屋詩人,重慶江津人,是民國時期著名詩人,其代表作《婉容詞》被譽為可與《孔雀東南飛》相媲美的長篇敘事詩。吳宓曾評價其詩作,“至是值文學革命,新詩初興,君亦多為新詩,以天性篤摯,富感情,又深研舊詩格律,故所作自有特長,與眾不同”,“然其后乃復為舊詩,造詣宏深。但君之舊詩終與人異,蓋真能镕合新詩舊詩之意境材料方法于一爐者”1,道出了吳芳吉詩歌創作介于新與舊、現代與傳統之間的特質。而吳芳吉作為文化保守主義者,通過筆下文字對于新文學、新文化運動乃至整個民國社會的觀察思考,亦往往呈現出特定歷史變局中普通文人的思想狀態與精神癥候,故而其詩亦有“詩史”的性質,成為民國社會動蕩與文化轉型背景下的時代鏡像。
吳芳吉1920年受聘入湘擔任長沙明德學校教員,后又赴周南女中、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任教,期間組織參與湘君詩社、“紅葉會”,并創辦《湘君》雜志,直至1925年離開。這一時期,恰逢新文化運動在湖南地區風起云涌,新文學、新思潮廣為傳播,“遂成一時極燦爛之光”2。同時,因不堪忍受民初軍閥混戰之苦,湖南自1920年起,開始在省長譚延闿、湘紳熊希齡以及青年毛澤東等湖南官民的共同努力下,嘗試推行“聯省自治”,起草憲法,籌備議會,期望“湖南可以做希臘的斯巴達,德國的普魯士,把湖南建成先進省”3。吳芳吉作為外省人,既作為本地教員置身其中,親歷世變,又以旁觀者的姿態在局外冷靜觀察,對于這一歷史時期的湖南有著自我獨特的思考,并最終呈現在他的詩文作品中。因此,梳理吳芳吉此階段的創作、思想活動,不僅是探究其文學道路的重要窗口,也可管窺當時湖南地區的社會文化生態。
一、訪屈子之遺風
1920年8月,因為參加愛國運動的學生和教員打抱不平,得罪了校方,吳芳吉辭去上海中國公學的教職,并出于個人經濟上的考慮,應允明德學校校長胡子靖的邀請,赴長沙任教。當時還遠在日本的詩友郭沫若,曾遙寄一首《送吳碧柳赴長沙》贈別:“洞庭古勝地,屈子詩中王。遺響久已絕,滔滔天下狂。愿君此遠舉,努力軼前驤。蒼生莫辜負,也莫負衡湘。”4在上海的一年多時間里,吳芳吉除了擔任中國公學教職,還曾就任《新群》雜志編輯,頻頻對北京、上海等地正如火如荼進行的“文學革命”“文化運動”發表自己的看法。離開這一風云激蕩的中心舞臺,對于心懷壯志的吳芳吉而言,心中多少有些不甘,他在組詩《別上海》的末尾這樣描寫自己人生的下一站旅途:
只我向何處去?舟人告我洞庭。那豈不有屈原的故里,與杜甫的游魂?那豈不有湘妃的血淚,與馮夷的鼓聲?奈何去彼詩人的絕域,風雨的荒程?5
在詩人個人印象及中國傳統文化譜系中,湖南乃屈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流放之地,是杜甫“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的飄零之所,是許多古代文人政治、人生失意之后的去處,許多遷客騷人甚至在此走向生命的終途。聯想到吳芳吉離開上海的原因,有些失落在所難免,但他很快融入了湖南的生活。正如郭沫若所描繪的那樣,對于傳統讀書人而言,三湘四水代表的古時瀟湘盛景,以及三閭大夫在此地留下的燦爛詩篇,同樣有著別樣的吸引力。對于正有感于新文化運動“魚龍混雜”“淆亂黑白”“恐人心世道未能被得文化運動之福,而已先受文化運動之禍”的吳芳吉來說,離開繁華的現代都市,入長沙城與麓山湘水為伴,于明德學校優雅清凈之校園潛心指導學生誦讀古詩文、研習國學經典,恰能實踐自己有關文學、文化的改良設想。更重要的是,在現代都市當中目睹世道人心日益敗壞、憂心于歐風美雨沖擊傳統文化的詩人,似乎于湖湘深厚文化底蘊中找到了一種情感的慰藉。
因此,初到湖南的吳芳吉,更多的是像柳宗元、劉禹錫、陸游、秦觀等古代寓湘文人一樣,在友人的陪同下,寄情于山水之間,登岳麓,泛湘江,游君山洞庭,并寫下了《愛晚亭》《自湘江望岳麓》《澇湖泛舟》《神鼎山森林中作》《君山濯足歌》等詩作。這些作品保有古典詩詞的神韻,亦夾有新意境、新詞語。如《愛晚亭》詩云:“我坐亭中思古人,古人窺得真和平。我想古人亦笑我,笑我應似自由神。自由神,古人今人兩不分。但聞山鳥繞亭鳴,泠然空谷曳長音,長音美以清,識得古今生命根。”6詩中既有“和平”“自由”這樣的新名詞、新思想,又有“山鳥繞亭”“空谷長音”等古典境界營造。這種詩學的自覺追求,正與吳芳吉入湘不久在《談詩人》一文中提出的主張相契合。在這篇文章中,吳芳吉表示,作為詩人,應該與世無爭,同自然接近:“今人對于甘守淡泊,或遁跡山林之事,攻擊甚力,這都是片面的見解。”“我也是附和‘返于自然’ReturntoNature的人。我是絕對的厭惡現今的社會。”7湖南旖旎的自然風光,恰好成為此時吳芳吉從新文化浪潮的旋渦中暫且退卻出來、繼而反思現代文明的寄托。
進入湖南任教的第二年年初,吳芳吉應湘陰籍學生彭澤岐的邀約,與友人前往汨羅,并寫下《汨羅訪屈原墓作》等詩作,這對他而言是一次文化尋根之旅。五四新舊文化碰撞、各種學說思想交鋒爭鳴,包括郭沫若在內的新文學作家,紛紛通過追溯屈原的高潔人格來吸納自我提倡個性解放與鼓舞愛國熱情的思想。正如美國學者勞倫斯·斯奈德所言,屈原“那充溢著熾熱的自信自尊和孤芳自賞情緒的詩篇,喚起那些因時代與命運而受黑暗統治所折磨的著名人物的個性、獨立精神與孤獨感”8。很顯然,新文學作家對于屈原的接受和推崇,更多著眼于個人主義等現代思想的傳播。而吳芳吉所苦苦追尋的,則是可以支撐現代民族精神的傳統文化資源。在汨羅江畔、屈子墓前,聽山風振起松濤,望青林飛出白鷺,他不僅有“汨羅山水佳,一見如親故”的感慨,更有“君魂不用招,君魂本無數”的發愿。在汨羅江北岸獨醒亭所寫《獨醒亭下作》中,他寫道“一人之精神,民族之性根”“訴我民族苦,招我民族魂”。民族日漸衰沉,好比一顆樹,原來樹上花顏何燦爛,而今卻花謝葉凋零,這需從民族根性上尋找原因。
至于吳芳吉期望從屈原身上以及屈子行吟過的湖湘大地喚醒什么樣的民族根性,雖然詩作中未曾指明,但在其與好友吳宓的書信中卻有坦露。1921年底,在致信吳宓回顧自己入湘一年多來的見聞感受時,吳芳吉曾表示:“湘中文學之盛,在近代中國實推第一。吉在上海新群社習染刻薄暴戾之氣,為此身墮落時代。入湘以后,訪靈均、濂溪、求闕、湘綺之遺風,漸知溫柔敦厚所以立教。其救濟我靈魂與骨氣者,為力至大。”9這里所表現出來的對于滬、湘兩地的情感姿態,與《別上海》中流露的心境已大不相同。上海這座現代都市中所遭遇的“刻薄暴戾之氣”等弊病逐漸顯現。借著游歷三湘四水的機會,吳芳吉也重新追溯了靈均(屈原)、濂溪(周敦頤)、求闕(曾國藩)、湘綺(王闿運)等湖湘先閑的詩文傳統。他在給友人鄧紹勤的書信中曾提到,自己入湘后,致力于收集湘中詩家,從屈原開始,直到近代曾國藩、王闿運、敬安(八指頭陀)等湘人詩集都有整理閱讀。這些顯然都是從儒學及溫柔敦厚詩教著眼的。故而1923年明德學校20周年校慶時,吳芳吉參與發起教員籌資,在校園內修建“楚辭亭”,親自題寫對聯紀念屈原10,后又組織湘君社在此雅集,并根據社員徐紹周所繪屈子像寫下《題屈子畫像》,在詩中歌呼“魂歸來,靈知否”,以鼓腹而狂歌的姿態再次為屈子招魂。
訪屈子之遺風的背后,是吳芳吉對湖湘文化所代表的一種傳統的接納,除了溫柔敦厚的詩教,還有一種精神骨氣。在經歷了北京、上海等不同地域空間與城市文明后,湖南這一曾經心目中“詩人的絕域,風雨的荒程”,給予了處于人生漂泊逆旅中的吳芳吉以一種文化慰藉,并使其生出一種心理上的親近之感。在1925年離湘之際,他又寫下了一首《南國》:“南國長沙美,能容五載居。高樓明月滿,佳氣碧湖虛。笑語相聞慣,殷勤互有余。安能拋汝去,蜀地少芙蕖。”11“芙蕖”原指荷花,漢代王褒追思屈原的《九懷》中有“抽蒲兮陳坐,援芙蕖兮為蓋”一句,吳芳吉以此象征屈子的高潔品格,也指向他在湘期間與本地師生、友人交往過程中所體驗到的文化品格,甚至不惜用自己的巴蜀故鄉作比。盡管這里有離別之際刻意美化的成分,但依然顯示出詩人對于湖南學子及湖湘文化的期待,并將之作為應對現實社會危機的希望寄托。
二、見我湘人兮氣骨
吳芳吉進入湖南時,湖南剛剛經歷了驅除軍閥張敬堯的運動,處于較為混亂的時期。作為南北軍閥必爭之地,當時的三湘大地屢有戰事,民眾飽受兵燹之苦,可謂1920年代初整個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有作者在報刊上發布社論《哀湖南》,稱連年的戰事已經讓湖南“變亂迭生,早已民窮財盡,十室九空”;“豈僅湖南,恐莽莽神州,都要陸沉,則吾湖南哀,又不啻為中國哀”12。據有的學者研究,1921年的中國正經歷著至暗時刻,神州大地災害不斷、兵匪橫行,光是湖南一省饑民就達200萬之多13。這種殘酷的現實,與同時如火如荼進行著的新文化運動,以及知識分子相對自由平穩的生活形成了巨大而又鮮明的反差。吳芳吉本人在來到明德學校任教后,先后經歷了湖南地區的聯省自治風潮、湘軍內訌、湘鄂軍閥戰爭、直系軍閥擾湘等政治軍事事件,目睹了各種由戰亂造成的人道災難,深感于“中國前途,仍屬悲觀,一刻不得有太平之象也”14。故而此階段的湖南形象在吳芳吉筆下并不全是褒揚,他不僅僅有對湖湘文化傳統的追思,也有對于殘酷現實的直觀見證和文學表現,并借批評現實社會與世道人心,呼吁一種民族的精神氣骨。
反映軍閥混戰給普通民眾造成的創傷,一直是吳芳吉詩歌的一個重要主題。此前在四川時,他就通過《兒莫啼行》《曹錕燒豐都行》《巫山巫峽行》《甘薯曲》《塤歌》等詩歌作品,展現亂世當中底層民眾的生活狀態,其中不乏他自己真實的生活體驗。來到湖南后,社會秩序依舊紊亂,吳芳吉雖暫時謀得穩定的工作,卻時時感受到外部戰事的紛擾對平民生活的沖擊。特別是1922年湘軍內訌,當此前被排擠出湖南的譚延闿被孫中山的廣州革命政府任命為湘軍總司令時,在衡陽起兵討伐時任湖南省長的趙恒惕炮擊長沙長達五十天之久,使無辜民眾橫遭禍端。吳芳吉所居住的明德學校寓所附近,經常會有炮彈落下。這期間他寫下了《北門行》《南門行》等詩歌,其中“誰教生亂世,民命豬與狗”(《北門行》)、“長沙十萬戶,縮首如牢囚”(《南門行》)等詩句,正是吳芳吉作為布衣書生對現實發出的泣血控訴。他的長子吳漢驤在長沙城被圍困期間患病,家中孤立無助,于是他便作《圍城中驤兒大病,每夜換班守護,自午夜常坐至天明,冷靜多感,索性題詩》一詩,來反映普通民眾在軍閥兵匪蹂躪下的生存境遇。詩云:
城邊隱約喇叭吹,流彈颯然落四圍。驚起棲鳥無樹息,漫漫長夜慘安歸?
我同鳥鵲等流亡,一水盈盈阻故鄉。何不臨城當匪去,替天行道足鋒芒。15
正是對于社會局面的直觀體驗和失望情緒,促使著吳芳吉入湘之后努力從湖南本地的文化傳統當中尋找改良時弊的精神資源,不但三閭大夫成為他追思的對象,近代以來為國事挺膺負責的湖湘人物亦成為他期望借以重建國民精神的依托。在1921年登衡山后所作的《南岳詩》中,吳芳吉這樣寫道:“此邦最是南方強,當前曾左后蔡黃。我來不幸逢遲暮,老成相繼早凋傷。”16在近代國家民族危機最為深重之際,湖南曾先后出現過曾國藩、左宗棠、蔡鍔、黃興等杰出人物,他們或是清廷中興的肱骨,或是締造共和的功勛。而現今卻呈衰落之象,整個湖湘大地飽受軍閥侵擾、生靈涂炭之苦。在紛亂的時局中,吳芳吉正是通過對近代湘人英武的追溯來反襯現實的無力和無奈,以及對湘中子弟遲暮頹唐的擔憂。在《南岳詩》中,他慨嘆道:
吁嗟斯人盡作古,古人世代皆踵武。湘中尤以健兒稱,個個生龍與活虎。如何古盛至今衰,文章德業鮮人才?太傅祠堂新戰壘,將軍墓表舊蒿萊。我知湘土美風俗,我知湘土古純樸。只因厚道轉偷安,坐令人才不再出!17
細細揣摩吳芳吉詩中之意,其與一年前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歡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有著相似之處,“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氣沉沉的景況,不覺說道:湖南人底精神那里去了”18。陳獨秀期望通過整合晚清民國時期湖南人的精神資源來推動提倡進取、開放精神的新文化運動,而這種期待,正與吳芳吉入湘之后通過詩文向湖湘子弟所表達的意愿一致。以此來看,吳芳吉并不是一位頑固的保守主義者。作為曾先后在聚奎學堂、清華大學等新式學校學習的學子,他懷有傳統士大夫的家國情懷,同時又認同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價值觀念。正因為如此,他才會對蔡鍔、黃興這樣的湖湘人物推崇備至,也才會對于湖南的地方自治運動表現出熱情和關注,并通過自己的方式參與其中。
早在入湘之前,1919年初途徑四川瀘州永寧河邊的護國巖,瞻仰護國戰爭中蔡鍔將軍率領護國軍入川時留下的遺跡時,吳芳吉寫了長詩《護國巖詞》,歌頌其作為“共和神”“國家干”“同胞使者”的豐功偉績,并重提“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精神。1921年3月,湖南省“省憲起草委員會會議”在長沙開幕,宣布從即日開始起草省憲,拉開了湖南地方自治運動的帷幕。吳芳吉亦參加了開幕典禮,并拜謁位于岳麓山的黃興、蔡鍔墓,作《兩墓表詞》,撫今追昔,既以對黃、蔡二位將軍的追思,“見我湘人兮氣骨”,亦希望在“湘憲”紀元,借此鼓舞湘人自立自強的精神:
湘波兮浩蕩,岳麓兮奔放。孤城兮微茫,大野兮平曠。莽縈帶兮四周,萬家環以瞻望,墓表兮指天,山河兮無恙。天之高兮洋洋,我心極兮悲壯。彼來日兮方長,惟斯人兮草創。吁嗟墓表兮堂皇,昭我湘人兮向上。(19)
在短短一年時間內,吳芳吉連續通過紀念近代湘人的文字來呼吁湘中之健兒、湘人之氣骨。與陳獨秀一樣,他期望借助重塑“湖南人的精神”,從國民性、民族精神層面來應對軍閥混戰局面下的社會亂局。而在此之前,毛澤東等人就已在長沙《大公報》數次刊文,為湖南人的自治自決進行輿論造勢,指出:“中國維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戌之秋,湖南人生氣勃發。新學術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設,譚嗣同熊希齡輩領袖其間,全國無出湖南之右”。“湖南有黃克強,中國乃有實行的革命家。”之所以在這之后“新銳頓挫,事業旋亡”,就在于“近事之中湖南受中國之累,不能遂其自然發展的結果”19。他們在反思當時中國武人橫行、政治腐敗的同時,也有一種地方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自覺。
自治運動當中這種自覺的文化精神與民族意識,以及對于近代湘人精神骨氣的重新發掘和提倡,同樣是吳芳吉所看重的。從他這一時期的文章書信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對自治運動所抱有的期望。故而1923年當省自治運動被軍閥內訌破壞時,吳芳吉于失望之余,在自注為“哀湖南省自治之鮮終”的《示同學少年》詩中,有“全湘活百姓,岳麓死將軍。傷時翻念古,誰與泣秋墳”“湘江流千里,東西成敵國。爭戰寧辭苦,所惜鮮人杰”等詩句,譏諷當時譚延闿與趙恒惕之間的內斗殃及湖湘百姓;也有“當時翼曾左,神州挽陸沉。云帆東海開,陣馬天山牧”“每讀《湘軍志》,何其古道篤!每詠《獨行篇》,何其厚風俗”20這樣的感嘆,從古道風俗的層面,呼喚心目中真正的湖湘人杰和民族氣骨。
三、領袖斯民,納之正軌
正是基于這種追溯近代湖南人氣骨、激發國家向上民魂的信念,才使得吳芳吉在湖南的文學、教育活動顯現出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價值。盡管其信念和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領袖提倡近代湖南人精神、期望借此改變國民消沉委頓與不能振作之現狀的初衷不謀而合,但他們在具體認知和實踐上有著各自的取舍:陳獨秀等人更偏向于獨立、開放、進取以至于“革命”的現代國民品性,并將之運用于反對孔教、反對舊道德的新文化運動上來;而自幼便深受儒學熏陶、恪守儒家道義的吳芳吉,一方面贊許這種從屈子開始就具有的感時憂國精神,欲重振“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傳統氣骨以應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另一方面卻憂心過于激烈的文化運動,會如操之過急的政治革命一樣,不僅不能換來國家民族的新生,反而會動搖社會文化的基礎根本。
在上海中國公學任教時,吳芳吉在發表于《新人》雜志的《答上海民國日報記者邵力子》一文中明確表示,自己并不反對新文化運動,甚至是極端贊成的,反對的只是有人將之當作投機事業,進行膚泛的叫囂、互相陷害諂毀。他指出新文化運動如要成功,首先在于參與者要有良好的人格。居湘期間,吳芳吉曾極力支持湖南當地的愛國行為。1921年底,當長沙的市民、工人、學生舉行大規模游行,以反對當年美、英、日、法等國為瓜分支配中國等遠東區域而在華盛頓召開的“太平洋會議”時,吳芳吉還曾興奮地寫下詩作《萬歲之聲》,贊揚湖南民眾的愛國熱情。但是,他對于借此尋釁滋事的盲動行徑和由此暴露的兇惡人性,包括煽動激進暴力和思想的文學,始終保持著警惕,故而在給好友吳宓的信中屢屢有諸如“湖南社會形勢日趨激進,在此頗為危殆”之語。特別是長沙數次爆發反日活動,一些人借反對日貨的名義,作出一些過激的暴力行為,“見人衣冠似日貨者,立即毀碎,復以硝強水漆面,曰亡國奴。令肉腐不能滌去”。這讓一直反感于以新文化運動、愛國運動為擋箭牌而肆意荼毒社會的吳芳吉尤感憤然,并將之歸因于五四學生運動的發展演變,他遣責道:
群眾專橫之事,自民國八年所謂五四運動者始。當時教育界諸公頗以為得意。今則蕩激益暴,彼日君子,復無悔禍之心,是可嘆也!21
類似于魯迅早年在《破惡聲論》等文章中對“以眾虐獨”、多數人專制進行的反思,吳芳吉對于這種群體性的盲動(無論是政治層面還是文化層面)也有著自我清醒的認知和批判。在發表于《新人》雜志的另一論文《談詩人》中,吳芳吉提出過文學“個人無政府主義”的概念。盡管他對于當時在中國青年中盛行的安娜其主義(無政府主義)有著嚴肅的批評,但極力主張這種個人的“無政府主義”。他認為文學之根本,在于個人而非團體,詩人不應被團體(新文化、新思潮)之觀念所裹挾,不應取媚于外部社會的風潮。延伸到文化層面,吳芳吉認為國家前途的好壞,除了此類群體性運動之外,更應注意個人的德性修養。他在自治運動期間給鄧紹勤的信中批評“中國今日之文學,為流氓滑頭所假借”,而所謂新舊文化云云,乃是“欺騙群眾以行其惡”22;又談到學生借運動為名要挾教師的活動,感嘆道:“坐令其為義和團,為過激黨,而不敢匡正以誘啟之。學風如此,復何言哉。”吳芳吉反對被群體意志所裹挾、煽動階級或民族仇恨的激進行為,期愿在內政日紛、外侮無已的時代“得明達穩健之士,領袖斯民,納之正軌”23。
也正因為此,吳芳吉雖支持湖南發生的自治運動和學生愛國行徑,但對于普通民眾特別是青年學子的思想動態有著自己獨立的觀察思考,并期望通過學校教育、文學創作、結社雅集及創辦文學刊物等活動,在文化層面以穩健的姿態來引導社會民眾。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吳芳吉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帶有鮮明的儒學色彩,注重‘詩教’(文學教育)和‘禮教’(倫理教育),并以之作為教育改良的基石和匡正人心的途徑”24。吳芳吉提倡儒家思想中的“性善”學說,注重個人道德的自我完善,看重傳統“溫柔敦厚”詩教的引導作用。他在當時明德學校的校刊《明德半月刊》上指出,“今社會最要之事,莫急于正人心以厚風俗,而藉風俗以化人心”25,主張潛移默化后來者,育人于無形。而與之不同,當時湖南學生界的宣言卻是“不要夢想一部省憲,就可以給予人民的自由,因為自由的獲得,是要革命的鮮血,不是呆板的文字”26。這一方面確是由于對于軍閥操縱下的所謂省憲、自治運動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吳芳吉所擔憂的一味追求激進和暴力,缺乏對社會及文化進行重建的耐心。
1922年,湖南宣布成為“自治省”后,吳芳吉在明德學校的教育漸漸有了成效。他在給吳宓的信中談到湘省教育情形時說:“湖南少年之迷信新潮,為眾省之冠。然一二月來,已有多人漸漸轉其方向,而趨于中道”,同時,有感于“此間諸生,富于文學趣味者尚多。惟以學校偏重英文、數學,故于國文進功甚少。”27同年底,吳芳吉又在致鄧紹勤的信中談及湘軍之后古文之不傳,借推崇曾文正公之文,批評譚嗣同的偏激,并論及古文之法,認為“為文不難,難乎在人。自古文家,其節莫不堅韌,其氣莫不浩然,其心莫不以道自任,其行莫不溫柔敦厚”28。在這里,吳芳吉將近代湘人身上尤為凸顯的堅韌浩然氣節與傳統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相提并論,表面言說的是古文之道,實際卻構成了對只注重氣節卻忽視古道風俗的群眾運動的補充思考。
也正是在這一年,受到吳宓在南京東南大學創辦《學衡》雜志的啟發,吳芳吉也萌生了借助明德學校辦讀書會與文化刊物以宣揚儒學道德根性的想法,這就是后來與《學衡》雜志遙相呼應的《湘君》雜志。1922年3月,《湘君》在長沙創刊,吳芳吉親自撰寫發刊詞闡明辦刊宗旨,所以相尚相勉者三事:道德、文章、志氣。他在同期為近代湘軍將領羅澤南詩選所作《〈羅山詩選〉導言》中說道:
三湘自屈子以還,素以騷人詞客、志士健兒稱雄海內。半世紀前,湘人征伐之威遍十八省。而文運之隆,迄于民國初基,猶為世所宗仰。……
羅山之詩,古道照人。何以致之,是亦風俗之所成而已。今湘中士夫,競新文學矣。求之于白話,求之于異邦,舍己以從人,逐末而棄本。29
正是在《湘君》雜志上,吳芳吉先后發表了《吾人眼中之新舊文學觀》《再論吾人眼中之新舊文學觀》等文章,與胡適等人的文學革命主張展開對話,闡明自己“文學惟有是與不是,而無所謂新與不新”的觀點,并邀請吳宓等人為《湘君》雜志撰稿,多刊發“矯正偽新派文學之失”的論文及舊體詩詞。同時,他還以明德學校的湘君社為基礎,多次組織教員與學生在岳麓山舉行紅葉會這樣的雅集活動,即使在軍閥內訌、長沙圍城的硝煙炮火中,也弦歌不輟,并留下了“楓葉已教紅萬樹,青山久不著狂歌”“炮火圍城天未醒,飛鴻何處悵云羅”(《寄答明德十七班諸君》)等詩句。作為一份地方性的文學刊物,吳芳吉的直接目的,正是期望以此刊物的文學實踐活動及所傳達的文化理想影響湘中子弟。他還通過《湘君》雜志與湖南的讀者互動,如發表于第三號與湘潭女生討論詩歌的《答湘潭女兒》30等等,但其中只有少數文章通過被《學衡》雜志轉錄而推向更廣的讀者群體。雖然因為不肯迎合潮流,《湘君》雜志在湖南本地的銷售寥落,但此段經歷無疑是吳芳吉自己文化觀念和文學抱負的一次施展。離開湖南后,吳芳吉曾作詩《湘居》追憶,其中有“湖上旌旗張異軍,湘君社友盡能文”“麓山勝友賞心同,邀約清秋萬樹楓”等句,字里行間透露出對湘君社詩友的懷念,以及對《湘君》雜志作為新文學之外“異軍”的驕傲之情。
四、結語
1925年8月,因為“湖南的思想界,日趨極端”31,且有波及到吳芳吉本人之勢,他不得不離開湖南,赴西安西北大學任教。他在湖南的五年生活,遠不如《湘居》中描寫的那般詩意浪漫,不僅其本人時常會憂慮于紛亂的時局及日益激進的社會,而且他在明德學校及《湘君》雜志的文學活動也并不被本地學生所接受和理解。當時長沙《湘報》新辦的副刊《野火》,便激烈地反對吳芳吉所代表的“復古風氣”,甚至批評其“是四川的一個冬烘遺少,我們久已知道他在長沙給了青年不少的麻醉,和浪漫的梅毒”32。在湖南的這種遭際,大概是吳芳吉短暫一生的縮影和寫照。在趨時求新的社會變革浪潮下,他被當作一個保守派,或被忽視,或受質疑。但透過這位白屋詩人的筆端,亦能窺見當時湖南地區日趨激進的社會思想情形。
吳芳吉在湖南期間的文學活動,并非徒勞無功。1932年他病逝于江津后,以《明德旬刊》為代表的湖南刊物屢有文章紀念,并在1935年出有紀念專號,稱“其創《湘君》,乃憫文人陷溺,與湘軍異事齊轍,終能翕合吾徒,去稂莠而滋嘉榖,排揵局而敞高堂”33,對其在湘期間的貢獻有了更為客觀公正的評價。后來著名的歷史學者、當時還是青年學生的周策縱,在長沙市第一中學的校園刊物《長高學生》上發表的習作《讀吳碧柳白屋詩存》云:“詩境重新大小吳,好詩與好色無殊。君詩屈子峨眉樣,我好君詩好色乎。”34吳芳吉是追溯著三閭大夫的足跡來到湖南的,湘中學子將其詩作與屈子并提,是對其湖南時期思想及文學價值的肯定,亦何嘗不代表現代湖南社會發展的另一股文化潛流。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