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0年6月,四川省公布了第二屆“四川十大歷史文化名人”,漢代司馬相如入選。這與其在經學、漢大賦、政論散文等諸多領域的開創性貢獻,具有“卓絕漢代”的崇高地位不無關系。自《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開始,歷代有關司馬相如的評價,都成為一個特定時代文化觀念的體現。在現代中國文化視野下,司馬相如被賦予全新的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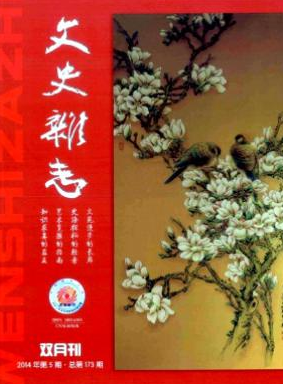
本文源自文史雜志 2021年1期《文史雜志》(雙月刊)創刊于1985年,是由四川省文史研究館;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主辦的文史刊物。《文史雜志》積極評介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燦爛文明以及優秀文化遺產;向群眾進行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普及宣傳,進行社會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啟發教育,包含文學,歷史,藝術三個范疇。《文史雜志》獲得四川省質量一級期刊。
關鍵詞:司馬相如;漢代;文化;文學
一
重視個人的權利,倡導自由平等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激蕩起重新建構文明新秩序的現代思潮。女性解放與婚姻自由在中國于是逐漸成為社會主潮。世人開始對司馬相如的為人和行事產生共鳴。對相如、文君故事的正面解讀似已成為當時社會思潮的主流,并因此對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巔峰人物如郭沫若等的崛起,有著直接的作用。
1919年9月11日的《時事新報·學燈》首次出現了“沫若”這個名字。郭沫若自己對這個筆名的解釋是:“沫若”(Mei Jo),是指故鄉的沫水與若水兩條河。在司馬相如散文《難蜀父老》中“故乃關沫若,徼牂柯,鏤零山,梁孫原”有“沫若”二字,可能就是沫水與若水二河名稱的開始。需要強調的是,“沫若”這個現代文化符號所隱含深沉的傳統印痕,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一個話題。遠在異國,回眸故土,“故鄉的兩條河”即大渡河以及流入大渡河的雅河,引發他諸多聯想。或許可以說,“渾身充滿創造氣”的郭沫若的文化性格,極有可能就是深受司馬相如在《難蜀父老》中“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1]的影響。馬積高教授的《賦史》對司馬相如大賦藝術特色的概括是“其奧妙全在于氣勢”;而郭沫若“女神時期”的絕大多數詩作、甚至包括他的其他代表作常常轟動一時,奧妙之一也應該“在于氣勢”。郭沫若對自己的鄉邦前賢,是充滿敬意的,如他在《蜀道奇》詩中所言:“文翁治蜀文教敷,爰產揚雄與相如。詩人從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蘇。”[2]
郭沫若于1923年問世的話劇《卓文君》,讓漢代蜀中才女卓文君以一個叛逆女性的現代形象重新出現在中國人面前。該劇對反對封建禮教、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爭取人格獨立和婚姻自由的“叛逆女性”卓文君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兩千多年前的“鄉賢”司馬相如“非常之人”的文化性格,再次進入新文化運動戰士的視野。在該劇的創作者郭沫若眼中,文君私奔相如是對舊式道德的完全背叛,是沖破中國封建羅網的“很好的標本”[3]。可以說,歷史話劇《三個叛逆的女性》(包括《卓文君》),是詩人郭沫若青春熱情外放性格的呈現,亦是新時代反封建斗爭的需要。
據“創造社四大臺柱”之一的成仿吾回憶,郭沫若曾經打算將《卓文君》以《司馬相如》為劇名面世。為此,郭沫若曾寫信囑托把《卓》劇題目改為《司馬相如》,但是成仿吾則認為無需更改,以后續作時再用別的名稱,這樣把原名留下來了。[4]郭沫若欲將《卓》劇以《司馬相如》為題發表,正是因為劇中對司馬相如充滿正面的肯定,如描寫卓文君對司馬相如才華的傾慕,設計了“高山流水”覓知音等情節,使得相如文君故事合乎歷史邏輯而不落入“劫財劫色”的俗套。
此外,郭沫若在《我的少年時代》等“自傳體”作品中,大量甚至有些刻意突出和渲染自己的少年性心理活動,這都讓人們想起唐代劉知幾在《史通·序傳》中對司馬相如的評價:“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5]郭沫若花費過相當多的功夫對司馬相如進行研究,如認為《遠游》并非是屈原的舊作,其實是司馬相如《大人賦》之草稿等論點,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郭沫若還在1957年題詞邛崍文君井公園:“反抗封建是前驅,佳話傳千古”,極力贊賞司馬相如與卓文君。
二
1926年,魯迅先生在廈門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為此編寫了著名講義《漢文學史綱要》,其中《司馬相如與司馬遷》一章明確指出:“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而一則寂寥,一則被刑。蓋雄于文者,常桀驁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6]。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中,有很多德才兼備的知識分子煢煢孑立,懷才不遇。魯迅先生的人生際遇大概亦是如此。他對司馬相如的人生與創作的感慨,化用他使用過的一句話,即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
作為當年探討中國文學史的首席作家魯迅,面對漢代司馬相如的浪漫不羈、反抗權貴與挑戰流俗等品質與才情,當是心潮激蕩。無疑,兩千年前的司馬相如在彼時叩響了一個思想啟蒙家和新文化運動戰士的心扉。魯迅在社會巨變與自我人生轉折的十字路口曾經反復思索“我今后的路還當選擇:研究而教書呢,還是仍作流民而創作?”[7]而在“革命文學論戰”中,魯迅也曾腹背受敵;加上“女師大事件”以及與許廣平關系引發的“流言”等等,使其最終選擇“逃亡”嶺南。了解了這段歷史,就更容易理解為什么魯迅著述多次引用司馬相如作品,甚至手書其《大人賦》中辭句饋贈章川島;也更容易理解魯迅先生對司馬相如的“傲誕”為人、“不欲迎雄主之意”的個性尊嚴,特別是“精神極流動”的作品氣韻的高度贊賞——因為這些都與魯迅先生當時的處境、心情相暗合,即如他在1932年的一次講演中提到的“所以幫閑文學又名篾片文學。小說就做著篾片的職務。漢武帝時候,只有司馬相如不高興這樣,常常裝病不出去”[8]。
魯迅先生以“廣博閎麗,卓絕漢代”[9]來高度評價司馬相如的文學成就,其“文章西漢兩司馬”之說,當受班固《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中關于“文章則司馬遷、相如”之論的影響。
魯迅先生在其講義《漢文學史綱要·司馬相如與司馬遷》中,還直接引用明代學人的評價:“《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10];又用“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張、潘有其材而無其筆”“子云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流動之處”[11]的評價,將司馬相如置放于漢代文壇首位,強調其影響深遠,“為歷代評騭家所傾倒,可謂至矣”[12]!
魯迅先生對司馬相如文學的創造性也頗為看重,有“蓋漢興好楚聲,武帝左右親信,如朱買臣等,多以楚辭進。而相如獨變其體,蓋以瑋奇之意,飾以綺麗之辭,句之短長,亦不拘成法,與當時甚不同”[13]的說法;換句話說,魯迅先生認為,司馬相如在文學創作上絕不因循守舊,非常注重創新。魯迅對司馬相如文學創作成就的推許,乃基于中國現代文化建構中極其活躍和重要的“創新”特質而發。
魯迅先生既注意司馬相如《子虛》《上林》《大人》諸賦的時代價值和地位影響,也很重視作者的短賦。他還多次提及自己對司馬相如的經學與小學的分析研究。他非常推崇司馬相如的文采,認為“司馬相如在文學史上也還是很重要的作家,為什么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14]。魯迅先生還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再次推崇《西京雜記》中有關司馬相如的故事,并稱贊:“若論文學,則此在古小說中,固亦意緒秀異,文筆可觀者也”[15]。
三
司馬相如把文學作為語言藝術進行試驗,對中國文學的形式美感的創造起到開創性的作用。正因為如此,在純粹的學術領域,錢鍾書先生以激賞的態度高度評價其文體創新意義,并對相如與文君的態度也絲毫不隱晦:“相如于己之‘竊妻,縱未津津描畫,而肯夫子自道,不諱不怍,則不特創域中自傳之列,抑足為天下《懺悔錄》之開山焉。”[16]中國當代美學家李澤厚、劉綱紀等認為,在中國歷史上,真正意義上開始獨立研究純粹的文藝、直接談論藝術創作,是從開創漢賦的司馬相如開始的。[17]
龔克昌教授認為,文學自覺時代的起點,應該提前到司馬相如進行文學創作的西漢前期,最主要的理由有兩點:第一,司馬相如已能夠充分表現文學藝術的基本特點,能自覺運用形象思維,運用并發展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積極追求文學藝術的形式美;第二,已提出比較系統的文學藝術創作主張而進行主動創作。誠如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所言,文學藝術已經不甘于繼續充當儒經的附庸,而是根據自身發展的特點,發展成為一個獨立學科。“這是文學藝術覺醒的表現,是文學藝術自覺時代到來的象征”[18]。事實上,以司馬相如為代表的大賦雄霸整個漢代文壇,傳達出大漢帝國博大恢宏的精神風采。漢賦的浪漫主義創作方法和華麗的辭藻、鋪張揚厲的筆法,標志著中國文學自覺時代的降臨。
司馬相如不似揚雄、王陽明等有“圣人”情懷或情結。正史載其“口吃”“不善交際”“不慕官爵”、愛“稱病”閑居等,讀書、寫作才是他人生最大的樂趣。應該說,司馬相如是一個有著巴蜀文化傳統特質的文人。他自覺地將國家統一、民族自尊的政治訴求,以及獨立、自由的文化主張等融入文學作品,為漢代及后世中國廣大知識分子所理解、喜愛、接受,甚至仿效。而這則是因為其契合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共同心理或稱集體無意識,契合了西風東漸以來的思想潮流。
注釋:
[1]李孝中校注《司馬相如集校注》,巴蜀書社2000年版,第58頁。
[2]郭沫若:《郭沫若選集》 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0頁。
[3]郭沫若:《卓文君》后記,《郭沫若選集》第3卷上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成仿吾:《〈卓文君〉后記》,《創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1923年3月10日。
[5]齊豫生等主編《白話四庫全書·史部·史通》,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頁。
[6][9][10][11][12][13]魯迅:《漢文學史綱要》,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頁—74頁。
[7]魯迅:《兩地書·1926年12月3日致許廣平的信》,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
[8][14]魯迅:《集外集拾遺·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
[15]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
[16]錢鍾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57—359頁。
[17]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第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53頁。
[18]龔克昌:《漢賦——文學自覺時代的起點》,《文史哲》1988年第5期;《漢賦新論》,《貴州大學學報》2003年4期。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