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峭,生卒年不詳,字景升,唐末五代道士,道教思想家。顯德四年( 957 年) ,“隱士譚景升居終南山,與陳摶相師友,著《化書》百十篇,窮括化原,久之仙去。”( 老磐: 《佛祖統(tǒng)紀(jì)》卷四十二) 《化書》是中國(guó)道教哲學(xué)史上專門以“轉(zhuǎn)化”為題,以哲學(xué)本體視野和道教神仙追求的終極信仰切入世界本體“道”及其化生形態(tài),進(jìn)而考察世界整體及多樣事物之間的變化情態(tài)、相互轉(zhuǎn)化和普遍聯(lián)系,并在此基礎(chǔ)上論述人身形質(zhì)轉(zhuǎn)化和修道成仙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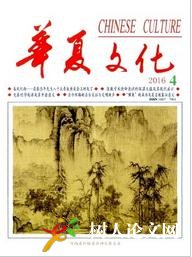
陳懷松, 華夏文化 發(fā)表時(shí)間:2019-12-25
一、“道化”哲學(xué)本體內(nèi)涵
“道”自從先秦老子開創(chuàng)并系統(tǒng)論述以來(lái),成為道教思想家關(guān)注和探討的哲學(xué)本體概念。譚峭在其著作中同樣認(rèn)為本體性的“道”是一種根本性的決定力量,整個(gè)世界的變化發(fā)展都是“道” 自身從形而上的本體層面逐漸向形而下的現(xiàn)象層面的不斷委落和轉(zhuǎn)化,其間經(jīng)過各種性質(zhì)迥異又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環(huán)節(jié),最終塑造了變化的總體情態(tài)及世界本身的多元性特征。
( 一) “化”的本體結(jié)構(gòu): 道之委落與回用
《化書》虛化萬(wàn)物思想,是在繼承老子、莊子以及佛教關(guān)于空、無(wú)、虛的思想基礎(chǔ)上提出來(lái)的。“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wàn)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wàn)物所以通也。”( 《化書》卷一《道化》) 這一綱領(lǐng)性的論述簡(jiǎn)明扼要地融攝了道教哲學(xué)的基本觀念:
其一,虛。“虛”的觀念在道家哲學(xué)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論道家思想特點(diǎn)在于“以虛無(wú)為本”。《老子》第四章言: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wàn)物之宗。”老子用 “沖”和“淵”的概念形容道的虛靜狀態(tài),它不但是萬(wàn)物的根源,而且支配和決定萬(wàn)物變化的作用不可窮竭。在道家和道教哲學(xué)視野中,“道”乃是一個(gè)變體,是一個(gè)動(dòng)體。它本身不斷變動(dòng),整個(gè)宇宙萬(wàn)物都隨著“道”而永遠(yuǎn)在“變”在“動(dòng)”,任何事物在變動(dòng)中都會(huì)消失熄滅,而“道”則永遠(yuǎn)不會(huì)消失熄滅。( 陳鼓應(yīng): 《老子哲學(xué)系統(tǒng)的形成和開展》,載《老子今注今譯》,商務(wù)印書館 2003 年版)
其二,神。道教哲學(xué)主要用這一詞語(yǔ)指稱神奇玄妙的變化情態(tài)。《周易》用整個(gè)宇宙內(nèi)在的陰陽(yáng)兩種力量的交錯(cuò)作用來(lái)解釋變化的原因,譚峭使用這一概念主要用于描摹萬(wàn)物超越人的理性和感知能力,捉摸不定、難以預(yù)測(cè)的變化特點(diǎn)。
其三,氣。道教哲學(xué)體系中,“氣”是一個(gè)決定理論結(jié)構(gòu)的基礎(chǔ)概念,最初的意義是指空氣、大氣和呼吸之氣,后來(lái)則將其引申為構(gòu)成各種物質(zhì)形體的元素,認(rèn)為整個(gè)宇宙的各種事物由各種不同的元?dú)饨M合而成。《莊子·至樂》便認(rèn)為世界上的各種物體都由氣構(gòu)成,氣聚則物生,氣散則物亡。生命的產(chǎn)生和維持都是依賴“氣”而實(shí)現(xiàn)的,氣是所有生命活動(dòng)的動(dòng)力和源泉所在。從氣的功能( 氣機(jī)) 意義來(lái)看,相當(dāng)于現(xiàn)代“信息”概念,即在機(jī)體的各種功能程序過程中作為主體存在的那種東西。( 楊玉輝: 《道教養(yǎng)生學(xué)》,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版)
其四,形。中國(guó)道家和道教哲學(xué)把有形狀、可通過人的感覺和理性感知和把握的物體,稱之為器或者器物。在一般意義上,形指形體,看得見、摸得著、有形有狀的形體。《周易·系辭上》謂: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 二) “化”的本體規(guī)定
譚峭指出: “太上者,虛無(wú)之神也。”( 《化書· 道化·神道》) 世界存在的虛無(wú)性以及變化情態(tài)的神妙性處于絕對(duì)的第一性根本地位。虛神氣形,融為一體。“命之則四,根之則一。”( 《化書· 道化·正一》) 正是這一根本的形而上力量及統(tǒng)攝作用,塑造了現(xiàn)實(shí)事物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多元性和多樣化。“化”作為本體依據(jù)表現(xiàn)出兩方面的特點(diǎn):
第一,遍在統(tǒng)攝。《化書·道化·老楓》載: “虛無(wú)所不至,神無(wú)所不通,氣無(wú)所不同,形無(wú)所不類。”這一特點(diǎn)還是道的另一種表現(xiàn),因由道的運(yùn)化作用和虛無(wú)、神妙、元?dú)狻⑿钨|(zhì)的連通和轉(zhuǎn)化,最終塑造了現(xiàn)象世界“彼我合一,萬(wàn)物一物,萬(wàn)神一神”的統(tǒng)一性和完整性。第二,有無(wú)相通。譚峭言: “龍化虎變,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wú)也; 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有無(wú)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化非終。”( 《化書·道化·龍虎》) 作為本體界的空虛與作為現(xiàn)象界的變化,各自均表現(xiàn)出有與無(wú)辯證統(tǒng)一的融合性,且在起始、終結(jié)與變化的各階段進(jìn)行著有與無(wú)的相互轉(zhuǎn)化。
( 三) “化”的存在表征
針對(duì)多元事物在現(xiàn)象層面表現(xiàn)出的多樣變化,譚峭首先強(qiáng)調(diào)了變化的絕對(duì)性: 屈曲之蛇化為蹣跚之龜,飛鳴之雀化為介甲之蛤,事物與事物之間的變化神妙莫測(cè),難以限定,有情之生命與無(wú)情之非生命體能夠發(fā)生遷變和轉(zhuǎn)化。接著譚峭指出事物在多樣變化之間呈現(xiàn)自身的性質(zhì),并非固定不變,而具有一定的相對(duì)性,物無(wú)常性,人無(wú)常心。他舉例說(shuō): “梟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我之晝夜,彼之晝夜,則是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為大人乎。” ( 《化書·道化·梟雞》) 晝夜昏明的界定基于一定的標(biāo)準(zhǔn),標(biāo)準(zhǔn)不一樣,比較的結(jié)果自然不同,而只有真正徹悟大道才能超越彼此的分界而統(tǒng)觀世界整體。最后,譚峭認(rèn)為萬(wàn)物之間具有感應(yīng)性,這種感應(yīng)可以在不同性質(zhì)甚至有生命與無(wú)生命之間進(jìn)行,是萬(wàn)物變化情態(tài)的另一種表現(xiàn)及其動(dòng)力所在。無(wú)始無(wú)終、遍納萬(wàn)物的虛空至道含藏了萬(wàn)物的“聲氣形相”,至大至小的事物及其細(xì)微變化均能夠被道融攝感應(yīng)。
( 四) 化的循環(huán)往復(fù)
在《化書》的理論體系中,虛是世界的本源,萬(wàn)物由虛化生,又化還為虛。這種虛、形互化,乃是道的根本屬性和存在形式。前一個(gè)虛是道順而生物的過程,后一個(gè)是物逆向而還原于虛的過程。這種循環(huán)往復(fù)的變化觀與老子《道德經(jīng)》“反 ( 返) 者道之動(dòng)”的圜動(dòng)思想一脈相承。
《化書》虛形互化的道化觀念,成為唐宋以來(lái)道教內(nèi)丹術(shù)的理論基礎(chǔ)。“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即“順而行之生人”; “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即“逆而行之成仙”。人與仙的差別及修煉依據(jù)正在于“道”循環(huán)往復(fù)運(yùn)動(dòng)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的既對(duì)立又統(tǒng)一的不同變化方向和路徑。修道者“忘形以養(yǎng)氣,忘氣以養(yǎng)神,忘神以養(yǎng)虛”,被概括為“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的三段式煉養(yǎng)術(shù)。由道至神,突破人的生死變化而又重新回復(fù)生命的原始?xì)庀ⅲ㈤_始另一階段由神向仙轉(zhuǎn)化,這一思想顯而易見本于《化書》又有新的發(fā)揮。
二、道化視野下形神的固陋與缺欠
《化書》在哲學(xué)本體論上對(duì)道化內(nèi)涵作了探討之后,又將變化的視野轉(zhuǎn)向人自身,用相當(dāng)篇幅討論了形神關(guān)系、人的主觀能動(dòng)性及修道追求等問題,秉承了道教哲學(xué)與道同體及無(wú)為自化的觀念,并將“化”的思考灌注到人生哲學(xué)之中,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人自身所表現(xiàn)出的種種由有限所帶來(lái)的固陋與缺欠。
第一,意識(shí)固執(zhí)。原本與世界本身融合為一的形體與精神,當(dāng)思想意識(shí)活動(dòng)越出自身對(duì)整個(gè)世界及自我本身進(jìn)行認(rèn)識(shí)的時(shí)候,卻無(wú)法避免認(rèn)識(shí)先天所具有的局限性,往往所見非全,所知非實(shí),“且夫當(dāng)空?qǐng)F(tuán)塊,見塊而不見空; 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形無(wú)妨而人自妨之,物無(wú)滯而人自滯之。”( 《化書·道化·蛇雀》)
第二,形體滯礙。自老莊以來(lái),超越肉身限制和現(xiàn)實(shí)束縛的絕對(duì)自由成為道教哲學(xué)一以貫之的主題,這一精神向往卻透視出了作為肉身形體在構(gòu)造和運(yùn)化過程所必然具有的形體滯礙性。 “跰趾可以割,陷吻可以補(bǔ),則是耳目可以妄設(shè),形容可以偽置,既假又假,既惑又惑。所以知魂魄魅我,血?dú)庾砦遥吒[囚我,五根役我。惟神之有形,由形之有疣。”( 《化書·道化·耳目》) 無(wú)論是形質(zhì)性的肉身還是精神性的魂魄靈命都在役使和戕害著人身。
第三,見識(shí)短淺。老子認(rèn)為局限于感官知覺難以達(dá)到對(duì)天道的認(rèn)識(shí),認(rèn)為“其出彌遠(yuǎn),其知彌少”。在道教哲學(xué)認(rèn)識(shí)論的觀念里,感性認(rèn)知往往妨礙著對(duì)真實(shí)世界的領(lǐng)會(huì),這是深置于人性之中的短淺見識(shí)。《化書》同樣有感于此。譚峭指出,“觀傀儡之假而不自疑,嗟朋友之逝而不自悲。”( 《化書·術(shù)化·海魚》) 濫用短淺認(rèn)知最終將招致自然天道的懲罰,最為可悲還在于: “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弊,勇者多死。”( 《化書· 仁化·海魚》)
第四,逐利厚身。道家傳統(tǒng)一向視名利為累身擾神、阻斷精神清寧和灑脫的障礙。《化書· 德化·飛蛾》論及此道: “營(yíng)營(yíng)然若飛蛾之投夜?fàn)T,蒼蠅之觸曉窗,知往而不知返,知進(jìn)而不知退,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逐利厚身的心理導(dǎo)致了在他人面前刻意凸顯自身存在的價(jià)值,博求萬(wàn)物,自取其亡。
三、生命安頓的體道境界
在變化的整體視域下,作為生命活動(dòng)的真實(shí)尺度,《化書》針對(duì)人在形神方面所固有的局限和欠缺,提出了變化過程中人與道合二為一的終極體道境界。譚峭指出修道成真的根本就在于窮源達(dá)道,煉養(yǎng)形神,洞明生死,藏精含虛。“是以古圣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yǎng)氣,忘氣以養(yǎng)神,忘神以養(yǎng)虛……真氣熏蒸而時(shí)無(wú)寒暑,純陽(yáng)流注而民無(wú)死生,是謂神化之道者也。” ( 《化書·道化》) 修道者已經(jīng)超越了生死界限,人身的生命氣息已經(jīng)與宇宙本身的虛化真氣融為一體,個(gè)體的生命局限因受真氣的攝受和依托已經(jīng)超越自身有限,而與絕對(duì)無(wú)限的真實(shí)世界建立了永恒而穩(wěn)固的聯(lián)系。在這一修道路徑的指引下,譚峭又具體論述了性命修道的各種境界。
( 1) 齊同萬(wàn)物。修道的最高境界即: “有無(wú)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化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 斃,神 不 可 得 逝。”( 《化 書 · 道 化 · 龍虎》) 這是《莊子·大宗師》“離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坐忘無(wú)我思想的進(jìn)一步發(fā)揮。泯同有無(wú)、齊合生死、順化情性、幽徹內(nèi)外之體道之人,便能夠“大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符至真,融其氣以生萬(wàn)物,和其神以接兆民”。“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 之 混 同,若 一 聲 之 哀 樂,若 一 形 之 窮 通。” ( 《化書·道化·神交》)
( 2) 心無(wú)執(zhí)礙。既然萬(wàn)物的運(yùn)動(dòng)變化基于自身內(nèi)部矛盾關(guān)系而無(wú)需外力干預(yù),呈現(xiàn)出一種自為自化的情態(tài),那么作為自然事物其中一類的人自身,其循道修行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心無(wú)系念,湛然洞明。《化書·仁化·書道》以書法具體解釋了這一境界: “神之所浴,氣之所沐。是故點(diǎn)策蓄血?dú)猓櫯魏樾裕瑹o(wú)筆墨之跡,無(wú)機(jī)智之狀,無(wú)剛?cè)嶂荩瑹o(wú)馳騁之象。若黃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fēng)穆穆然。”書法的絕妙正在于手筆俱忘、神氣飄灑,揮運(yùn)無(wú)跡,自有一種無(wú)心渾化氣象。
( 3) 清靜隨化。“清靜”概念在老子道論體系中用以說(shuō)明“道”自然運(yùn)化、清明寧?kù)o的本然狀態(tài),對(duì)應(yīng)于人心。《老子》十五章指出: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孰能安以動(dòng)之徐生?”清靜成為在混沌變化世界中獲得持久生命的根本原則。譚峭則認(rèn)為: “唯清靜者,物不能欺。”( 《化書·道化· 環(huán)舞》) 站在道教哲學(xué)清靜隨化的角度,個(gè)人修養(yǎng)應(yīng)“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然后牧之以清靜,棲 之 以 杳 冥,使 混 我 神 氣,符 我 心 靈” ( 《化書·德化·五常》) 。
四、結(jié)語(yǔ)
以上簡(jiǎn)要考察了《化書》的道化本體論、形神觀念與體道境界,《化書》所提出的“道化”理論的思維方式和身心修煉思想是不斷鞭策和啟發(fā)現(xiàn)代性命安頓的主要思想資源之一,我們所能做的首先不是去證明《化書》所論不符合現(xiàn)代科學(xué)理論,而是更多地尋求《化書》與現(xiàn)代科學(xué)相符的思想內(nèi)容,并在哲學(xué)思維與性命圓融的意義上更為透徹深入地領(lǐng)會(huì)其思想的永恒價(jià)值。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