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建筑是凝固的音樂”是一句常被人提及的比喻,古往今來,不乏有學(xué)者對建筑與音樂的關(guān)聯(lián)性進(jìn)行研究與探討。該文從建筑創(chuàng)作的角度來思考兩種藝術(shù)的關(guān)聯(lián)性,從畢達(dá)哥拉斯的和聲比例理論到當(dāng)今的數(shù)字化設(shè)計(jì),通過對部分實(shí)踐案例的批判性思考,得出兩種藝術(shù)的轉(zhuǎn)譯應(yīng)該是構(gòu)造層面的有機(jī)轉(zhuǎn)化,而非藝術(shù)作品的二次表達(dá)。在聯(lián)覺心理學(xué)的基礎(chǔ)上,提出可行的轉(zhuǎn)譯方法,使得兩種藝術(shù)的類比實(shí)踐不停留在文學(xué)比喻的層面,對未來音樂—建筑的“跨界”設(shè)計(jì)提供了新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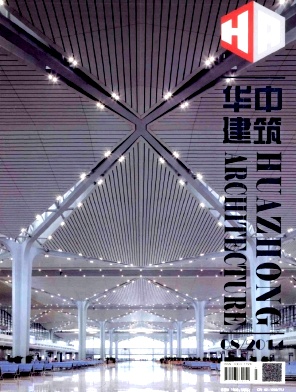
本文源自華中建筑 發(fā)表時間:2021-03-10《華中建筑》(月刊)創(chuàng)刊于1983年,是湖北省人民政府國有資產(chǎn)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主管,中南建筑設(shè)計(jì)院和湖北省土木建筑學(xué)會主辦,系大型綜合性建筑學(xué)術(shù)期刊,其宗旨在于:在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diǎn)的基本路線指引下,發(fā)掘發(fā)揚(yáng)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建筑文化遺產(chǎn),傳播交流我國的建筑設(shè)計(jì)創(chuàng)作、科研、教學(xué)及建設(shè)成就,為探索中國建筑發(fā)展的道路,促進(jìn)中國新建筑流派的孕育成長和豐實(shí),推進(jìn)中國新建筑文化的開拓和發(fā)展而努力。
關(guān)鍵詞 建筑 音樂 轉(zhuǎn)譯
1 背景介紹
音樂與建筑的類比是常被學(xué)者們提到的話題,相比建筑而言,音樂的表現(xiàn)形式更抽象,表現(xiàn)內(nèi)容更自由。正如瓦西里·康定斯基所說: “除極少數(shù)例外,長期以來,音樂從不以復(fù)制自然現(xiàn)象為己任,而是力圖表達(dá)藝術(shù)家的心聲,力圖為樂音本身創(chuàng)造自是自治的生命。”[1]所以從建筑創(chuàng)作的角度,對這兩種藝術(shù)的類比研究,其目的是為了借鑒音樂這一形式藝術(shù)的表現(xiàn)手法來豐富建筑自身的創(chuàng)作。
“建筑是凝固的音樂”也是人們熟知的用于探討建筑音樂相關(guān)性的名言,該比喻是 19世紀(jì)初德國浪漫派的集體產(chǎn)物[2]。這句話從美學(xué)維度上對兩種藝術(shù)建立了比喻化的聯(lián)系,然而探索它們的轉(zhuǎn)譯方法則需挖掘兩者更深層次的構(gòu)造聯(lián)系。
2 不同時期轉(zhuǎn)譯方法的批判性思考
2.1 經(jīng)典和聲比例法則的爭論
早期對于音樂建筑的轉(zhuǎn)譯實(shí)踐可以追溯到畢達(dá)哥拉斯學(xué)派,他們將琴弦兩端固定,通過調(diào)整琴弦比例來進(jìn)行實(shí)驗(yàn)[3]。發(fā)現(xiàn)弦長比例是1:2、3:2和4:3的兩個音組合會發(fā)出和諧的聲音。從現(xiàn)代樂理來說,音程可以理解為音與音的距離,弦長比1:2對應(yīng)的音程為8度,弦長比3:2和4:3對應(yīng)的音程為純四度和純五度,它們聽起來都是悅耳融合,屬于協(xié)和音程[4]。
當(dāng)時的人們對于這一成果感到興奮,認(rèn)為發(fā)現(xiàn)了宇宙和諧的奧秘,后人便開始將這部分比例發(fā)展成一系列的數(shù)列。像阿爾伯蒂、帕拉迪奧等著名的文藝復(fù)興時期的大師們,不管在理論著作還是實(shí)踐案例里都涉及了這些協(xié)和音程所形成的比例。
這種對和聲比例法則的追求直到17、18 世紀(jì)才開始出現(xiàn)大量批判的聲音。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佩勞的言論,他反對音樂和聲與視覺比例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并聲稱比例遵循的“建筑規(guī)則”之所以和諧,沒有其他原因,僅僅是因?yàn)槲覀兞?xí)慣了他們而已[5]。如今部分學(xué)者再談?wù)撘舫毯椭C時,認(rèn)為音與音的和諧其實(shí)與兩個音的頻率比和我們感知他們的方式有關(guān)系。比如當(dāng)兩個音的頻率比是某些簡單分?jǐn)?shù)時(例如3:2,5:4),這些音的組合聽起來是和諧的。當(dāng)兩個音的頻率比接近這些分?jǐn)?shù)但又不精確時,就會產(chǎn)生不和諧的聽覺效果;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和諧的音程與聽者的文化地域也有關(guān)系,比如讓一個歐洲人去聽阿拉伯的音樂也會覺得不適應(yīng)[6]。
2.2 經(jīng)院哲學(xué)背景下的統(tǒng)一與秩序
然而在西方歷史上,建筑與音樂的關(guān)聯(lián)卻不僅限于數(shù)字比例這一方面。從12世紀(jì)30、 40年代至1270年這個時間段里,在巴黎周圍 100英里的范圍內(nèi),哥特教堂與宗教音樂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高度一致性。當(dāng)時的法國鞏固了王權(quán),逐漸消滅了封建割據(jù),社會體制經(jīng)歷了全面的變革。在這種背景下,隨著自然科學(xué)、人文學(xué)科的不斷發(fā)展,人的心理感受開始受到重視。人們從絕對的信仰思維里掙脫出來,開始思考理性判斷與虔誠信仰的關(guān)系。當(dāng)時興盛的經(jīng)院哲學(xué)則將兩者結(jié)合在了一起,借助理性的原則來“解釋”宗教信仰,喚起眾人的感知能力,使得更多人相信宗教[7]。而經(jīng)院哲學(xué)所提倡的理性原則為當(dāng)時的建筑、音樂、文學(xué)等藝術(shù)發(fā)展指明了路徑。
在哥特之前的羅曼式教堂結(jié)構(gòu)體系是十分雜亂的,同一座建筑常出現(xiàn)交叉拱、肋拱、圓筒形拱、穹頂?shù)榷鄠€元素[7],但到了哥特時期,整個教堂的結(jié)構(gòu)系統(tǒng)由一個個基本單元,有序排列組合而成。以沙特爾大教堂為例(圖2),整個平面結(jié)構(gòu)體系都由同源的四分肋拱組成,比起單獨(dú)的肋拱,連續(xù)的肋拱相互之間也形成了結(jié)構(gòu)平衡體系。所以這種邏輯清晰的形式不僅反映在視覺層面,也反映在結(jié)構(gòu)傳力層面。這也印證了經(jīng)院哲學(xué)所提倡的系統(tǒng)性,即“同樣層次的部分,部分中的部分,統(tǒng)統(tǒng)按照其所在層次,來排列組合出一個完整的體系”[7]。
同時期的音樂發(fā)展也出現(xiàn)了巨大的變革,迪斯康特這種宗教音樂首次引入了節(jié)奏模式的概念。在此之前的宗教音樂,都缺乏一種基本的時間單位,整個音樂節(jié)奏相對松散。隨著節(jié)奏模式的引入,迪斯康特建立在六種基本的節(jié)奏型上(圖3),而這六種節(jié)奏型是由長短兩種基本音符組成,它使得各聲部音樂線條能彼此協(xié)調(diào)起來。13世紀(jì)中期,經(jīng)文歌更是突破了固有的節(jié)奏模式,其音樂中不僅包含長音符、短音符還包括時值更短的小音符,這些在現(xiàn)代記譜中被譯作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8](圖4)。節(jié)拍的明確讓音樂對時間的管理更加嚴(yán)格理性,使得音與音之間的對位更清晰,也推動了音樂的發(fā)展,這也體現(xiàn)了經(jīng)院哲學(xué)追求清晰的系統(tǒng)性原則。
在這段歷史時期里,建筑和音樂都有著從混亂狀態(tài)到井井有條的經(jīng)歷,如今很難考證它們是否存在相互借鑒的情況,但也可將其看作是兩種藝術(shù)對當(dāng)時經(jīng)院哲學(xué)的體現(xiàn)。其最大的啟示在于建筑和音樂的轉(zhuǎn)譯不能只停留在數(shù)字轉(zhuǎn)化上面,而是需要通過理解轉(zhuǎn)譯對象的思維模式、藝術(shù)手法,運(yùn)用自身的設(shè)計(jì)媒材進(jìn)行獨(dú)立表達(dá),最終得到的結(jié)果將更科學(xué)理性。
2.3 現(xiàn)代曲譜的空間轉(zhuǎn)譯
如今隨著數(shù)字化設(shè)計(jì)手段的成熟,部分建筑師已不滿于音樂中單一特征的靈感借鑒,他們開始嘗試將整首樂曲或某一音樂片段進(jìn)行數(shù)字化、圖像化的處理。企圖建立一種音樂特征與空間特征一一對應(yīng)的關(guān)系,來達(dá)到一種將音樂“翻譯”成建筑空間的目的。
國內(nèi)在這一塊爭議較大的是建筑師王昀對于五線譜與建筑空間的轉(zhuǎn)譯,他在《跨界設(shè)計(jì)建筑與音樂》[9]中提出了一個將音樂作品轉(zhuǎn)譯成住宅空間的方法(圖4)。他認(rèn)為五線譜中音符之間的間距與空間中墻的間距是異質(zhì)同構(gòu)的,所以他利用自己的主觀審美截取了某首樂曲的幾行五線譜,并將其進(jìn)行抽象簡化,然后根據(jù)簡化的圖示發(fā)展成空間形態(tài),最后加入住宅的功能,一個由音樂生成的住宅就形成了(圖5~6)。
國內(nèi)有學(xué)者對這一轉(zhuǎn)譯方法的批判點(diǎn)在于不該將五線譜作為轉(zhuǎn)譯的原始材料,認(rèn)為五線譜只是音樂記譜的方式,音符和連音線只是符號,這種對應(yīng)關(guān)系僅僅是音樂與建筑在圖形上的轉(zhuǎn)化,并沒有觸及到二者之所以美好的本質(zhì)。并提出即使要用五線譜,也應(yīng)該規(guī)范節(jié)奏與音符之間距離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而不是隨意挑一個版本的樂譜拿來生成空間[10]。
事實(shí)上,即使有圖像能科學(xué)地?cái)?shù)字化樂曲里的所有音樂特征,嘗試將其轉(zhuǎn)換成建筑空間也是非常激進(jìn)的。建筑設(shè)計(jì)的目的不是為了表現(xiàn)某一音樂對象,一首樂曲的產(chǎn)生是作曲家內(nèi)心力量和外在自然力量的綜合表達(dá),而建筑的生成也受到場地、功能等諸多要素的限制。所以兩種藝術(shù)形式在本質(zhì)上就存在不可替代的價(jià)值,建筑師向音樂學(xué)習(xí)應(yīng)該去了解讓音樂美好的藝術(shù)手段是什么?它們遵循了什么基本原則?如何將這些原則與建筑設(shè)計(jì)手法相結(jié)合?
3 轉(zhuǎn)譯方法的提出
3.1 聯(lián)覺心理現(xiàn)象
聯(lián)覺是從一種感覺引起另一種感覺的心理活動[11]。我們經(jīng)常看到一種顏色,感覺它非常的溫暖,這事實(shí)上就是聯(lián)覺現(xiàn)象所起的作用。拋開個別特殊的聯(lián)覺現(xiàn)象,我們普遍會受到類似現(xiàn)象的影響,比如我們會覺得高音聽起來更“輕”,低音聽起來更“重”。并且這類感受不會因?yàn)槲覀儌€人經(jīng)驗(yàn)、知識背景不同而變化,它僅僅是停留在感覺層面的心理活動。
中央音樂學(xué)院的周海宏教授曾在其論文《音樂與其表現(xiàn)的世界:對音樂音響與其表現(xiàn)對象之間關(guān)系的心理學(xué)與美學(xué)研究》用心理學(xué)實(shí)證方法證明了與音樂聽覺相關(guān)的6種要素(音高、音強(qiáng)、時間相關(guān)、時間變化率、緊張度、新異性體驗(yàn))與聯(lián)覺對應(yīng)關(guān)系規(guī)律[12],表 1整理歸納了其研究結(jié)論中與空間知覺相關(guān)的聲音要素的聯(lián)覺現(xiàn)象。
盡管上述對應(yīng)關(guān)系僅僅是從聲學(xué)要素中提取對象,音樂的表現(xiàn)是一個綜合的過程。但音樂的表現(xiàn)源于這些聽覺要素,部分的性質(zhì)一定會對總體的狀態(tài)起到作用,聯(lián)覺現(xiàn)象的提出是音樂轉(zhuǎn)譯建筑的理性基礎(chǔ)。
3.2 轉(zhuǎn)譯原則
音樂轉(zhuǎn)譯建筑的方法其實(shí)應(yīng)該發(fā)展成一種構(gòu)造層面的類比研究,這種類比方法應(yīng)該拋棄音樂作品作為轉(zhuǎn)譯材料,而是試圖抽取兩種藝術(shù)的基本特征,并使它們之間能夠得出有用的類比,最后通過這一方法使得一般音樂的美好特征能夠被構(gòu)建到建筑設(shè)計(jì)中。瓦西里·康定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嘗試了音樂類比,并認(rèn)識到這種方法的優(yōu)點(diǎn)和局限性: “在不同藝術(shù)門類之間藝術(shù)手法的比較和借鑒是切實(shí)可行的,但必須從根本入手。一門藝術(shù)必須弄懂另一門藝術(shù)如何運(yùn)用藝術(shù)手法,然后借鑒同樣的基本原則去運(yùn)用自身的藝術(shù)手法,所不同的是它需要使用專屬于自己的媒材去表達(dá)。”[1]
3.3 激發(fā)空間的運(yùn)動感知
已經(jīng)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建筑與音樂的潛在差異在于:建筑是空間的藝術(shù),而音樂是時間的藝術(shù)。當(dāng)我們在建筑空間里移動的時候,我們也會因時間的不同,來感受不同的空間,所以空間與時間最重要的連接點(diǎn)就是運(yùn)動。將建筑空間音樂化的重要原則就是激發(fā)建筑體驗(yàn)中的運(yùn)動感知。而建筑體驗(yàn)的變化可以在建筑中通過精心設(shè)計(jì)的空間進(jìn)程來創(chuàng)造,這些空間可以在尺度、形式、材料上有所不同。
在現(xiàn)代,這種方法的著名案例是由雕塑家邁克爾·海登和建筑師赫爾穆特·雅恩設(shè)計(jì)的芝加哥聯(lián)合航空公司航站樓的人行隧道(圖7),在這個空間里它不僅有變化的燈光和明亮的墻壁。所有的霓虹燈裝置都是設(shè)計(jì)師精心編排的,當(dāng)游客站在傳送帶時,觀察者的視覺感知是按時間順序被精確控制的,這就類似于音樂曲式結(jié)構(gòu)的起承轉(zhuǎn)合一樣。盡管這種精心編排的線性空間在普通建筑中很難實(shí)現(xiàn),但依然可以在一些引導(dǎo)性空間(比如入口,廊道等),通過強(qiáng)調(diào)形式,光線,材料等變化來模擬音樂中的特征變化,從而豐富建筑空間的體驗(yàn)。比如鹿野苑石刻博物館在入口空間序列的營造上(圖8),通過逐步抬升的條形青石使得游客穿過竹林看到建筑,這種脫離尋常的體驗(yàn)也制造了一種儀式感,為之后的空間埋下伏筆。
3.4 抽象簡化特征
在轉(zhuǎn)譯過程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對音樂特征的提取和與建筑設(shè)計(jì)手法的類比。然而音樂特征是非常繁雜的,如頻率、振幅、音色、音調(diào)、音高、音長、和弦、速度、節(jié)拍、旋律等, 以及近來在音樂可視化領(lǐng)域提出的一些音樂物理特性,如能量、過零率、頻譜矩、頻譜流、帶寬、帶周期等[13]。建筑師面對如此多特征的提取和類比是耗時耗力的,也是沒有必要的。因此針對建筑設(shè)計(jì)的需要,僅需提取個別音樂特征進(jìn)行類比研究,使得最后結(jié)果變得簡單也使人容易理解。
比如在《建筑空間組合論》一書中所提到的形式美法則——韻律與節(jié)奏[14],就是對音樂某一具體特征進(jìn)行的轉(zhuǎn)譯。韻律在音樂與詩歌中是表明音調(diào)的起伏和節(jié)奏感[14]。在一段音樂作品中,節(jié)拍數(shù)量超過64拍就會使人變得難以理解,所以音樂家們會把類似于歌劇、交響樂這一類音樂作品分隔成獨(dú)立優(yōu)美的部分。同樣我們要記住一組超過15個不相關(guān)的元素或單詞時也是非常困難的[15]。所以在音樂和詩歌作品里面,我們會有重拍和弱拍,也會有重復(fù)的形式或主題,使得整個作品結(jié)構(gòu)變得簡化可理解。因此,建筑設(shè)計(jì)過程中也應(yīng)該利用韻律與節(jié)奏這種音樂特征,避免最后的作品變得雜亂無章。
20世紀(jì)60年代,道格拉斯·哈斯克爾對國際主義風(fēng)格的一致性曾提出,應(yīng)該從爵士樂的切分節(jié)奏中尋找靈感,拒絕規(guī)律的開窗和結(jié)構(gòu)并主動探索那些不和諧的比例。而他的行動呼吁在20世紀(jì)90年代動態(tài)和解構(gòu)形式的建筑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這種節(jié)奏韻律轉(zhuǎn)譯立面的另一個著名案例就是柯布西耶的拉圖雷特修道院。要知道音樂的節(jié)奏韻律是隨著時間推進(jìn)而產(chǎn)生變化作者信息:劉建辰,重慶大學(xué)建筑城規(guī)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 452173706@qq.com 的,而柯布西耶一直致力于創(chuàng)造一種“散步的空間”,這與音樂的運(yùn)動性不謀而合。當(dāng)時他身邊正好有一位具備工程師和作曲家雙重背景的助手——埃阿尼斯·塞納基斯[16]。塞納基斯利用調(diào)整橫豎向窗欞間隔來處理立面開窗(圖9),這些不等距的窗欞間隔就類似音的長短組合,使得整個立面優(yōu)美流暢。但這種手法運(yùn)用卻不止于立面的靜態(tài)轉(zhuǎn)譯,在修道院的外廊空間中(圖10),經(jīng)陽光的照射,光影的對比更是放大了這種實(shí)體節(jié)奏,將二維平面上的節(jié)奏轉(zhuǎn)化到了三維空間之中。當(dāng)人在這種空間走過,感受到的不再是“凝固的音樂”,而是“流動的音樂”。
結(jié)語
音樂與建筑的類比研究有著悠久的歷史,每一代建筑師出于各種因素的影響給出了自己的分析方法與轉(zhuǎn)譯手段。當(dāng)下“跨界”設(shè)計(jì)的盛行,相信還會有更多的建筑師從音樂中吸取靈感。本文后半部分在闡述轉(zhuǎn)譯方法時,并沒有將音樂特征與建筑特征進(jìn)行一一類比,而僅僅闡述了轉(zhuǎn)譯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原則。其原因也是這兩門藝術(shù)學(xué)科的特征轉(zhuǎn)譯是不存在客觀聯(lián)系的,它一定是基于建筑師的主觀審美和藝術(shù)創(chuàng)造力。但是在轉(zhuǎn)譯實(shí)踐上,建筑師也要避免文學(xué)化的比喻,強(qiáng)化音樂表現(xiàn)特征的理解,使得轉(zhuǎn)譯成果能讓大眾真實(shí)感受到。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