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黃河沿岸的河南省孟津縣為例,從利用狀況與坡度分布、景觀格局與空間鄰接、耕作距離與道路通達、經濟梯度與生態安全等方面,對孟津縣“非糧化”耕地的形態特征進行了系統識別。結果表明:孟津縣耕地的“非糧化”空間與優質農業生產空間高度重疊,耕地的非食物化利用傾向明顯,耕地向林地調整的比重過大;由于糧作耕地和非糧作耕地在勞動生產率上存在較大的差異,導致種植經濟型作物的耕地規模偏小且較為分散,無法形成規模經濟;高速度的交通工具縮短了農戶的耕作路途時間,耕作距離對耕地“非糧化”的影響力度在下降,交通干線附近分布數量較多的即可恢復地類,與近幾年的“廊道景觀工程”建設密切相關;高經濟梯度區的經濟型撂荒占比較大,偏遠地區農戶對耕地的依賴程度相對較高;生態紅線是維護區域生態安全的剛性底線,在生態紅線之內,應積極實施“再野化”工程。結合新時期國家黃河生態戰略,以建設復合型黃河生態廊道為目標,提出了不同區位、不同類型“非糧化”耕地的恢復調整方案,研究結果可為新時期國土整治工作提供決策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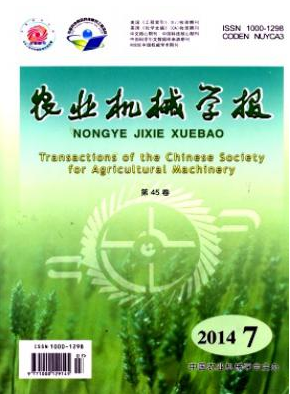
本文源自關小克; 王秀麗; 趙玉領, 農業機械學報 發表時間:2021-07-19
關鍵詞:孟津縣;“非糧化”耕地;形態特征;優化
0 引言
糧食安全是關乎國家發展的全局性、戰略性問題,目前耕地保護與糧食安全的相關議題再度升級[1-2]。耕地作為土地資源的精華部分,是確保食物安全的基礎資源、是促進社會發展的空間載體、是維系生態安全的景觀基質[3-6],針對新時期耕地保護的剛性管控與區域資源空間錯配的現實矛盾,耕地保護研究者圍繞耕地的質量內涵[7-10]、健康產能[11-13]、風險管控 [14-17]等領域開展了重點研究,相關研究對發展新時代的健康農業、支撐健康中國做出了有益探索。近年來,我國農業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區域布局趨于合理,但是部分地區出現了耕地“非糧化”的傾向,一些地方把農業結構調整簡單理解為壓減糧食生產,一些經營主體違規在基本農田上種樹、挖塘,一些工商資本流轉耕地改種非糧食作物等,以功能衰退為表征,不少地方的耕地利用呈現出“邊際化”、“撂荒”等不良趨勢[18-20],耕地“非糧化”的無序發展,必然會影響到國家糧食安全[21-25]。《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防止耕地“非糧化”穩定糧食生產的意見》明確提出:把穩定糧食生產作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前提,必須將有限的耕地資源優先用于糧食生產,嚴格控制耕地轉為林地、園地等其他類型農用地。研究者們高度關注耕地“非糧化”利用,張宗毅[26]基于全國 1740 個種植業家庭農場數據,發現非糧作物與糧食作物存在顯著的生產效率差異,土地經營規模較大的樣本更傾向種植糧食作物;羅必良 [27]認為我國農業種植結構調整導致的“非糧化”具有階段性的特征,保障國家糧食安全,需要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和完善農業分工體系;張藕香[28]認為,防止耕地“非糧化”需要加強土地用途管制,疏通農田水利“最后一公里”。相關研究結論對保障糧食安全、維護社會穩定做出了積極貢獻。然而,耕地“非糧化”受市場需求、管理政策、農戶決策、地塊條件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但以往的研究大都是基于統計數據或大樣本的調查數據,對“非糧化”耕地的形態特征識別還不夠深入,不能有效應對耕地精細化管理的現實需要。隨著人口增長、消費升級和資源環境趨緊,我國的糧食產需維持緊平衡的態勢將長期存在,深入研究耕地“非糧化”的影響因素及其空間異質性,提出針對性的管控策略,促使區域耕地利用向“趨糧化” 方向發展,對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化解糧食安全挑戰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孟津縣南部與洛陽市主城區鄰接,在城市擴展過程中,該區域的農業空間不斷被擠占,其易變性強、穩定性差的特征尤為突出;北部與黃河小浪底水庫和西霞院反調節水庫鄰接,是黃河流域生態安全的關鍵核心地段之一,在生態目標優先之下,區域耕地作為空間重構、生態修復的資源載體,其利用形態與格局受到了一定影響。鑒于此,本研究基于國土“三調” 成果,提取“非糧化”耕地的圖斑信息,系統刻畫“非糧化”耕地的空間形態特征,解析耕地“非糧化”利用的主控因素,以提出耕地“趨糧化”利用的調控方案,為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提供決策參考。
1 區域概況與數據來源
1.1 區域概況
孟津縣位于黃土高原東南邊緣,是黃河中游與下游的地理分界處。縣域中西部是黃土丘陵區,區內千溝萬壑、土壤貧瘠,中東部為邙嶺余脈,區內地形起伏較大,土層深厚,縣域東北部是黃河谷地,地勢相對較為平坦。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的初步成果顯示,2019 年全縣國土總面積為 734.77km 2,耕地面積 300.00km 2,約占國土總面積的 40.83%。其中,水澆地面積 101.72 km2,主要分布在縣域中南部及北部的朝陽、送莊、常袋、平樂及會盟等鄉鎮;旱地面積 188.57km2,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城關、橫水、白鶴及小浪底等鄉鎮;水田面積 9.71km2,主要分布在東北部黃河谷地的會盟鎮。
1.2 數據來源與處理
土地利用數據來源于孟津縣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成果;《孟津縣生態紅線劃定成果》(2020),孟津縣 DEM 數據(http:www.resdc.cn);《孟津縣統計年鑒》。
在數據處理方面,結合研究的需要,參照 GB/T 21010-2017《第三次全國土地調查土地分類》和《土地規劃分類》,將研究區土地利用數據歸并為耕地、園地、林地、其他農用地、城鄉建設用地、交通運輸及其他建設用地、自然保留地共 7 類。在 ArcGIS 軟件支持下,轉換成 10m×10m 的柵格數據。
2 研究思路與方法
2.1 研究思路
耕地的利用形態是鄉村地區人地關系的現實反映,伴隨著農戶生計分化和鄉村轉型發展,耕地“非糧化”利用的現象日益凸顯。鑒于此,本研究利用孟津縣第三次國土調查數據,提取縣域“非糧化”耕地的圖斑信息,采用景觀格局分析法、空間鄰接分析法、緩沖區分析法等方法,從利用狀況與坡度分布、景觀格局與空間鄰接、耕作距離與道路通達、經濟梯度與生態安全等視角,系統刻畫“非糧化”耕地的空間異質特征,深入探討耕地“非糧化”利用與相關要素的作用關系,識別出影響耕地“非糧化”利用的主控因素,提出不同類型、不同區域“非糧化”耕地的優化調控方案。
2.2 研究方法
2.2.1“非糧化”耕地提取
“非糧化”耕地是指將用于種植糧食作物的耕地調整為種植經濟作物或者其他非糧食作物的耕地[25]。2019 年底國家下發了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的初步成果,“三調”以精細化國土空間治理為導向,充分滿足了耕地保護和分類管理的現實需要,規定農用地的最小上圖的圖斑面積為 400m2 ,對部分地類進行細化拆分,增加了圖斑屬性注記,全面掌握了耕地的利用狀況,對由產業結構調整而來的園地、林地等地類,增加了工程恢復、即可恢復等屬性標注,系統掌握了耕地儲備資源的基本情況[29]。“三調”成果顯示,孟津縣耕地包括種植糧食作物、糧與非糧輪作、糧林間作、種植非糧食作物、未耕種等 5 種利用形態。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中的“非糧化”耕地主要由兩部分組成:①從“三調”中提取地類名稱為耕地,種植屬性為“未耕種”、“種植非糧食作物”的地類圖斑;②從“三調”中提取地類名稱為園地、林地或其他農用地,種植屬性標注為“工程恢復”、“即可恢復”等的可調整地類圖斑。
2.2.2 景觀格局分析法
耕地的景觀格局指數是耕地空間格局信息的高度濃縮,能夠有效反映耕地資源的結構組成和空間形態特征 [30-31],將分析地類以 10m×10m 的柵格化處理后,在景觀格局分析軟件 Fragstats4.2 支持下,分別計算不同利用模式下耕地的景觀格局特征。
2.2.3 空間鄰接分析法
斑塊的功能、結構與其空間鄰接的斑塊類型有著密切關系[32],通過分析對象斑塊的空間鄰接特征可有效診斷出對象斑塊利用形態受到的潛在風險或受周邊用地類型的影響程度 [33-34]。通過對“非糧化”耕地斑塊和全域圖斑的緩沖和疊加運算,可獲取“非糧化”耕地斑塊的空間鄰接特征。
3“非糧化”耕地的形態特征分析
3.1 利用狀況與坡度分布
3.1.1“非糧化”耕地的利用狀況
當前,人們的膳食結構呈現出主糧降低、類型多樣的演化態勢,加上種糧效益低、農村勞動力短缺,在多重要素的疊加之下我國耕地“非糧化”的現象愈演愈烈。截至 2019 年底,孟津縣“非糧化”的土地面積為 17637.09hm2,約占全縣國土面積的 24.00%。在地類構成上, “非糧化”的耕地面積為 2854.04hm2,約占全縣國土面積的 3.88%;可調整地類面積為 14783.05hm2,約占全縣國土面積的 20.12%,可調整地類中,園地、林地、其他農用地面積分別為 5080.07、8792.46、910.52hm2,如表 1 所示。
從分布區域來看,未耕種的土地面積為 717.38hm2,主要分布在麻屯、朝陽、平樂等南部鄉鎮,如圖 1 所示,其中,未耕種的水澆地、水田等高質量耕地面積占未耕種耕地面積的 34.19%,在城鎮擴張、優質耕地不斷減少的時代背景下,高質量耕地被撂荒是需要關注的重點;種植非糧食作物的耕地面積為 2136.66hm2,主要分布在麻屯、送莊、白鶴東部、會盟西部等優質耕地集中區,優質耕地具有多用途適宜性,既適合耕作利用也適宜花卉、苗木、藥材等特色經濟作物種植,因此,在種植非糧食作物的地類中,水澆地、水田等優質耕地面積為 1032.41hm2,占種植非糧食作物土地面積的 48.32%;即可恢復的地類面積為 7006.90hm2,整體上,即可恢復地類的耕作層沒有受到破壞,調整恢復為耕地的難度較小,主要分布在城關、朝陽、平樂和會盟等鄉鎮,其中,即可恢復的園地面積為 3225.39hm2,即可恢復的林地面積為 3685.07hm2,即可恢復的其他農用地面積為 96.44 hm2,在即可恢復的地類中,林地占比最大,占比為 52.59%;工程恢復的地類面積為 7776.15hm2,該類型需要采取一定的工程措施才能恢復調整為耕地,主要分布白鶴、送莊、橫水西部,該區地形起伏相對較大,主要以林地為主,林地面積約占工程恢復地類面積的 65.68%。綜上分析,孟津縣優質耕地的 “非糧化”比重偏高,且“非糧化”耕地向林地調整的比重過大,如不對耕地“非食物化” 傾向進行有效管控,必然會對糧食安全生產造成一定沖擊。
3.1.2“非糧化”耕地的坡度分布特征
坡度相對穩定且不易改變是影響耕地質量的一項重要指標,作為典型的黃土溝壑區,孟津縣大于 15 º的坡耕地有 1620.42hm2,其中,未耕種與種植非糧食作物的耕地面積為167.32 hm2,調整為其他地類(工程恢復、即可恢復)的面積為 91.36hm2,大于 15 º坡耕地的非糧化率合計為 15.96%。在生態文明優先下,有序推動坡耕地的退耕還林(園),有助于降低水土流失、提高農業綜合效益、促進良性生態空間的形成,但是,由于缺乏系統的規劃和引導,孟津縣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基本上處于散亂、自發狀態,且主要分布在平原及緩坡地帶,由表 2 可知,0º~15º是“非糧化”耕地分布較為集中的區間,該區域共有 17378.41hm2 被“非糧化”利用,約占全部“非糧化”地類的 98.53%,0º~6º孟津縣優質耕地分布的核心地帶,該區域非糧化耕地面積占全縣非糧化耕地的 77.11%,非糧化空間與優質農業生產空間的高度重疊,給耕地保護帶來巨大壓力。
3.2 景觀格局與空間鄰接
3.2.1“非糧化”耕地的景觀格局特征
不同利用模式的耕地在空間結構、分布形態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景觀格局指數能夠有效反映耕地利用形態的細部差異。運用 Fragstat4.2 軟件計算不同利用模式耕地的景觀格局指數,選取斑塊個數(NP)和平均斑塊面積(AREA-MN)表征斑塊的規模狀況;用斑塊平均最近距離(ENN-MN)和聚集度指數(AI)表征斑塊破碎程度。由表 3 可以看出,未耕種的耕地斑塊個數最少,且分布較為離散,導致斑塊平均最近距離(ENN-MN)最大;種植非糧食作物和糧作耕地在勞動生產率上存在較大的差異,農戶可以通過機械化實現對糧作耕地的規模化管理,但是對蔬菜、花卉、苗木、中草藥等勞動力消耗大的經濟作物卻無法實現規模化耕種,因此,糧作耕地的平均斑塊面積(AREA-MN)最大,約為種植非糧食作物耕地規模的 6.9 倍;同理,聚集度指數(AI)也是種植非糧食作物耕地的最小,糧作耕地的聚集程度最高;即可恢復和工程恢復類型,在景觀格局指數的相似度較高,整體上來看,即可恢復的聚集度指數(AI)和平均斑塊面積(AREA-MN)略大于工程恢復地類,這與即可恢復地類中的園地比重大有較大的關系,因為果園需要一定的規模才能產生經濟效益。
3.2.2“非糧化”耕地的空間鄰接特征
斑塊的空間鄰接特征可從海量空間數據中發掘出空間斑塊之間的空間依賴路徑、相互作用強度以及共生或因果模式[35]。目標斑塊與某種地類的臨接比例越高,說明目標斑塊與該地類間的關聯性越強,假如某種地塊與耕地的鄰接比例高于 50%,表示該地塊大部分被耕地包圍,同時也說明該地塊復墾為耕地具有較高的適宜性。由表 4 可以看出,孟津縣未耕種、種植非糧食作物、即可恢復、工程恢復 4 類的“非糧化”耕地,均與耕地保持著最高程度的空間鄰接,說明孟津縣“非糧化”耕地調整恢復為糧作耕地均有較高的自然適宜性。由表 4 還可以看出,未耕種和種植非糧食作物的地類圖斑與其他農用地和林地鄰接度較高,說明該類型的耕地在“效益引線”不足的情況下,極可能調整為林地或其他農用地;即可恢復和工程恢復地類與其他農用地和城鄉建設用地的鄰接度較高,在農業利用效益持續低迷的情形下,受到建設占用的壓力巨大。
3.3 耕作距離與道路通達
3.3.1“非糧化”耕地的耕作距離特征
農村居民點是農戶的生活居住場所,耕地是農戶重要的生產對象和生產資料,農村居民點與耕地存在一定的空間共生關系[36]。另外,農村居民點與耕作地塊需要保持合理的耕作半徑,耕作半徑受區域自然條件、社會因素、經濟因素以及土地利用因素的影響[37]。在 500m 范圍內,未耕種、種植非糧食作物、即可恢復、工程恢復等占其各自類型總面積的比例分別為:92.69%、90.79%、92.69%、91.66%,即大部分的“非糧化”耕地主要分布在距離村莊較近的區域范圍,而糧作耕地在居民點 500m 緩沖范圍內的面積為 21812.98hm2,約占全部耕地面積的 89.17%,低于所有的“非糧化”耕地,這是由于黃河灘區耕地面積大多是孟津縣的糧食核心產區,灘區耕地普遍距離村莊較遠,但是灘區耕地面積地塊大,規模化經營程度高,產生了一定的規模經濟。另外,隨著摩托車、電動車、農用三輪車等高速度交通工具的普及,縮短了農戶的耕作路途時間,耕作距離對耕地“非糧化”利用的影響力度在下降。
3.3.2“非糧化”耕地的道路通達特征
交通干線作為物質、信息交換的重要廊道,交通干線往往會對沿線土地利用產生較大影響。由表 6 可以看出,在距離交通干線 200m 的范圍內,未耕種的土地面積為 234.25hm2,約占該類型耕地總面積的 32.65%;種植非糧食作物的土地面積為 534.99hm2,約占該類型耕地總面積的 25.04%。由于交通干線附近農戶往往以便利的交通條件為依托,從事非農產業比重較大,農業收入占其家庭收入的比重較低,導致耕地被撂荒、或者被調整為種植非糧食作物(花卉、苗木)的面積較大;在距離交通干線 200m 的區間內,即可恢復和工程恢復面積分別占其類型總面積的 29.64%和 23.22%,其中即可恢復比重高,這與近年來大規模推行的 “廊道景觀工程”建設密切相關;由于糧食生產主要與田間道、村道等生產性道路關系密切,因此,在交通干線 200m 范圍內的糧作耕地面積為 4577.50hm2,僅占該糧作耕地總面積的 18.71%。
3.4 經濟梯度與生態安全
3.4.1“非糧化”耕地經濟梯度特征
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性,導致區域間土地利用呈現出明顯的梯度分異特征,經濟梯度差異決定著農村地域類型的復雜性及發展模式的多樣性。2018 年,全縣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為 13771 元,分別以人均收入的 116.66%(16065 元)、83.33%(11475 元)為分割點,將孟津縣村莊劃分為 3 個經濟梯度空間(圖 2),通過對三次產業從業人員的修正,獲取孟津縣不同經濟梯度區間的耕地“非糧化”特征。在區域資源條件與重大基礎設施沒有明顯改變的情況下,經濟梯度空間格局一旦形成,就容易固化[38]。
孟津縣高經濟梯度區大都位于縣城周邊、臨近洛陽城區的交通干線附近及產業集聚區周邊區域,處于高經濟梯度區的土地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 21.59%,高經濟梯度區的農戶從事非農產業比重較高,以農業勞動力析出為代表的經濟型撂荒正在快速發展,區內未耕種的土地面積為 477.56hm2,占全部未耕種耕地面積的 62.39%(表 7);中經濟梯度區大都遠離城鎮,發展條件一般,中經濟梯度區土地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 57.44%,中經濟梯度區的農戶在資源信息獲取和務工機會等方面,與高經濟梯度區農戶存在顯著差距,但是區內整體的耕作條件較為便利,農戶大多數傾向糧食種植,該區域糧作耕地面積占全部糧作耕地的 61.99%,另外,區內部分農戶在經濟效益的驅動下,將種植結構調整為經濟效益較高的非糧作物,該區域種植非糧食作物的面積為 1271.21hm2,占全部種植非糧食作物面積的 59.50%;低經濟梯度區主要分布在白鶴、小浪底、橫水、常袋等鄉鎮,該區域地形起伏大、地塊零碎,農業生產條件較差,低經濟梯度區土地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 15.64%,由于低經濟梯度區的位置相對較為偏遠,農戶收入來源有限,對耕地的依賴程度相對較高,該區域糧作耕地占全部糧作耕地的比重為 16.42%,高于區域面積占國土面積 15.64%的比重。
3.4.2“非糧化”耕地生態安全特征
黃河在孟津段長度為 59km,并擁有小浪底水庫、西霞院水庫等大型水利樞紐工程,孟津縣是黃河流域生態保護的關鍵節點地帶。生態紅線是維護區域生態安全的剛性底線,孟津縣劃定的生態紅線包括了河南黃河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河南孟津小浪底省級森林自然公園,以及區域內的黃河河道、水庫水面等大型種子斑塊,如圖 3 所示。孟津縣生態紅線主要沿黃河呈帶狀分布、且占國土面積比重較小,因此,落入生態紅線內的“非糧化”耕地僅占“非糧化”耕地總面積的 2.27%,見表 8。
打造“自然風光+黃河文化+慢生活”的復合型黃河生態廊道是推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的戰略舉措,在生態紅線之內,對于 401.28hm2的“非糧化”耕地,要盡量降低人為干擾,積極實施生態化耕種和“再野化”工程,有序實施退耕還濕、還灘,盡力還原自然風光。對于 2025.04hm2的糧作耕地(表 8),要引導農戶進行生態化耕種,對影響黃河生態廊道建設的地塊,要實施有條件的耕作退出;生態紅線 1000m 以內的緩沖區,是生態保護的過渡區,應以黃河流域生態保護為重心,進行適當的生態基礎設施建設,以維持區域生態安全的穩定。
4 不同耕地利用類型的優化調控
雖然孟津縣的“非糧化”耕地調整恢復為耕地具有較高的自然適宜性,但在現有耕地不斷被“邊際化”利用的背景下,如果不加分類、“一刀切”地將“非糧化”耕地恢復調整為耕地,不僅會使政策執行效果大打折扣,而且還會造成反復“折騰”的“過程性”浪費。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日益凸顯的今天,孟津縣“非糧化”耕地的調整利用,要充分對接國家黃河戰略,結合區域的生態紅線、農戶的發展需求、調整的難易程度等,分區、分類實施。
4.1 未耕種耕地的調控
經濟型撂荒是當前孟津縣耕地撂荒的主要原因,確保優質耕地的糧作、糧用是防止耕地 “非糧化”的核心要務。對位于生態紅線內 12.56hm2的未耕種耕地,應順勢引導,按照還原自然風光的建設目標,在保證農戶效益不受損失的基礎上,對生態紅線內的未耕種土地實施生態化耕種或“野化”利用;對位于其他區域的未耕種土地,積極引導土地流轉,通過發展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形式,發展糧食適度規模經營,大力發展代耕代種、土地托管等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提高種糧規模效益。
4.2 種植非糧食作物耕地的調控
在經濟效益的驅使下,部分農戶將糧作耕地調整為種植非糧食作物,但是種植非糧食作物的用工量遠高于糧食作物,從而導致種植非糧食作物耕地的平均斑塊面積偏小,聚集程度偏低,無法產生規模經濟。對于生態紅線內 121.82hm2的種植非糧食作物耕地,應按照生態紅線內的管制規則,引導耕地的生態化耕種,嚴格控制化肥、農藥的使用,按照以水定地的原則,控制農業用水總量,逐步壓縮水稻種植面積;對于生態紅線之外種植非糧食作物的耕地,應進一步完善產業布局規劃,結合非糧作物的類型,引導經濟作物種植的集聚效應,加快丘陵山區農田宜機化改造,支持糧食加工設施建設,延長產業鏈條,實施規模化、品牌化工程,提高糧食經營效益。
4.3 即可恢復地類的調控
即可恢復地類中,由于調整為林地、園地或其他農用地的時間較短,僅需要簡單的處理就能恢復為耕地。對于生態紅線內的即可恢復地類,應最大程度減少人為干擾,有條件引導其“野化”利用。孟津縣的即可恢復地類與交通干線的關系密切,在交通干線 400m 的范圍內分布著 47.83%的即可恢復地類,對待即可恢復地類中的園地,應承認其存在的合理性,對于在基本農田上種樹等“非食物化”的地塊,應及時恢復調整為耕地,防止調整不及時,從即可恢復“成長”為工程恢復。
4.4 工程恢復地類的調控
孟津縣工程恢復地類中,林地占比為 65.68%,且主要分布在小浪底、白鶴西部地形起伏較大的區域,對待工程恢復地類,要盡量維持其現狀,防止不當的工程施工對區域生態環境造成破壞。
5 結論
(1)由于缺乏系統性的規劃和布局,孟津縣的產業結構調整基本處于散亂、自發狀態,在調整過程中,優質耕地的“非糧化”比重偏高,且“非糧化”耕地向林地調整的比重過大。 “非糧化”耕地主要分布在 0~15 º的坡度區間,“非糧化”集中區與優質農業生產區高度重疊;“非糧化”耕地的平均斑塊面積(AREA-MN)、聚集度指數(AI)均小于糧作耕地。從空間鄰接情況來看,孟津縣“非糧化”耕地調整恢復為糧作耕地具有較高的自然適宜性;隨著高速度交通工具在農村的普及,耕作距離對耕地“非糧化”利用的影響力度在下降。交通干線附近的即可恢復地類比重高;以農業勞動力析出為代表的經濟型撂荒在高經濟梯度區分布比重較大,中經濟梯度區農戶傾向糧食種植,低經濟梯度區農戶收入來對耕地的依賴程度相對較高。落入生態紅線內的“非糧化”耕地僅占“非糧化”耕地總面積的 2.27%,對待生態紅線內的“非糧化”耕地,應有序實施退耕還濕、還灘,盡力還原灘區自然風光。
(2)在現有耕地不斷被“邊際化”、“撂荒”利用的背景下,如果“一刀切”地將“非糧化”耕地恢復調整為耕地,容易造成“過程性”浪費。孟津縣“非糧化”耕地的調整利用,要充分對接國家黃河戰略,結合區域的生態紅線、農戶的發展需求、調整的難易程度等,分區、分類實施。在生態紅線之內,應盡量減少人為干擾,積極實施生態化耕種和“再野化” 工程。在生態紅線之外,對于未耕種土地,應積極引導土地流轉,通過發展家庭農場、代耕代種等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提高種糧規模效益;對于種植非糧食作物耕地,要進一步完善產業布局規劃,引導經濟作物種植的集聚效應,加快丘陵山區農田宜機化改造,實施規模化、品牌化工程,進一步糧食經營效益;對于即可恢復中的園地,要承認其存在的合理性,對于在基本農田上種樹等“非食物化”的地類,應及時調整,避免從即可恢復“成長”為工程恢復;對于工程恢復地類,應盡量維持其現狀,防止不當的工程施工對區域生態環境造成破壞。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