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實(shí)踐論》《矛盾論》是毛澤東對(duì)中國(guó)革命歷史經(jīng)驗(yàn)的總結(jié),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guó)革命具體實(shí)際相結(jié)合的哲學(xué)著作,在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理論意義。 歷史虛無(wú)主義者以顯性的可見(jiàn)文本直接比對(duì)的方式,蔑稱《實(shí)踐論》《矛盾論》為國(guó)內(nèi)外哲學(xué)著作的抄襲與翻版,進(jìn)而否定毛澤東及其思想的歷史價(jià)值和意義,此操作方式集中呈現(xiàn)于對(duì)《實(shí)踐論》《矛盾論》的非科學(xué)、非歷史地解讀。 我們需要從根本上揭穿歷史虛無(wú)主義觀點(diǎn)的虛假性、材料使用上的不正當(dāng)性和解讀模式的非科學(xué)性,并在此基礎(chǔ)之上深度透視認(rèn)知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的重要理論價(jià)值及現(xiàn)實(shí)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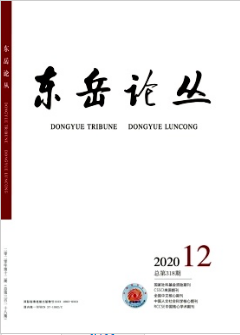
本文源自王曉峰, 東岳論叢 發(fā)表時(shí)間:2021-07-14
[關(guān)鍵詞]毛澤東哲學(xué);癥候閱讀;歷史虛無(wú)主義
《實(shí)踐論》和《矛盾論》(以下簡(jiǎn)稱“兩論”)不僅是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的結(jié)晶,也是毛澤東總結(jié)和闡發(fā)中國(guó)革命的歷史經(jīng)驗(yàn),推動(dòng)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guó)革命具體實(shí)際相結(jié)合的重要理論著作。 “兩論” 的提出,標(biāo)志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集體實(shí)現(xiàn)了從農(nóng)民包圍城市的革命實(shí)踐到以馬克思主義中國(guó)化為核心的理論實(shí)踐的辯證過(guò)程。 然而正是由于“兩論”在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兩論寫(xiě)作背景復(fù)雜性、概念術(shù)語(yǔ)的模糊性和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性等特點(diǎn),學(xué)界關(guān)于兩論歷史地位的評(píng)價(jià)再次出現(xiàn)了爭(zhēng)議①。 “兩論”抄襲說(shuō)、雷同說(shuō)甚囂塵上,成為歷史虛無(wú)主義者定位和評(píng)判“兩論”的核心關(guān)鍵詞。 從根本上來(lái)說(shuō),歷史虛無(wú)主義是教條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變體。 歷史虛無(wú)主義者關(guān)于“兩論”的評(píng)判,同時(shí)也是教條主義主導(dǎo)下的簡(jiǎn)單對(duì)照式閱讀方式對(duì)于“兩論”文本解釋的越界和對(duì)于文本自身歷史性、價(jià)值性維度的遮蔽。 因此,必須要明確閱讀和學(xué)習(xí)“兩論”的方法論和閱讀模式的重要性,借助于癥候閱讀及其與文本直讀辯證結(jié)合的方式,實(shí)現(xiàn)文本自身和文本閱讀過(guò)程中的歷史和邏輯、理論和實(shí)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統(tǒng)一,進(jìn)而重新審視新民主主義革命時(shí)期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所具有的現(xiàn)實(shí)意義與理論價(jià)值,旗幟鮮明地反對(duì)歷史虛無(wú)主義。
一、歷史虛無(wú)主義的基本觀點(diǎn)與態(tài)度
歷史虛無(wú)主義的本質(zhì)是教條主義,具體表現(xiàn)為以“兩論”為核心的簡(jiǎn)單對(duì)照式閱讀模式以及關(guān)于毛澤東本人歷史評(píng)價(jià)的否定性研究模式。 這種以“去政治化”為目的而展開(kāi)的關(guān)于兩論的學(xué)術(shù)研究通常帶有一定的、潛藏著的政治立場(chǎng)與價(jià)值評(píng)判,并在關(guān)于部分爭(zhēng)議文本的解讀過(guò)程中采用一種顯性的、簡(jiǎn)單的、粗糙的文本直接對(duì)比閱讀模式,其目的是將毛澤東的核心哲學(xué)文本定義為對(duì)他人作品的抄襲與翻版,進(jìn)而否定毛澤東本人的人格及其思想的歷史價(jià)值和意義,作出兩論“抄襲改寫(xiě)論”和“雷同翻版論” 的否定性論斷。
(一)歷史虛無(wú)主義的否定對(duì)象:《實(shí)踐論》與《矛盾論》的真實(shí)性
《實(shí)踐論》《矛盾論》的產(chǎn)生具有時(shí)代性和歷史必然性,是毛澤東關(guān)于中國(guó)革命道路與具體實(shí)踐的哲學(xué)思考和深刻總結(jié)。 直接地來(lái)看,“兩論”又是與中國(guó)革命的豐富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①。 第一, 從實(shí)踐上來(lái)看,20 世紀(jì)20 年代到30 年代,中國(guó)社會(huì)主義革命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guó)既無(wú)法像西歐一樣依靠工業(yè)化大生產(chǎn)去培養(yǎng)以生產(chǎn)力為基礎(chǔ)的工業(yè)無(wú)產(chǎn)階級(jí),也無(wú)法像俄國(guó)革命一樣以工業(yè)相對(duì)集中的大城市為基礎(chǔ)進(jìn)行武裝暴動(dòng)去奪取全國(guó)政權(quán)。 第二,從理論上來(lái)看,馬恩的經(jīng)典論斷以及俄國(guó)革命的經(jīng)驗(yàn)與中國(guó)革命的具體實(shí)踐之間事實(shí)上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罔顧中國(guó)實(shí)際,教條地應(yīng)用馬恩經(jīng)典已經(jīng)造成了黨內(nèi)思想的混亂,并使得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和中國(guó)革命遭受了一系列重大挫折與損失。 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的雙重任務(wù)要求毛澤東從哲學(xué)的高度、以實(shí)事求是的態(tài)度對(duì)革命態(tài)勢(shì)加以深入考察和深度透視。 因此,“兩論”的產(chǎn)生具有劃時(shí)代的歷史意義與實(shí)踐價(jià)值。
“兩論”是理論與實(shí)踐相互統(tǒng)一的杰出作品,更是毛澤東關(guān)于自身理論與實(shí)踐的一次深刻總結(jié)與提升。 豐富的閱讀量和閱讀史是毛澤東得以進(jìn)行理論創(chuàng)新的基礎(chǔ)。 埃德加·斯諾曾說(shuō):“他博覽群書(shū),對(duì)哲學(xué)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②毛澤東的閱讀并不僅限于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他曾謙稱自己“也讀過(guò)一些古希臘哲學(xué)家、斯賓諾莎、康德、歌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③。 因此,“兩論”在中國(guó)政治史、哲學(xué)史上都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shí)和理論價(jià)值,尤其是備受?chē)?guó)內(nèi)外無(wú)以計(jì)數(shù)學(xué)者關(guān)注的《矛盾論》,幾乎是公認(rèn)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guó)發(fā)展的新形式的里程碑”和“關(guān)鍵的轉(zhuǎn)折點(diǎn)”④。
正是因?yàn)?ldquo;兩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guó)化過(guò)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國(guó)外學(xué)者也嘗試從“兩論”中去尋找和探源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形成的理論地基。 然而,因?yàn)閲?guó)外學(xué)者隱含的政治立場(chǎng)以及對(duì)于“兩論”文本的不熟悉,部分國(guó)外學(xué)者比如阿瑟·科恩就曾提出,“兩論”是解放后著作的命題。 另一方面,部分國(guó)外學(xué)者更是從簡(jiǎn)單的對(duì)照式閱讀方式出發(fā),認(rèn)為“兩論”的原始版本是對(duì)蘇聯(lián)教科書(shū)和李達(dá)《社會(huì)學(xué)大綱》等文本的抄襲。 因此,關(guān)于毛澤東哲學(xué)研究領(lǐng)域的歷史虛無(wú)主義批判,必須重視“抄襲改寫(xiě)論”和“雷同翻版論”這兩個(gè)重要觀點(diǎn)。
(二)“兩論”與蘇聯(lián)作品的關(guān)系問(wèn)題之誤判:歷史虛無(wú)觀之“抄襲改寫(xiě)論”
歷史虛無(wú)主義關(guān)注的第一層次是“兩論”與蘇聯(lián)教科書(shū)之間的理論聯(lián)系。 “抄襲改寫(xiě)論”認(rèn)為,毛澤東的《實(shí)踐論》與《矛盾論》大篇幅地抄襲和改寫(xiě)了蘇聯(lián) 30 年代的哲學(xué)教科書(shū),而沒(méi)有增添新的理論要素。 因此,“兩論”根本不是毛澤東哲學(xué)的理論創(chuàng)新,而是一種意識(shí)形態(tài)的作品。 從這個(gè)維度出發(fā),他們既否定了“兩論”的真實(shí)性,也進(jìn)一步否定了毛澤東哲學(xué)的合法性。 從文本依據(jù)來(lái)看,歷史虛無(wú)主義者認(rèn)為,毛澤東在撰寫(xiě)“兩論”之時(shí)主要是參考并抄襲了《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新哲學(xué)大綱》和《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等哲學(xué)教科書(shū),進(jìn)而從形式與內(nèi)容雙重維度挪用了教科書(shū)中的核心要素和理論體系建構(gòu)方式⑤。
“抄襲改寫(xiě)論”的問(wèn)題在于文本考據(jù)的失真與還原主義邏輯。 必須指出,蘇聯(lián)教科書(shū)構(gòu)成了毛澤東思考哲學(xué)問(wèn)題的重要理論場(chǎng)域之一,但是其并不構(gòu)成毛澤東進(jìn)行理論創(chuàng)作的唯一邊界。 根據(jù)尼克·奈特的考證,在延安時(shí)期,毛澤東不僅閱讀過(guò)《辯證法唯物論教程》《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等著作,更閱讀了相當(dāng)多的馬恩原著,其中包括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列寧的《談?wù)勣q證法問(wèn)題》《唯物主義和經(jīng)驗(yàn)批判主義》等著作,并為此做了大量的筆記和批注,僅在研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之時(shí)就“有將近一萬(wàn)兩千字的批注”①。 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許全興教授指出:“在 1936 至 1937 年 7 月間,毛澤東系統(tǒng)地發(fā)憤讀書(shū)(尤其是哲學(xué)),總結(jié)經(jīng)驗(yàn),在理論上了一個(gè)很大的臺(tái)階”②。
單純地從文本考據(jù)出發(fā),并不能還原毛澤東寫(xiě)作“兩論”的原初語(yǔ)境。 與此相反,單純的文本考據(jù)卻往往會(huì)采用一種超歷史的還原主義邏輯并得出關(guān)于作品和作者本人“去歷史化”的否定性結(jié)論。 美國(guó)學(xué)者、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斯圖爾特·施拉姆(Stuart R. Schram)就曾直言不諱地指出:“毛關(guān)于辯證唯物主義的講演……相當(dāng)大的部分,尤其是開(kāi)始講的那幾章,幾乎是不加掩飾地抄襲蘇聯(lián)的材料。”③除此之外,波蘭學(xué)者萊塞克·科拉科夫斯基也在他的《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以及它們各種起源、發(fā)展和瓦解》一書(shū)中指出:“毛的兩篇哲學(xué)論文———《實(shí)踐論》和《矛盾論》是一種對(duì)他所讀過(guò)的列寧和斯大林著作的大眾化與簡(jiǎn)單化的解說(shuō)。”④很明顯,施拉姆和科拉科夫斯基在關(guān)于“兩論”的歷史性定位的問(wèn)題上出現(xiàn)了還原主義的錯(cuò)誤。 準(zhǔn)確來(lái)說(shuō),他們通過(guò)文本的考據(jù)注意到了毛澤東著作中的理論線索,但是在還原主義的邏輯下卻忽視了著作背后的歷史性場(chǎng)域。
(三)“兩論”與國(guó)內(nèi)作品的關(guān)系問(wèn)題之誤讀:歷史虛無(wú)觀之“雷同翻版論”
歷史虛無(wú)主義關(guān)注的第二層次是“兩論”與其同時(shí)代相關(guān)作品的理論聯(lián)系。 “雷同翻版論”認(rèn)為,毛澤東的“兩論”是毛澤東關(guān)于國(guó)內(nèi)三本重要哲學(xué)著作———《社會(huì)學(xué)大綱》 《大眾哲學(xué)》和《社會(huì)科學(xué)方法論》⑤的整合而不是毛澤東自身的理論創(chuàng)新。 除此之外,他們也試圖從毛澤東的秘書(shū)陳伯達(dá)的著作入手,論證在“兩論”的寫(xiě)作過(guò)程中陳伯達(dá)的理論立場(chǎng)對(duì)于毛澤東理解哲學(xué)問(wèn)題的潛在性影響。
“雷同翻版論”的問(wèn)題在于缺乏支撐性的文本依據(jù)并存在大量抽象的、平面化的理論預(yù)設(shè)。 《社會(huì)學(xué)大綱》《大眾哲學(xué)》和《社會(huì)科學(xué)方法論》集中體現(xiàn)了 20 世紀(jì) 30 年代中國(guó)哲學(xué)界的理論水平,但是并沒(méi)有任何文本依據(jù)可以證實(shí)毛澤東抄襲抑或請(qǐng)陳伯達(dá)代筆。 從現(xiàn)在可以公開(kāi)的文獻(xiàn)資料來(lái)看,毛澤東撰寫(xiě)“兩論”的過(guò)程比較復(fù)雜,其中既有蘇聯(lián)教科書(shū)的影響,也有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西方近代思想以及毛澤東與同時(shí)代的思想家理論之間相互碰撞所構(gòu)成的合力。 我們從《毛澤東書(shū)信集》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為集政治家、革命家、哲學(xué)家、文學(xué)家和詩(shī)人于一身的歷史巨人,與他善于和同時(shí)代的眾多思想家進(jìn)行交流與對(duì)話分不開(kāi)⑥。
“雷同翻版論”試圖去預(yù)設(shè)一個(gè)抽象的、平面化理解的毛澤東形象。 在這樣的命題結(jié)構(gòu)之中,毛澤東似乎只能以一個(gè)純粹政治家的身份出現(xiàn)。 從這個(gè)角度出發(fā),必然會(huì)得出毛澤東既沒(méi)有能力也沒(méi)有時(shí)間去進(jìn)行哲學(xué)寫(xiě)作的錯(cuò)誤結(jié)論。 然而問(wèn)題在于,抽象化的理論預(yù)設(shè)明確地與歷史發(fā)展的真正進(jìn)程不符。毛澤東不僅是一個(gè)偉大的政治家,更是一個(gè)有著自身獨(dú)特理論創(chuàng)新的哲學(xué)家。 長(zhǎng)征結(jié)束之后,毛澤東不僅有時(shí)間、更有能力從理論和實(shí)踐兩方面去總結(jié)和提升中國(guó)革命的歷史經(jīng)驗(yàn)。 也正是在兼具政治家和哲學(xué)家雙重身份的前提之下,毛澤東才有能力在實(shí)踐的基礎(chǔ)之上與國(guó)內(nèi)外的思想家進(jìn)行理論上的雙向互動(dòng)。
綜合透視以上兩方面的“抄襲說(shuō)”,其討論的核心實(shí)際上并不在于“抄襲”的內(nèi)容,關(guān)鍵在于讀者在閱讀文本的過(guò)程中采用的方法論。 歷史虛無(wú)主義的方法論基礎(chǔ)即在于認(rèn)為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是他人思想的翻版、改寫(xiě)或模仿,持此論者所看到的更多是形式層面上的某種“雷同”,而對(duì)于隱藏在白紙黑字背后的豐富思想及其存在的價(jià)值維度卻無(wú)力加以進(jìn)一步的深入思考和闡明。 因此,深入把握“兩論”的內(nèi)在理論邏輯結(jié)構(gòu),盡可能地窮盡文本的真實(shí)意蘊(yùn),就必須超越表層的話語(yǔ)形式,從單純的“文本直讀”轉(zhuǎn)向 “文本直讀”與“癥候閱讀”相結(jié)合的科學(xué)閱讀模式。
二、“兩論”爭(zhēng)議的實(shí)質(zhì)———閱讀模式的沖突
一定的閱讀模式?jīng)Q定了一定時(shí)期文本展開(kāi)的深度和廣度,更決定著文本背后歷史性維度的敞開(kāi)。直接地來(lái)看,單純性的“文本直讀”僅能確證表面上的文字信息,而只有積極引入“癥候閱讀”方法,才能透過(guò)文字與符號(hào)的表層敘述邏輯切入其背后的深層問(wèn)題式,從而避免作出諸如“抄襲說(shuō)”“翻版論”等簡(jiǎn)單論斷。
(一)“證據(jù)陷阱”與“碎片化邏輯”———“文本直讀”歷史性維度的遮蔽
文本直讀的基礎(chǔ)和前提是關(guān)于文本自身歷史性維度的懸置與主體的介入。 “證據(jù)陷阱”和“碎片化邏輯”出現(xiàn)在主體閱讀過(guò)程中關(guān)于文本自身內(nèi)容的切割和轉(zhuǎn)換。 因此,這種以私人的閱讀背景和心理經(jīng)驗(yàn)推動(dòng)下的文本直讀必然會(huì)出現(xiàn)關(guān)于同一文本材料相互矛盾的論斷。 相關(guān)學(xué)者認(rèn)為,“證據(jù)陷阱”即 “在看似客觀存在的、代表中立性與客觀性的‘證據(jù)’ (即經(jīng)驗(yàn)對(duì)象)面前,由于主體‘審視證據(jù)方法’的差異,面對(duì)同一‘證據(jù)’往往會(huì)達(dá)至截然不同的結(jié)論”,這就意味著從“證據(jù)審視”層面可以找到問(wèn)題的根源,也即兩種“證據(jù)審視”———依據(jù)顯性的文字編碼證據(jù)與穿透直觀證據(jù)深入其本質(zhì)———會(huì)帶來(lái)“截然不同的理論圖景”①。 從歸根結(jié)底意義上說(shuō),“直讀”模式中的“證據(jù)陷阱”的產(chǎn)生不是因?yàn)槲谋窘庾x者偏離文本太遠(yuǎn),而是恰恰相反,文本解讀者與文本之間的距離太近,甚至在這種解讀模式中,主體的過(guò)分介入已全然陷入到文本的文字與符號(hào)堆中無(wú)法抽身出來(lái),導(dǎo)致他們對(duì)文本賴以產(chǎn)生的社會(huì)歷史背景、文本對(duì)現(xiàn)實(shí)實(shí)踐的指導(dǎo)意義以及文本對(duì)未來(lái)社會(huì)發(fā)展的啟發(fā)等多個(gè)維度視而不見(jiàn)。
“證據(jù)陷阱”的背后隱藏的是關(guān)于一定時(shí)期歷史性維度的“碎片化邏輯”。 這種“碎片化邏輯”的問(wèn)題在于其孤立、靜止、零碎地思考文本與文字本身,忽視了深藏于其中的思想理論的完整、系統(tǒng)、延續(xù)的圖景,特別是忽視了文本所特有的問(wèn)題意識(shí)和內(nèi)容層次的重要性等級(jí)。 在《矛盾論》中,單就“矛盾同一法則”而言,毛澤東的“矛盾論”顯然意味著“對(duì)立統(tǒng)一規(guī)律”在重要性上明顯高于“否定之否定”以及 “質(zhì)量互變”規(guī)律,而在蘇聯(lián)教科書(shū)中就沒(méi)有這樣的認(rèn)識(shí)②。 實(shí)際上,毛澤東甚至曾斷言不存在所謂的 “否定之否定”。 這就意味著“矛盾論”的存在并非如蘇聯(lián)教科書(shū)以及相關(guān)譯文那樣停留在理論文本表層邏輯,而是呈現(xiàn)出了毛澤東自身思想的強(qiáng)大創(chuàng)造力和生命力。
文本直讀中歷史性維度的缺失是其本質(zhì)性的缺陷。 “兩論”本身就是歷史的產(chǎn)物,不從寬廣的歷史性維度出發(fā)去透視 20 世紀(jì)初國(guó)內(nèi)外的歷史環(huán)境及觀念的變遷與發(fā)展?fàn)顩r,就根本無(wú)法對(duì)文本加以正確解讀和認(rèn)知。 因此,在不深入了解這段歷史的情況下武斷地對(duì)“兩論”加以解讀和詮釋,便很難把握住其中的精髓,更難以將其中最有價(jià)值的內(nèi)容呈現(xiàn)出來(lái)。 實(shí)際上,在中蘇建交初期,受中蘇友好關(guān)系的影響,蘇聯(lián)學(xué)界對(duì)“兩論”給予了極大關(guān)注并作出了高度評(píng)價(jià),認(rèn)為《實(shí)踐論》的“作者全面地考察了辯證唯物論的認(rèn)識(shí)論,并論證和發(fā)展了每一個(gè)原理”①,《矛盾論》是“杰出的、深刻的、有重要價(jià)值的著作,是對(duì)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理論的卓越貢獻(xiàn)”②。 與之形成對(duì)比的是,上世紀(jì) 60 年代,蘇聯(lián)從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出發(fā),對(duì)“兩論”作出歷史虛無(wú)主義化的否定。 因此,僅僅抓住這種前后不一致乃至前后矛盾的解讀與評(píng)價(jià),忽略和漠視其中的歷史性線索,去單純地否定“兩論”,是一種非歷史、非科學(xué)的解讀模式。
非反思性地對(duì)“兩論”進(jìn)行文本直讀,是歷史虛無(wú)主義“抄襲改寫(xiě)論”和“雷同翻版論”命題產(chǎn)生的根源。 總體來(lái)看,歷史虛無(wú)主義既忽視了文本的深層次內(nèi)容結(jié)構(gòu),也忽視了文本內(nèi)在思想價(jià)值的延展性, 更忽視了人類社會(huì)歷史的變遷和延續(xù)以及與之相伴隨的人們的思想與認(rèn)識(shí)的深刻變化,從而不可避免地成為了一種形式直讀與對(duì)于文本非法性地過(guò)度解讀。 因此,重新審視和回顧“兩論”的目的,就在于將其核心價(jià)值及思想原創(chuàng)性從形式化、平面化的文本直讀中進(jìn)行解蔽與探源。 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筆者認(rèn)為,我們?cè)诮庾x“兩論”之時(shí)應(yīng)當(dāng)積極借鑒法國(guó)結(jié)構(gòu)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學(xué)者阿爾都塞所提出的一種深入認(rèn)知思想家作品的閱讀方法———“癥候閱讀”。
(二)“癥候閱讀”:探源“兩論”的深層問(wèn)題式
“癥候閱讀”是由法國(guó)著名哲學(xué)家阿爾都塞提出的獨(dú)特閱讀模式,其目的是透過(guò)文字的表象去探源文本內(nèi)部的深層問(wèn)題式。 在阿爾都塞看來(lái),所謂的歷史真實(shí)以及文本的全部意蘊(yùn)“不可能從它的公開(kāi)的語(yǔ)言中閱讀出來(lái),因?yàn)闅v史的文字并不是一種聲音(Le Logos)在說(shuō)話,而是諸結(jié)構(gòu)中某種結(jié)構(gòu)的作用的聽(tīng)不出來(lái)、閱讀不出來(lái)的自我表達(dá)。”③因此,就需要一種能夠超越文本字面意義束縛的閱讀方法——— “癥候閱讀”方法。 阿爾都塞說(shuō):“所謂癥候讀法就是在同一運(yùn)動(dòng)中,把所讀的文章本身中被掩蓋的東西揭示出來(lái)并且使之與另一篇文章發(fā)生聯(lián)系,而這另一篇文章作為必然的不出現(xiàn)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④以此為基礎(chǔ),阿爾都塞非常強(qiáng)調(diào)閱讀模式自覺(jué)的重要性:“逐一的進(jìn)行‘癥候’閱讀,即系統(tǒng)地不斷地生產(chǎn)出總問(wèn)題對(duì)它的對(duì)象的反思,這些對(duì)象只有通過(guò)這種反思才能夠被看得見(jiàn)。” ⑤也就是說(shuō),非反思性地進(jìn)行文本直讀,很大程度上有可能是關(guān)于文本自身深層問(wèn)題式的曲解,文本的深層信息只有借助 “癥候閱讀”的方法才能逐一呈現(xiàn)。
文本內(nèi)部的深層問(wèn)題式是以歷史性維度為基礎(chǔ),指向文本所未直接表述、語(yǔ)言文字未直接呈現(xiàn)的邏輯結(jié)構(gòu)和價(jià)值取向。 國(guó)外學(xué)者之所以在理論上難以進(jìn)入“兩論”所關(guān)涉的內(nèi)在時(shí)空?qǐng)鲇?不僅僅是他們采用了一種抽象的、平面的文本直讀,更在于他們?nèi)狈σ环N歷史性的維度即只是將“兩論”當(dāng)作是單純的文本而不是毛澤東在文本背后所指向的實(shí)踐智慧與辯證法問(wèn)題。 這就像國(guó)內(nèi)學(xué)者所指出的,抄襲論的最大問(wèn)題就在“將思想的建構(gòu)過(guò)程及其本質(zhì)內(nèi)涵簡(jiǎn)單化,……將思想視為由概念、詞句等因子簡(jiǎn)單堆積的產(chǎn)物,是上述因子量的積累和形式上的簡(jiǎn)單編排,而忽視了概念、詞句背后所深含的理論架構(gòu)與本質(zhì)邏輯”⑥。 盡管在毛澤東與蘇聯(lián)教科書(shū)中存在著許多相似的文字表達(dá)內(nèi)容,然而蘇聯(lián)教科書(shū)的語(yǔ)境中存在的意義并不存在于中國(guó)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下的《矛盾論》中,其意在表達(dá)的東西也并不完全等同于毛澤東的《矛盾論》。
因此,對(duì)《矛盾論》的科學(xué)解讀,既要重視蘇聯(lián)教科書(shū)和國(guó)內(nèi)作品中處于顯性狀態(tài)的表層文字邏輯, 又要深刻地意識(shí)到潛藏在表層文字邏輯背后的深層問(wèn)題式。 只有如此,《矛盾論》中毛澤東原創(chuàng)性要素才能夠積極呈現(xiàn)且受到重視與認(rèn)同。 實(shí)際上,強(qiáng)調(diào)“兩論”的原創(chuàng)性以及對(duì)中國(guó)革命實(shí)踐的指導(dǎo)意義的聲音并不是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孤立地發(fā)出的,而是由國(guó)內(nèi)外眾多學(xué)者在獲得基本認(rèn)同和認(rèn)定之后得出的研究結(jié)果。 杰姆遜指出:“在 19 世紀(jì) 50、60 年代的法國(guó),毛澤東的《矛盾論》對(duì)馬克思主義者的影響是很大的,是結(jié)構(gòu)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典著作之一”①,其中的原創(chuàng)性與對(duì)推動(dòng)現(xiàn)實(shí)革命實(shí)踐的重要性非傳統(tǒng)蘇聯(lián)教科書(shū)所能比擬。 諾曼·萊文在認(rèn)真考察這一著作時(shí)也曾指出:“毛澤東沒(méi)有簡(jiǎn)單抄襲斯大林教科書(shū)體系的基本觀點(diǎn),真正影響毛澤東的不是斯大林的教科書(shū)體系,也不是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jīng)驗(yàn)批判主義》 ,而是列寧的《哲學(xué)筆記》 。”②高度肯定毛澤東的《矛盾論》這一代表作的阿爾都塞更是指出其復(fù)雜性與原創(chuàng)性就在于指出了“矛盾與矛盾之間、各矛盾方面之間存在的支配關(guān)系” ,“這種支配關(guān)系是矛盾的基本關(guān)系”③。 因此在這個(gè)意義上來(lái)說(shuō),抄襲論并沒(méi)有深入到毛澤東在“兩論”中指稱的深層問(wèn)題式,而只是停留在文本的表象。
(三)科學(xué)文本閱讀模式:“文本直讀”與“癥候閱讀”的辯證結(jié)合
“文本直讀”與“癥候閱讀”是學(xué)習(xí)和研究“兩論”的科學(xué)閱讀模式。 實(shí)際上,“直讀”恰恰奠定了“癥候閱讀”的基礎(chǔ),而“癥候閱讀”則是在“文本直讀”基礎(chǔ)之上進(jìn)一步重構(gòu)對(duì)作品的表層邏輯結(jié)構(gòu)的認(rèn)識(shí)。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就以“文本直讀”的方式對(duì)比過(guò)“ 《辯證法唯物論》 (講授提綱) ” 、《矛盾論》以及蘇聯(lián)教科書(shū)《辯證法唯物論教程》④。 《矛盾論》中有相當(dāng)一部分內(nèi)容確實(shí)是受到蘇聯(lián)教科書(shū)的影響,甚至也有部分錯(cuò)誤看法的繼承。 譬如,看待“否定之否定法則”部分時(shí)的一些思考在新中國(guó)成立后得到毛澤東本人的修正與刪除。 總體來(lái)看,版本之間的刪節(jié)與增補(bǔ)體現(xiàn)出了毛澤東在不同時(shí)期關(guān)于同一問(wèn)題的思考和認(rèn)知模式的變動(dòng)。 重視“文本直讀”就是在堅(jiān)持文本序列系統(tǒng)性的基礎(chǔ)之上,為“癥候閱讀”建立扎實(shí)的文本考據(jù)功夫。
“癥候閱讀”法,超越了對(duì)文本的簡(jiǎn)單解讀與思考,而是將其表述放置于特定的理論空間及時(shí)代背景之中,這就需要借助更多的理論作品與時(shí)代作品以拓寬理論視閾,進(jìn)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認(rèn)知與審視。就理論積淀與創(chuàng)作背景而言,從《毛澤東哲學(xué)批注集》就能夠看到,毛澤東的哲學(xué)思想明顯具有深厚的中國(guó)古代哲學(xué)思想的根基,特別是在對(duì)樸素辯證法的認(rèn)知與把握上,結(jié)合了中國(guó)歷史的經(jīng)驗(yàn)發(fā)展規(guī)律, 能夠更加深入淺出地闡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與理論,而這些則是蘇聯(lián)教科書(shū)和其他很多理論著作所不具備的。 除此之外,就時(shí)空背景而言,中國(guó)近代發(fā)展史與特殊性極其顯著的革命史,以及毛澤東本人經(jīng)歷的革命成功與失敗的現(xiàn)實(shí)體驗(yàn)與深刻總結(jié),也都包含在毛澤東對(duì)相關(guān)問(wèn)題的深度思考與認(rèn)識(shí)之中,這就擺脫了黨的其他領(lǐng)導(dǎo)人所犯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和命令主義等錯(cuò)誤,更加科學(xué)而有效地認(rèn)知并改造現(xiàn)實(shí)。 正如許全興教授所言:“任何一個(gè)沒(méi)有偏見(jiàn)的人,只要把《實(shí)踐論》 《矛盾論》與上述三本蘇聯(lián)哲學(xué)教科書(shū)有關(guān)部分相比較就不難看出,無(wú)論在體系上還是在內(nèi)容上,毛澤東同志都依據(jù)中國(guó)革命的實(shí)踐進(jìn)行了理論上的創(chuàng)造”⑤。 毫無(wú)疑問(wèn),沒(méi)有這種基于現(xiàn)實(shí)考量的理論創(chuàng)造性,就不可能有如此驚人的理論效應(yīng)和對(duì)現(xiàn)實(shí)實(shí)踐的強(qiáng)大作用力。
綜上所述,正如阿爾都塞在《讀〈資本論〉 》一書(shū)中所提出的那樣:“要把毛澤東于 1937 年寫(xiě)的《矛盾論》看作政治實(shí)踐中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結(jié)構(gòu)的反思描述” ,而非“單純的‘概念化’ ”⑥。 從經(jīng)典文本的閱讀方法與觀察視角的轉(zhuǎn)換之中,我們可以看出以“抄襲論”為代表的歷史虛無(wú)主義觀點(diǎn)是一種以還原主義邏輯為核心的簡(jiǎn)單對(duì)照式閱讀模式。 一方面,歷史虛無(wú)主義對(duì)文本的解讀過(guò)分地依賴文本本身,忽略了文本背后深刻的歷史背景與理論淵源;另一方面,他們更忽視了歷史性維度對(duì)于中國(guó)現(xiàn)實(shí)的解釋力與改造力。 因此,科學(xué)地閱讀“兩論”必須將“文本直讀”與“癥候閱讀”辯證地統(tǒng)一起來(lái),才能理解“兩論”文本與現(xiàn)實(shí)實(shí)踐之間歷史的具體的統(tǒng)一。
三、以“兩論”為代表的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的意義與價(jià)值
以“兩論”為代表的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具有復(fù)雜的整體結(jié)構(gòu),其中既包括蘇聯(lián)教科書(shū)及國(guó)內(nèi)譯者的影響,也有毛澤東自身關(guān)于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西方近代哲學(xué)以及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與思考。 因此單一地以文字和用詞結(jié)構(gòu)的相似性去指認(rèn)“兩論”關(guān)于蘇聯(lián)教科書(shū)的抄襲,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對(duì)于文本思想背后深層問(wèn)題式的遮蔽。 毛澤東一向拒斥用機(jī)械主義的方式理解馬克思主義,這不僅是國(guó)內(nèi)眾多學(xué)者所公認(rèn)的, 亦是為包括尼克·奈特在內(nèi)的不少海外學(xué)者所注意到了的①。 因此我們需要從根本上揭穿歷史虛無(wú)主義觀點(diǎn)的虛假性、材料使用上的不正當(dāng)性和解讀模式的非科學(xué)性,并在此基礎(chǔ)之上深度認(rèn)知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的重要理論價(jià)值及現(xiàn)實(shí)意義。
(一)歷史虛無(wú)主義的誤判:對(duì)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創(chuàng)造性與系統(tǒng)性的忽略
歷史虛無(wú)主義者對(duì)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最大的誤讀與誤判就在于他們忽略了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與系統(tǒng)性。 我們?cè)谥匦陆庾x和思考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時(shí),要正本清源,辨清毛澤東本人的哲學(xué)思想與其他思想的諸多細(xì)微差別乃至本質(zhì)差異。
第一,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是建立在豐富的實(shí)踐基礎(chǔ)之上的理論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 毛澤東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深入地研究和探索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問(wèn)題。 在“矛盾的特殊性”問(wèn)題上,毛澤東不僅深刻地指出了矛盾特殊性對(duì)于理解矛盾結(jié)構(gòu)的重要性,更將對(duì)立統(tǒng)一規(guī)律定義為理解辯證法問(wèn)題的核心和基礎(chǔ),超越和批判了教條主義孤立、靜止、片面的形而上學(xué)傾向。 在改造世界的方面,毛澤東更是將馬克思主義中國(guó)化推進(jìn)了一大步。 毛澤東將這一命題豐富和拓展為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兩個(gè)重要的維度,而且在實(shí)踐層面對(duì)主觀世界的改造給予了極大重視。 由此可見(jiàn),忽視“兩論”文字背后承載的歷史價(jià)值即引導(dǎo)革命方向與成功實(shí)踐的經(jīng)驗(yàn)事實(shí),不僅與文本的事實(shí)不符,更與現(xiàn)實(shí)歷史發(fā)展的進(jìn)程相違背。
第二,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是基于“多元”理論資源的把握、吸收與改造基礎(chǔ)上的理論系統(tǒng)性轉(zhuǎn)化。 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guó)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互融合的理論結(jié)晶。 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chǎng)、觀點(diǎn)與方法,批判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的封建主義因素,將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的合理內(nèi)核用馬克思主義的術(shù)語(yǔ)清晰地表達(dá)出來(lái),賦予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新的活力與生命力。 正如臺(tái)灣學(xué)者劉季輪所言:“毛澤東是在他自己的一套符號(hào)系統(tǒng)中,來(lái)重新運(yùn)用這些詞句的。 語(yǔ)句依然,但它們的位置、它們的作用、它們的意涵,都必須重新加以考釋。”②因此,“兩論”文字的背后并不是一個(gè)平面化的語(yǔ)義系統(tǒng),而是一個(gè)復(fù)雜的系統(tǒng)結(jié)構(gòu)。 毛澤東在行文過(guò)程中引用的各種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的成語(yǔ)、典故、事例的內(nèi)涵與外延都已經(jīng)發(fā)生了重大的轉(zhuǎn)變。 因此,不從系統(tǒng)化的視角審視“兩論”的文本,就無(wú)法讀出毛澤東文本的內(nèi)在意蘊(yùn)與深層問(wèn)題式。
第三,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是建立在豐富歷史資源之上的與現(xiàn)實(shí)革命運(yùn)動(dòng)緊密相連的理論的要點(diǎn)性轉(zhuǎn)化。 要點(diǎn)性轉(zhuǎn)化是指擺脫文本具體內(nèi)容的束縛與制約,既是對(duì)于前人思想精髓與重點(diǎn)的精準(zhǔn)把握,又是對(duì)時(shí)代主題與歷史任務(wù)的準(zhǔn)確定位。 無(wú)論從理論文本中加以考察,抑或是從其實(shí)踐層面加以透視,都不難發(fā)現(xiàn)毛澤東本人對(duì)于形式主義、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持有極為強(qiáng)烈的批判與否定的態(tài)度。 然而,歷史虛無(wú)主義者卻認(rèn)為毛澤東的“兩論”是一種教條主義式的抄襲與翻版。 準(zhǔn)確來(lái)說(shuō),對(duì)于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的作品、蘇聯(lián)的教科書(shū)以及《社會(huì)學(xué)大綱》等書(shū)目,毛澤東都帶著強(qiáng)烈的現(xiàn)實(shí)關(guān)懷與問(wèn)題意識(shí)去加以精心閱讀。 這同時(shí)也就意味著他本人對(duì)于他性文本中所提出的具體結(jié)論與原則并沒(méi)有立刻形成剛性的理論定式,而是將更多的精力聚焦于對(duì)內(nèi)容形式背后的理論要點(diǎn)和內(nèi)容核心的把握和借鑒,將這些最能夠與中國(guó)現(xiàn)實(shí)相契合的“動(dòng)力論”要素、方法論精髓進(jìn)行思考與要點(diǎn)化,從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審視問(wèn)題的世界觀與方法論。
(二)重釋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的歷史價(jià)值與理論貢獻(xiàn)
以“兩論”為核心的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與價(jià)值,是關(guān)于 20 世紀(jì) 20 年代到 30 年代中國(guó)革命實(shí)踐的重大理論總結(jié)。 理論是實(shí)踐的前導(dǎo),中國(guó)社會(huì)主義革命的成功就在于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 毛澤東本人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也談到過(guò):“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guó)的東西,在中國(guó)過(guò)去是吃過(guò)大虧的”①。 盡管施拉姆對(duì)于“兩論”文本的考據(jù)存在誤判,但還是對(duì)毛澤東的理論貢獻(xiàn)給予了最高的評(píng)價(jià):“毛澤東關(guān)于矛盾問(wèn)題所作出的杰出貢獻(xiàn)、是他一生中絕無(wú)僅有的”②。 這就意味著,對(duì)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的解讀與評(píng)價(jià),必須重視其理論貢獻(xiàn)、實(shí)踐貢獻(xiàn)以及理論貢獻(xiàn)的后續(xù)效應(yīng)。
第一,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堅(jiān)持了實(shí)事求是的核心理念。 無(wú)論是《實(shí)踐論》還是《矛盾論》,其背后反映的第一個(gè)價(jià)值理念就是實(shí)事求是。 毛澤東將實(shí)事求是這個(gè)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的經(jīng)典命題在更宏觀的理論視閾中賦予了全新的內(nèi)涵,在哲學(xué)的高度上“徹底地打破了對(duì)辯證法的教條主義的理解”③。 很明顯,毛澤東的核心關(guān)懷、閱讀旨趣以及理想信念都在于運(yùn)用科學(xué)的思想尤其是借助暗含于其中的方法論精髓去認(rèn)知中國(guó)的國(guó)情,把握社會(huì)歷史潮流涌動(dòng)的方向,以深刻認(rèn)識(shí)和改造中國(guó)的現(xiàn)實(shí),服務(wù)于現(xiàn)實(shí)的革命實(shí)踐。 因此,實(shí)事求是的理念與精神,在毛澤東那里,無(wú)論從理論的吸收與創(chuàng)造維度,還是從對(duì)實(shí)現(xiàn)實(shí)踐的分析、駕馭與指導(dǎo)維度都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第二,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奠定了科學(xué)的唯物論基礎(chǔ)。 毛澤東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rèn)識(shí)論”是“以科學(xué)的社會(huì)實(shí)踐為特征的”④。 也即是說(shuō),要獲取對(duì)現(xiàn)實(shí)革命局勢(shì)的全面而深刻的認(rèn)識(shí),就必須在理論的高度上,既要徹底地批判機(jī)械唯物主義的“投降論”,也要徹底地批判唯心主義的“速勝論”,為中國(guó)革命奠定科學(xué)的唯物論基礎(chǔ)。 在《實(shí)踐論》中,毛澤東多次強(qiáng)調(diào)實(shí)踐的第一性原理,并用生動(dòng)形象的實(shí)例去指出實(shí)踐關(guān)于理論、理論關(guān)于實(shí)踐的雙向互動(dòng)聯(lián)系。 在毛澤東看來(lái),實(shí)踐與認(rèn)識(shí)的關(guān)系問(wèn)題絕不是從實(shí)踐到認(rèn)識(shí)的簡(jiǎn)單對(duì)接過(guò)程,而是一種互動(dòng)與互嵌的復(fù)雜關(guān)系。 如毛澤東自己所言,社會(huì)實(shí)踐“就是檢驗(yàn)理論與發(fā)展理論的過(guò)程,是整個(gè)認(rèn)識(shí)過(guò)程的繼續(xù)” ⑤。 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實(shí)踐本身就是一種認(rèn)識(shí)世界的方式,更是唯物主義立場(chǎng)在認(rèn)識(shí)論領(lǐng)域的展開(kāi)。
第三,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矛盾觀。 矛盾是辯證法的核心,通過(guò)列寧的《哲學(xué)筆記》,毛澤東間接地讀到了黑格爾的矛盾理論。 除此之外,阿爾都塞和諾曼·萊文等國(guó)外學(xué)者更是試圖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對(duì)毛澤東的矛盾理論與黑格爾哲學(xué)之間的關(guān)系問(wèn)題加以詮釋學(xué)意義上的闡發(fā)。當(dāng)然,對(duì)毛澤東的矛盾理論建構(gòu)而言,更重要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對(duì)于黑格爾的批判性分析以及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的全新理論分析模式。 我們能夠很明顯地看到,在《矛盾論》中對(duì)“對(duì)立統(tǒng)一規(guī)律”的創(chuàng)造化、系統(tǒng)化、要點(diǎn)化,較為充分地體現(xiàn)出毛澤東哲學(xué)抓住了“唯物辯證法的實(shí)質(zhì)和核心”⑥,認(rèn)識(shí)到中國(guó)革命的主要矛盾是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并區(qū)分出對(duì)抗性的和非對(duì)抗性的矛盾的重要性。
(三)再探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的時(shí)代價(jià)值與意義
將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放置于當(dāng)代中國(guó)重新加以透視和詮釋,特別是將其放置于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國(guó)家的關(guān)鍵節(jié)點(diǎn)和偉大歷史方位,不僅僅是簡(jiǎn)單地將深藏于毛澤東的實(shí)踐與文本的思想觀點(diǎn)與方法論精髓加以挖掘和闡釋,而是要將其中的真正對(duì)當(dāng)下社會(huì)發(fā)展有益的“動(dòng)力論”要素加以提煉,并使之對(duì)當(dāng)今中國(guó)的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實(shí)踐提供某種非替代性的思想啟發(fā)和精神動(dòng)力。
第一,堅(jiān)持實(shí)事求是的精神,引領(lǐng)中國(guó)社會(huì)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實(shí)踐。 盡管毛澤東所處的時(shí)代乃是“前工業(yè)化”和“前現(xiàn)代化”的時(shí)代,但他的理論與實(shí)踐的諸多探索卻始終以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為最終目的。 他甚至試圖走出一條異質(zhì)于西方資本主義所走過(guò)的道路以實(shí)現(xiàn)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為現(xiàn)代化提供中國(guó)方案。更重要的是,在實(shí)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人完成了讓中國(guó)人民“站起來(lái)”的歷史使命。 現(xiàn)代化是一個(gè)系統(tǒng)性的工程,必須堅(jiān)定不移地堅(jiān)持實(shí)事求是的實(shí)踐作風(fēng),認(rèn)識(shí)到事物發(fā)展本身的過(guò)程性以及主體對(duì)客體的認(rèn)識(shí)的歷史性,以全新的實(shí)踐改造原有的主觀認(rèn)識(shí),進(jìn)而推動(dòng)新的實(shí)踐,更要避免因?qū)嵤虑笫蔷竦膯适Ф箤?shí)踐指導(dǎo)思想教條化和主觀化。
第二,堅(jiān)持矛盾分析法,分析當(dāng)代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主要矛盾。 毛澤東關(guān)于矛盾分析的方法是理解當(dāng)前中國(guó)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實(shí)踐的重要工具。 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在科學(xué)地繼承了毛澤東矛盾分析方法的前提下,我們不僅抓住了發(fā)展生產(chǎn)力這一主要矛盾,更積極地發(fā)揚(yáng)了自力更生與對(duì)外開(kāi)放相結(jié)合的理念與策略,強(qiáng)化了社會(huì)發(fā)展過(guò)程中的自主性與能動(dòng)性。 應(yīng)當(dāng)指出,經(jīng)濟(jì)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不可避免地會(huì)帶來(lái)各種社會(huì)問(wèn)題,社會(huì)主義初級(jí)階段必然會(huì)面臨各種風(fēng)險(xiǎn)挑戰(zhàn)。 因此,各級(jí)黨委和政府更需要遵循辯證法的基本規(guī)律,正確處理不同類別,不同性質(zhì)的矛盾問(wèn)題,分清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以便于將其加以正確處置,維護(hù)好社會(huì)的安定、有序與和諧。 在這個(gè)意義上來(lái)說(shuō),毛澤東的哲學(xué)思想仍然保持著旺盛的生機(jī)與活力,仍需要繼續(xù)堅(jiān)持和發(fā)揚(yáng)毛澤東哲學(xué)思想,推動(dòng)其在新時(shí)代持續(xù)不斷地出場(chǎng)。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jiàn)問(wèn)題 >
SCI常見(jiàn)問(wèn)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