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設計就是抽象和具象的和諧統(tǒng)一,才能充分建筑的美感和空間感,本文主要探討建筑設計中的抽象與具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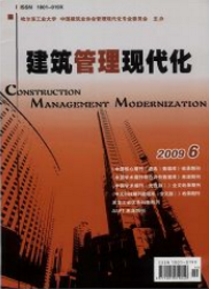
《建筑管理現(xiàn)代化》是建設部主管,由哈爾濱工業(yè)大學、中國建筑業(yè)協(xié)會管理現(xiàn)代化專業(yè)委員會主辦的國家級期刊。創(chuàng)刊于1987年9月,為雙月刊,國內(nèi)外公開發(fā)行。本刊主要報道國內(nèi)外行業(yè)內(nèi)的新成就、新成果;宣傳報道建筑企業(yè)的建立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轉(zhuǎn)換經(jīng)營機制的新經(jīng)驗。
“從具體到抽象,從抽象到具體”,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于所有的實踐活動過程的描述,比如科學實驗。但這一說法在建筑設計中,也許尤為典型。在這里,我首先想把“具體”定義為一種“建造”,把“抽象”定義為“建造之前”,如此,表示我們想要關(guān)注過程——一個設計誕生的過程。
“從具體到抽象,從抽象到具體”,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于所有的實踐活動過程的描述,比如科學實驗。但這一說法在建筑設計中,也許尤為典型。在這里,我首先想把“具體”定義為一種“建造”,把“抽象”定義為“建造之前”,如此,表示我們想要關(guān)注過程——一個設計誕生的過程。
建筑作為實踐活動的客體,它由墻體、柱子、梁板以及它們的開口(如窗洞、門洞等)等元素組成,更重要的,這些元素們組織在一起,形成了人們要使用的空間,所謂“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把磚塊和磚塊用砂漿粘結(jié)并壘起來形成墻,把水泥石子和鋼筋澆注在一起形成柱子、梁板等等,一個具體的建筑就是以類似這樣的建造方式一點點完成的。然而一個建筑并不是這樣就可以被建造了,“造一個怎樣的房子”這個問題將我們帶到建造之前,或者說是建筑師展開設計的落筆之前。
在此引用安德烈•迪普拉澤斯(Andrea Deplazes)為蘇黎世瑞士聯(lián)邦理工大學(ETH)建筑系一年級的學生作業(yè)集所寫的引言的內(nèi)容,他在這篇名為“制作建筑(Making Architecture)” 的引言里為建筑師的“建造之前”又引用了和亞里斯多德有關(guān)的一個詞——metaphysicists。metaphysics在漢語中被譯為“形而上學”,是日本哲學家井上哲次郎根據(jù)我國的《易經(jīng)•系辭》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譯過來的。亞里士多德把人類的知識分為三部分,用大樹作比喻:第一部分,最基礎的部分,樹根,是形而上學,它是一切知識的奠基;第二部分是物理學,好比樹干;第三部分是其他自然科學,以樹枝來比喻。這“形而上學”在亞里斯多德這里是“大樹”的樹根,在《易經(jīng)》中是抽象之“道”,也正是“建造之前”要有的功課。設計的過程,恰好就是將抽象的“道”,亦即思想和概念,向具體的“器”——也就是建筑的物質(zhì)性轉(zhuǎn)移的過程。需要一提的是,這抽象之“道”又是從具體之“器”之中獲得的,這一次的具體或可稱之為“元-具體”,也就是在新的具體創(chuàng)造出來之前的那些“具體”們,比如既存之物、過往案例、地形、地理等等。
迪普拉澤斯教授指導下的ETH建筑系一年級的一個學生作業(yè)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手套——物體”,一個時間只有一天的手工作業(yè)。學生們被要求從給定的一剛一柔兩種材料庫中各選取一種,去制作一幅手套。在這個前提下,你必須要籍著所選的具體材料建立一種結(jié)構(gòu),你不能直接沿用已有的建構(gòu)方法,你必須要思考出或理解到某種結(jié)構(gòu)原理、某種構(gòu)造方式,才能利用這剛?cè)醿煞N材料建立一種結(jié)構(gòu)體——附著的、包覆的、互動的……而這種結(jié)構(gòu)體又必須和你的手指發(fā)生功能及空間關(guān)系——保護的、保暖的、運動的……
毫無疑問,在制作這個手套之前,你得先想清楚要制作的手套和手的關(guān)系,而關(guān)于手的認識取決于對具體的手的觀察與了解,最后關(guān)于手的一些認識被體現(xiàn)在制作完成的一個的手套中,或者也可以說,被轉(zhuǎn)移為一剛一柔兩種材料的連接關(guān)系(圖1),這種轉(zhuǎn)移真是神奇,我們傾向于把這種轉(zhuǎn)移就叫做設計。然而,作為手套,這些手套們似乎還不能被作為常規(guī)的手套來使用,但它將一些非常規(guī)的主題推向了前臺,比如材料們的交接關(guān)系等等。迪普拉澤斯在那本作業(yè)集里這樣寫道:“它們將手與手套的關(guān)系主題化了,它們用建筑的方式詢問了一個覆層和所圍合出來的空間之間的關(guān)系。” 不過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又會說,這個手套太抽象了!不是嗎?一個并不能被真正使用的手套,用“抽象”這個詞形容恰恰好。這樣的設計和制作就像一次解剖活動,這個作業(yè)并不是要去制作一幅真正的手套,而是一次設計訓練,影響訓練結(jié)果的除了學生們各自對手的理解之外,還有一個誘導條件——你只能選擇一剛一柔兩種材料,這是導致結(jié)果主題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讓一次手套的制作活動演變?yōu)橐淮谓馄驶顒樱_實,手的部分具體性也被以這樣的方式明確地抽象了出來。
在當代的設計中,這種抽象性的表達似乎占據(jù)了越來越大的比重,那么,具體的建筑們需要這樣的抽象嗎?
一段時間以來,有關(guān)筱原一男“白之家”的抽象性的討論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也是我首次開始關(guān)注“抽象性”這一概念,最初我看著這個頗有些日本傳統(tǒng)風格的坡屋頂?shù)男∽≌瑹o法理解它的“抽象性”所在,隨著對筱原作品的系統(tǒng)性了解,還有像對日本年輕的建筑師藤本壯介寫的有關(guān)“白之家”《聯(lián)系永恒與日常之物——新的白、新的抽象》等文字的閱讀,我開始逐漸理解“白之家”那掩蓋掉內(nèi)部木構(gòu)架結(jié)構(gòu)的白色吊平頂以及最終以“白”字命名的這個小住宅在1966年的筱原作品中的特殊意義(圖2)。
隨后各種有關(guān)抽象性的討論進入視野,在一個題為《抽象的最前端》 的伊東豐雄和石上純也的對談中,甚至見到伊東這么說:“最近在各種各樣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人在討論抽象性、抽象的圖,也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的抽象……各種抽象催生出新的問題,成為新的討論話題,這是非常有趣的”,可見抽象一詞在日本當代建筑師的實踐語境中出現(xiàn)的密度之高了。在2009年出版的《西澤立衛(wèi)對談集》 這本書里,伊東豐雄、西澤立衛(wèi)、石上純也、藤本壯介等人也有大段的關(guān)于建筑“抽象性”的討論,不過他們談的這個抽象性并非我在本次競賽題目中想要表達的重點所在,所以在此不再展開,但是這本書里的討論,特別是伊東、石上等人參觀完西澤的十和田美術(shù)館后在回東京的新干線列車上所討論的那一段“抽象性”,非常精彩。盡管各種討論中有關(guān)“抽象”的話語概念被不斷偷換,就像本文前后“具體”與“抽象”的所指也不斷在飄移一樣,但似乎都有一個類似的共識,那就是抽象是走向新事物的動力,就連迪普拉澤斯在贊美具體的建造的同時,也不忘提及,“正是那些未建成建筑,就是所謂的‘空中樓閣’,才是推動著世界的動力” 。
我想再回到筱原一男,因為是他將我從抽象性又帶回了具體性,和人類學相關(guān)的具體性。
筱原一男1975年的時候去了一趟非洲,他在一篇題為《第三種風格》的文章中這樣寫道,“……我打開了窗簾,但是我看到的幾乎不是非洲(雖然有那么片刻,眼前的景色讓我想起了卡薩布蘭卡)。出現(xiàn)在眼前的這么一群建筑,可以在任何一座法式城市里找到。我把頭貼到了玻璃上,盡量向下望,我感到了一陣強烈的熱浪。這一次,我的眼睛捕捉到了某些熱帶樹木的輪廓和色彩。我住的房間位于樓的頂層,12還是13樓,從這里可以俯瞰到前夜我抵達這個賓館時最先進入的雨蓬(事實上,我是凌晨1或2點鐘到達的)。在一株枝葉繁茂的大樹下,站著5或6個黑人。除了他們,腳下的土地,塞內(nèi)加爾的達卡,表明了它是一座有著某種法國風情的城市。”
筱原一男在這個看似法國風情的非洲城市中捕捉到了兩樣東西——讓他覺得他可能真的身處非洲——某些熱帶樹木的輪廓和色彩、5或6個黑人。接著,他又寫道,“……不經(jīng)意間,我碰到一群年輕人在洗澡。這是一個漁村,出海之后,漁民就在海邊洗澡。當一片片落水濺落在黑色上面,那些黑色的身體、黑色大手結(jié)實的曲線、腳、頭顱、腰身,似乎像波浪一般涌動。就在露天淋浴的混凝土墻之外,就是黃金海岸。或許最深刻地代表著非洲空間的東西并不是真實的建筑或是街景,甚至不是海洋。相反,非洲空間的個性乃是它的居民本身。在這樣一次喧鬧的遭遇之后,我的非洲之旅抵達了終點。”
筱原一男一旦領(lǐng)會到非洲的具體性和它的居民之間的關(guān)系,他知道自己甚至不需要更多的旅程了。回國之后,筱原一男在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一書中印證了他關(guān)于“野蠻”與“具體性”的人類學直覺,并以此為他那一年即將施工的“上原通的家”作了一個“雨林”這樣野性的比喻。
我理解筱原的具體性卻是他1974年建成的“谷川之家”(圖3、4)。位于森林里起伏基地上的一個不大的住宅,卻用了接近3/4的室內(nèi)面積覆蓋了一個和原本地形完全吻合的裸土的坡,仿佛剝離了意義的木構(gòu)架支撐著白色平整的斜面天花,近似赤裸的空間就像ETH學生們的手套作業(yè)一樣將生活其中的人與土地的關(guān)系主題化了,筱原以這樣一種方式將現(xiàn)代生活中的人所能獲取的區(qū)別于自然空間的住居空間又逼回了野性自然的具體性之中,筱原將這個空間命名為“夏之空間”。筱原一男1980年代以后的作品走向了另一種幾何性和象征主義,但頗有些預示意味的是,他2001-2006年最后一個并未建成的設計作品——廖科山地之家又喚回了谷川時代的具體性,延展入室內(nèi)的地形、頗有些隨意的坡頂下的斜撐、甚至深入地下的浴室,人在室內(nèi)與室外地形相遇, 還有深入地下的洞穴般的空間,不過40平方米左右的住宅,濃縮了記憶與原始,野性之中,又帶著濃郁的關(guān)懷,以及對活著這一本能欲望的歌頌。
不得不說,筱原對具體性的關(guān)注轉(zhuǎn)移為他的建筑作品,卻又是以高度抽象性的方式來完成的呢,所以筱原在他的書中用了“廖科山地的初等幾何學”這么一個抽象的名字來命名他這最后一個住宅作品。建筑果真不就是從抽象到具體,抑或從具體到抽象么?
參考文獻:
[1] Andrea Deplazes(瑞士)編著,(原著Deplazes, Andrea, edited, “Making Architecture”, Zurich: GTA Verlga, c.2010)
[2]藤本壯介(日本)著,平輝譯,郭屹民校,《聯(lián)系永恒與日常之物——新的白、新的抽象》,[3]伊東豐雄+石上純也(日本)著,ZJJ爸爸+ZJJ譯,《抽象的最前端》(日本) 西澤立衛(wèi)編著,謝宗哲譯,西澤立衛(wèi)對談集,臺灣,田園城市 2010
[4]筱原一男(日本)著,城市筆記人譯,第三種風格英譯版原文見2G 58/59期,2011 .2-3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