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立足于周文的小說創作,系統梳理周文小說創作的歷程,全面總結其小說創作的藝術特色,如題材選取的獨特性、現實主義的指導思想與創作原則、白描手法的成功運用和冷峻客觀的表達等,進而更加明確周文小說研究的文學史價值與廣泛深遠的社會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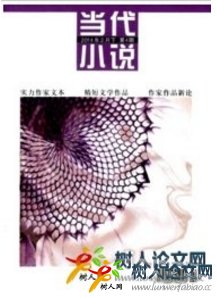
《當代小說(下半月)》(月刊)創刊于1979年,由濟南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辦是為拓展和豐富雜志的學術品格而專門發表學術論文的學術下半月刊,雜志集學術性、權威性、專業性于一體,內容豐富,印刷精美,雅俗共賞。
周文是中國現代文學百家之一,被魯迅稱為最優秀的左翼青年作家之一。周文運用自己特有的生活經歷與經驗,向現代文學貢獻了別樣世界的獨特風景,其小說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和鮮活的生命動力,跳躍著濃重的鄉土氣息。周文還始終遵循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和指導思想,清醒的面對生活的本相與人性的惡質,將他體驗到的真實運用白描手法加以客觀理性的冷峻表達,形成了自己保持一貫的獨特風格,從而,在左翼文壇中占有一席之地。
周文是中國上世紀30年代左翼文壇優秀的青年作家,于1907年6月17日生于雅安滎經城關鎮,1952年7月1日卒于北京。原名何開榮,字稻玉,筆名何谷天、樹嘉、周文等,以周文行世。周文的小說創作走過了一條艱苦多辛的創作之路。到達上海之前,是其小說創作的探索萌芽時期,為其日后創作積累了源源不竭的題材經驗。上海“左聯”期間,周文得到了魯迅的指導與幫助,達到其小說創作的頂峰,成為“多產”作家,享譽左翼文壇。后期轉向大量實際的革命工作之中,作品漸少,創作陷入沉寂。楊義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評價周文“是一個小說創作歷時不長,卻以豐厚而特異的生活積累,于三、五年間迅速成為藝術高手的作家”。正如楊義所講,周文的小說確有可圈可點之處,尤其是其小說創作獨特而鮮明的藝術風格,亦使他在30年代的左翼文壇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一
周文的小說創作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與人文地理特征。周文運用自己獨特的生活經歷與經驗,描寫川康邊地軍政生活,向現代文學的歷史中貢獻了“邊荒一隅”的獨特風景,拓寬了鄉土文學的發展道路。
周文是一位立足于本鄉本土的現實主義作家,其作品大多反映了西康生活的現狀,成為那個時代的一面鏡子。周文在25歲之前,一直生活在他的家鄉――西康。西康是今天的西藏東部與四川西部交界地區,也稱川康地區。川康一帶交通十分閉塞,外面的人很難進去,里面的人也很難出來,地理環境的封閉性,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物質生產和社會發展,也導致了當地居民思想文化上的落后。辛亥革命以前,此地屬農奴制社會,土司掌管一切,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其殘酷的壓榨剝削,比封建社會統治更為駭人聽聞。辛亥革命之后,四川護法戰爭正式發生之前,滇、黔軍和川軍為奪川政大權,終于釀成1917年的“劉羅”“劉戴”兩次省間大戰,這也標志著四川地區混戰的開始。此后,四川軍閥混戰次數之多、時間之長、危害之巨,在全國也頗為罕見。周文的家鄉滎經所屬的這個地區被劃為川邊特別區,也叫西康特別區,戰爭使這里的人民蒙受浩劫、流離失所,終年生活于水深火熱的深重災難之中。周文生活的年代,其故鄉滎經是軍閥統治下煙毒蔓延、兵匪橫行的地方 ,青少年時期的周文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成長,這一切在他腦海里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也為他日后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寶貴的素材。
“川康的交界處,是一個綿延不絕起起伏伏的高山。離開那個古舊的城市,通過許多荒蕪的田路和一些硬崖的狹谷,直到太陽當頂的時候,才可以走到這山腳……”這是周文在《茶包》中所描述的西康風情,這位生于西康邊地的四川作家,也以其生動的西康社會眾生相和獨特的地域風情,顯示了他的美學追求和文化建構,以悲劇的方式感知、表現人生,置悲劇于社會人生和文化價值模式里,去反思西康邊地人的生存方式和他們的價值意識。楊義將周文歸入四川鄉土作家,就是對其小說獨特題材的充分肯定。鄉土文學在20年代的作家群集中在浙江,發展到30年代,完成了由東向西的漸進過程,出現了四川作家群,包括沙汀、艾蕪、周文、陳銓、羅淑等人。四川的鄉土小說使鄉土文學自20年生之后,不斷走向前進,同時也是30年代左翼文學向現實主義深化的重要標志和成果,周文作為其中的一分子,當然功不可沒。
周文曾說:“在一個較為偏僻的地方。我曾經在那里面生活過來,體驗過來,看見了些平凡的或不平凡的事件,生活在那里面的各種各樣人物且是邊荒一隅的人物,那生活于我究竟太熟悉了,決心寫它了。”正因為如此,在周文的作品中,就涌現了一批“邊荒一隅”的人――軍閥、官兵、商人、地主、牧師、知識分子、農民、丫鬟等。周文的小說通過展現川康人的悲劇,揭露和控訴了川康舊社會的黑暗,表現了自己對川康生活的痛苦思索,對現實生活的悲憤關注,也表達了他對現代文明所包涵的合乎歷史進步社會發展的現代觀念,對進步而開放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準則的強烈渴望和呼喚。在周文的作品中,他還習慣于把川藏邊境、西康高原和大梁山地區一代的方言語成功運用到作品中,采用“生動精彩”的詞兒、諺語、歇后語等,把生活在這里的川人性子里的直爽粗獷、話語中風趣幽默又飽含“辣味”的諷刺,生動形象、簡練中又寄予人物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展現得淋漓盡致,使小說語言呈現出新鮮活潑、簡潔明快、樸素生動、富有個性化的藝術魅力。
二
現實主義是周文始終堅持的創作原則和指導思想。周文有著不達真實不罷休的嚴謹的創作態度,他深知現實主義創作的根本特征在于按照生活本來的樣子,按生活自身的情理和邏輯去如實地描繪和再現,其核心就是“寫真實”,所以他的小說作品都是其經歷甚至親歷過的,他能夠毫無保留的客觀真實地反映生活,清醒地面對生活的本相與人性的惡質,以純客觀的他者姿態大膽的抨擊和揭露社會問題。周文曾說:“藝術作品決不是‘故事的編排’,‘政治的雜音’,而應該是以現實的人為主體。”周文確是一個在人性深層開掘上的絕對的寫實主義者,他暴露了非常態下人性潛藏的惡相與本質,以及常態下人們在瑣碎生活中的麻木與混沌,通過展現人的生存權利的被戕害,生命價值的被懸置以及在社會整體環境之中形成的麻木、絕望、虛無與彷徨的精神狀態,以此來表達他對人終極意義的痛苦思索和對現代文明的渴望與呼喚。周文長篇小說代表作《煙苗季》是其現實主義創作思想的最好詮釋。 《煙苗季》創作于1936年秋天,這是他個人創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唯一一部長篇小說。《煙苗季》長約十四、五萬字,取材于作者的親身經歷,講述的是20年代中期一個偏遠封閉的小縣城內發生的軍閥內部派系之間的傾軋變故,圍繞著禁煙委員和補充團長兩個肥缺,江防軍的旅長一派與曾私通“江防軍”的參謀長一派展開了一場有關權力的明爭暗斗。小說生動刻畫了官場與軍隊爾虞我詐的種種狡黠與殘忍,真可謂栩栩如生、刀刀見血,提供了20世紀20年代川康地區軍政一體、官匪難分的逼真畫卷。楊義評價《煙苗季》“以紛繁的線索,偶或難免節外生枝,以生動的人物性格,每每是細致逼真地揭示了川康地區軍閥為政的兇殘和險惡,揭示了軍閥之間割地分肥,軍閥內部上下猜忌、派系糾結,裙帶風、朋黨風滲透于每個組織細胞的封建性結構”,“小說于刀光劍影之中,讓人們感受到泥土混著血的藝術沉重感”。
周文反思過自己的創作,“創作不是為創作而創作,不是僅僅為了個人的愛好而創作,而是為了反映時代……因此,我對于當前的現實問題,開始提高到極其緊張的注意上面來了,對創作的態度也開始了新的認識。我拋棄了過去隨便寫的觀念,每回在鋪開紙,提起筆來以前,就自然而然要想一想,我這篇東西有什么意義?是為了什么?為了誰?”因此,雖然周文始終站在左翼政治家的立場上,但他抱有自己的文學主張,堅持寫自己熟悉的題材,立足現實,力求真實,大膽暴露當時人們日常經驗之外的別樣世界,且只是單純的暴露,不作其他任何意義上的引導。既充實豐富了“鄉土文學”的題材范圍,又體現出題材本身特有的文化內涵,包括社會人生的豐富性與復雜性,跳出了“左聯”內部文學創作趨向公式主義牛角尖的危機,體現出了周文對現實主義的特定理解與領悟。如小說《紅丸》,寫了一群貪官污吏,以戒煙為名,貪贓枉法的種種罪惡,在軍隊打敗仗的情況下,連與連、排與排之間,集體交換煙槍抽大煙的腐敗現象。作品展現了當時軍閥的貪婪、官吏的腐朽、軍隊的腐敗,深刻地、本質地表現了煙槍社會的本質特色,這是十分現實主義的。周文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從不作無病呻吟的自怨自艾,不去做縹緲虛無的浪漫幻想,他將雙腳深深扎入現實主義的土壤之中。
三
閱讀周文的小說,不會有強烈直接的價值引導的感覺,這很大程度上便是源于白描手法的成功運用。周文并不試圖去圖解政治,或是簡單地做某種思想的傳聲筒,其作品的傾向是隱蔽的,并不指點出來,而是從情節和場面的描寫中自然地流露出來。無論是自然社會環境的展現,還是人物情節的交代,周文總是原原本本地按照事件本來的面目進行客觀真實地表達,時刻注目于細節描寫的真實,真正做到了“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周文認為“無論人物或環境,都去寫它要害的地方,找他的特點,(至于怎樣找法,當然應該深入到現實生活里面,用最大的注意去分析每一種事件的特征,和認識每一種人物的特性)想來也就差不多了”。這一點在其惟一的長篇小說《煙苗季》中體現得最為明顯。《煙苗季》故事的敘述時間僅僅限于三天,小說的主要場景也只是在駐軍營地和旅長家兩處,在狹小的時空內,圍繞著禁煙委員的肥缺,近二十個人物悉數登場,展開了一場權力的爭奪戰。對于每一個主要人物,作者都抓住其獨有的特點進行素描,如主要人物旅長的出場,作者這樣寫道: “就在這時,前面的門檻那兒,首先跳進兩條高大的黃洋狗,一進門就直向太太的腿前跑來,接著門檻那里又跳進五六條黃色和白黑花的洋狗來,跑得地板轟隆轟隆價響。圍繞著太太跑一圈,就在窗邊分散開來了,站住,抖著舌條,望著前面。前面,旅長在天井那兒出現了。他的背后簇擁著十幾個掛盒子炮的弁兵。旅長是一個高個兒,油黑的圓臉,兩道濃黑眉毛,一個端正的鼻子,兩只發出射人的光的眼睛,頭戴呢博士帽,身穿灰織貢呢的長袍,緩緩地走了進來。旅長一進了門檻,那十幾個弁兵就分散開來,各自走進天井兩邊的臥房里去。”在這里,作者沒有任何硬性插入的敘述,只是一種十分自然的描寫,用一群狗來襯托旅長的威風,是精心的一筆,既真實又富有寓意,在波瀾不驚的自然描寫中,勾勒出了一個殺人不眨眼的軍閥形象,并且寫出了四川軍閥的極度腐敗。
周文小說的白描手法不僅運用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同時也體現在環境的描寫中。在中篇小說《雪地》中,周文運用白描手法,將那白得怕人的大雪山真實地展現在讀者的面前:連綿起伏滿目皆白,看不見星點綠色或黃色,飄飛而陰濕的白霧令人窒息,銀漾漾的白光刺人眼目,使人無法前行。那凍徹骨髓的酷寒――雪山行軍的一營隊伍出關時就凍死了兩排人,另有一排人被雪連腳趾都抹脫了成了廢人,二十來個人失去了手指頭;更有那輕則斥罵、重則將士兵踢下雪崖的兇蠻軍官……雪山行軍的描寫令人震悚,不寒而栗。
四
冷靜的敘述語言與客觀理性的表達。在周文的小說創作中,以積極姿態投入描寫,卻又有意識地與真實的川康保持一定的藝術距離,盡量避免過多自我情感的投入,因此,在周文的著作中,很少插入他的評語和說明。在其悲劇情感的表達上決不直抒胸臆,而是在真實具體的場景或氣氛描寫中讓主觀感受自然流露,這種平實、冷峻的寫實態度與創作方式使其作品體現了以生活為真實為根本的悲劇特色。
周文小說的冷峻風格是一種“表達的冷”,一種平實自然的冷靜,甚至一種不動聲色的冷酷。在其作品中,我們很難遭遇到曲折復雜的故事情節、驚險刺激的懸念技巧或者大段大段的議論抒情,他總是以客觀冷靜的平實筆調,來展示一幕幕的人生場景。小說《紅丸》講述的就是一個小小的辦公室內,眾人明爭暗搶一壇剛剛查獲的紅丸的片斷。圍繞著一壇小小的紅丸,小說中的人物各懷鬼胎,貪婪面目逐一展現。“張科員也走過來了,站在壇子邊。局長的胖臉聽差也走來了,站在門外邊,細著兩眼盯住壇子。李督察員也走來了,隔門伸進半個臉來。”紅丸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紅丸在閃光,于是所有人們的眼睛都閃光”。在這看似波瀾不驚的外表之下,都暗藏著緊張激烈的勢力斗爭,而這種由表面的平靜與內部情節的緊張所構成的張力,恰恰凸顯了周文小說的獨特魅力。
周文以客觀冷靜的姿態實踐自己全部的小說創作。在其作品中,我們很難看到作家自己的影子,周文始終游離于文本之外,以他者的姿態對事件的發展、人物的命運作冷靜的近于冷酷的敘述與描寫,不攙雜主觀的喜怒哀樂,愛憎嫌惡,這種冷峻的表達風格往往形成一種具有原始沖擊的震懾力。在《山坡下》中,關于賴老太婆死亡過程的描寫便典型表征了周文在表達方式上的冷峻風格。
參考文獻:
[1]周文.山坡下[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2]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3]周文.煙苗季[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4]周文.雪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