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 侵華日軍利用其優勢航空兵力對中國國土進行大規模無差別轟炸, 作為戰時陪都的重慶, 空襲的威脅更是步步緊逼, 對民眾進行防空知識和技能的教育與宣傳尤為迫切。國民政府組建了防空機構, 并通過文字宣傳、舉辦防空展覽和防空演習等多種宣傳方式給民眾灌輸防空常識。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同時激發了民眾的抗戰熱情, 成為戰時動員的重要環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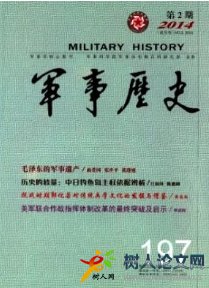
《軍事歷史》(雙月刊)創刊于1986年,由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主辦。 軍事歷史學術性刊物。主要發表軍事研究的成果,報道軍史研究的動態與信息。
現代立體戰爭, 其“勝負之決, 必以空軍”[1]。對于一個國家來說, “無空防即無國防”[2]。國民政府的防空建設起步較晚, 于1932年才開始籌備, 又著重于消極防空。蔣介石在《國民與航空》序上說:“今日之中國, 以國際局勢之緊張, 與內外環境之險惡, 全國國民, 應集中全力于自衛, 而自衛之要, 又當集中全力于空防之建設。”[3]當時中國因人力物力的限制不能充分建設積極的軍事防空, “敵國之空軍, 均較吾國強, 以吾國貧困之現狀, 欲迎頭趕上, 恐為難能, 然在此國難期間之今日, 其唯有先從速著手于消極防空乎!”[4]81938年, 國民政府移都重慶后, 日機的威脅進一步加劇。如何喚起山城民眾投入防空事業是國民政府的迫切之需, 為此, 國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民眾防空知識的宣傳和防空技能的教育。
關于抗戰時期重慶的防空問題, 學界前輩多有涉及。據筆者目力所及, 有關于防空建設的整體研究 (1) , 也有關于積極防空或消極防空的專項研究 (2) 。雖對防空宣傳問題多有涉及, 但都不甚詳盡。本文擬就對這一問題作一梳理, 以求教于前輩。
一、全面抗戰爆發, 重慶防空地位上升
(一) 國府遷渝, 空襲威脅加劇
現代戰爭的“總體化”趨勢, 使得無論前方還是后方, 無論政治經濟軍事重地還是偏僻鄉村, 無論前線戰斗人員還是婦孺老幼, 都有空襲的威脅。重慶雖為內陸城市, 亦有空襲之憂, 隨著國府遷渝, 重慶遭受空襲的危機大大加深。1937年11月20日, 國民政府發布《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 26日下午, 林森一行人率先到達重慶, 至1938年12月8日, 蔣介石也率領軍事委員會相關軍事人員遷駐重慶, 遷都過程基本完成。重慶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戰時首都, 從一個西南邊陲小城一躍成為了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中心, 也是國際矚目的焦點之一, 重慶的戰略地位自不待言。
日機自1931年轟炸錦州開始, 一路步步緊逼, 相繼對上海、廣州、武漢、南京等地狂轟濫炸, 日軍大本營《345號大陸指令》聲稱:“攻擊敵戰略及政略中樞時, 須集中兵力, 投入優良的飛機, 特別要捕捉、消滅敵最高統帥和最高政治機關。”[5]日本對重慶的轟炸也在1938年2月開始, 那時遷都工作尚未完全結束, 空襲的陰云就已籠罩在重慶上空, 所以“‘萬事莫如防空急’, 這話在重慶市尤其重要”[6]。
(二) 重慶防空力量薄弱
當時中國防空事業剛剛起步, 重慶的防空力量更是薄弱不堪。抗戰期間, 日本首先調用了450架飛機襲擊中國, 不久增至800架, 而中國當時國力弱小, 軍隊裝備低劣, 空軍雖有600架飛機, 單可參戰的不足半數, 使得中國的制空權在戰爭開始后不久即喪失殆盡。到1938年廣州、武漢陷落前夕, 中國空軍進入更為艱難的時期, 飛機數量從參戰時的200余架減少到135架, 這和日本擁有800余架性能先進的飛機相比形成天壤之別。在雙方歷次空戰中, 中國空軍損傷極重。1938年2月18日, 日軍首次轟炸重慶, 中國空軍10架戰斗機起飛迎敵, 結果被擊落6架, 擊傷4架;在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轟炸中, 日機分別以36架和27架襲渝, 雖中國空軍奮起反擊, 但是仍然損失慘重;1939年5月4日, 短短48分鐘內即炸死市民3 318人, 炸傷1 973人, 損毀房屋2 840棟又963間[7]。空襲的慘烈使得“無空防即無國防”理論更加深入人心, 力量本就十分弱小的中國空軍在連續作戰中蒙受著巨大損失。1940年9月13日, 璧山空戰中, 日本第一次將性能優越的零式戰斗機投入使用。“經此一役, 中國大后方的空軍基本損失殆盡。自此之后, 重慶上空的指揮權被日軍完全掌控, 中國空軍再也無力組織大規模的對日空戰。”[8]259
從消極防空方面來講, 雖國民政府興建了防空壕、防空洞等避難設施, 但是其中私人防空洞發展最快。1941年10月下旬, 各公私防空工事能為其中的461 080人提供掩蔽, 當時重慶人口為687 943萬人, 其中公共防空工事容量僅占總容量的27%[9]224, 所以能夠提供給一般市民的避難場所仍十分有限。而且更為艱難的是, 重慶教育水平極為落后, 民眾防空意識薄弱, 即使部分受過訓練的知識分子若要問及防空的意義, 也“雎盱而不能答”[4]9。一般民眾尚不知飛機為何物, 更勿論防空。
總之, 防空教育與宣傳對于防空建設尤為重要, 國民政府防空當局認為:“民眾對于防空意義的了解, 對于防空知識之灌輸, 防空技能之學習, 可以因普遍的宣傳而達到目的。”[10]37但是民眾防空知識貧乏, “欲建設國民的各項消極防空, 應先盡可能地利用防空展覽會、宣傳隊、電影、播音機、報紙、雜志、書報等, 作廣大的防空宣傳, 以引起敵愾同仇的觀念、國家民族的思想, 使全國無論是在城市或鄉村之居民, 無不能知道人人有空襲之危險, 人人有防空之責任, 且能深明防空之各項辦法及動作, 于急難之時, 各自從容避免損害”[10]81。
二、空襲威脅下的重慶積極開展防空宣傳
(一) 組織機構
1. 四川省防空協會重慶辦事處。
1935年, 國民政府在全國各省普建帶有全民宣傳性質的防空協會, 四川省防空協會應運而生, 同年8月1日成立的四川省防空協會重慶辦事處是重慶最早的防空機構, 由重慶市市長李宏錕和重慶警備司令李根固分別任正副處長, 下設宣傳組, 重慶防空宣傳教育開始有部門專司。1938年7月, 四川省防空協會重慶辦事處奉令改組, 將辦事處升格為省防空協會支會[9]147。但因為防空支會經費不能按月撥付, 會務工作實際上無形停頓。同年11月8日, 重慶市動員委員會宣告成立[11]。
2. 重慶市防空司令部。
1937年9月1日成立了重慶市防空司令部, 隸屬重慶市政府, 下設有宣傳委員會, 由國民黨重慶市黨部派員負責。1938年2月, 日機第一次轟炸重慶, “熱鬧山城, 頓成死市”[12]。為進一步加強防空建設, 國民政府將重慶市防空司令部改組為重慶防空司令部, 隸屬于航空委員會, 原宣傳委員會撤銷, 其業務并入第三科。
3. 陪都空襲救護委員會。
最初設立的名稱是重慶空襲緊急救濟聯合辦事處, 下設服務總隊, 根據《重慶市空襲服務救濟聯合辦事處服務總隊隊員服務須知》可知, 服務總隊平時服務工作就有“勸導人口疏散并解答疑難問題, 宣傳防空防毒救護等常識”[8]245。
此外, 全國防空工作的最高指揮機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航空委員會防空總監部也坐鎮重慶, 學校防空教材就出自于此。
(二) 防空宣傳的形式
1. 文字宣傳
防空宣傳大綱。防空宣傳大綱是最主要的刊物, 內容切要、簡明, 具有提綱挈領的性能, 印發至全黨、政、軍、文化、交通等機關社團, 使所有宣傳人員有所依據。1938年7月, 四川省防空司令部下達《防空宣傳實施綱要》, 對防空宣傳的要旨和事項、方式方法、組織形式、基本原則、時間與步驟等6個方面作出具體規定[9]354;1940年8月3日頒發《對敵機濫炸陪都宣傳大綱》, 要求陪都防空機構有關人員將“大綱”在各防空洞講述[9]355;等等。
防空報刊。抗日戰爭爆發前, 重慶報業已有一定的發展, 日報8家、晚報1家, 大大小小的通訊社有11家。僅在1939年重慶市報紙就有20家, 最盛時達22家, 通訊社方面有50余家[13]。即便是在“五三”“五四”大轟炸之后, 重慶報界組成的《重慶各報聯合版》也從未停刊一天。《新民報》《國民公報》《新華日報》《中央日報》等報紙常常刊載防空防毒知識, 同時報道戰況。防空雜志主要是研究防空學理與技能, 并促進各地防空之建設, 灌輸國民防空之常識。全國各黨、政、軍、文化、交通等機關社團按期訂購。1920年5月創刊的《航空》 (后更名為《航空月刊》) 雜志是中國最早的航空宣傳刊物。1934年1月, 航空署成立中央防空學校, 發行《防空》雜志, 該雜志成為當時指導全國防空建設的刊物。此外還有1939年創刊的《防空軍人》、軍事委員會防空處編《防空畫刊》、四川省防空協會主編的《防空季刊》, 1942年重慶防空司令部第四處編《重慶防毒通訊》, 1935年防空總監民防處編《現代防空》, 1940年防空總監部防空節出版《防空節紀念特刊》[9]358, 學者袁成毅先生在這方面多有研究[14]。
防空書籍。關于防空書籍, 既有當時有關防空機關編寫的普及性讀物, 也有民間專家學者的研究著述。比如:防空學校1936年編《防空常識》《民間防空之消防》, 商務印書館1937年出版《國民防空必讀》, 中山文化教育館1938年出版郭長祿著《論日機轟炸我國之違法》, 中國科學公司1941年出版黃立之翻譯的英國著作《城市防空》, 重慶防空司令部1938年編印《防空警報》, 重慶中山文化教育館1938年出版朱晨著《民眾防空論》, 重慶中山書局1938年出版商健行編《防空篇》等。此外, 還有一些防空小冊, 如《告本市各界同胞書》《市民防空須知》《防毒方法》《避難方法》等。這些著作涉及內容豐富, 有的介紹防空、防毒、疏散和警報信號知識, 有的講解空襲警報時注意事項和防炸避難的方法, 這些防空刊物對普及防空常識、減少空襲損失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防空標語。防空標語是防空業務的標志, 而且最易深入民間。防空機關通常將擬定的標語中選定最有刺激性, 最有意義, 且最簡單、明確、淺近者印發全國各機關和社團, 再由各機關社團制印張貼。在第一屆防空節紀念大會, 由防空總監部特別制定了許多防空標語, 如“防空是國民自衛工作, 努力防空就是努力救國”“防空技術科學化”“防空教育大眾化”等14條標語[9]359。當時各大報紙也會刊登防空標語。比如《重慶各報聯合版》就多次刊登, “夜間一聞警報, 各家燈光應一律熄滅或施行嚴密遮敝”, “燈火管制在于使敵機失卻投彈目標”, “夜襲時不要在室外吸煙, 更不可用電筒照射”[15]。《新華日報》曾刊載“警報時自備糧水”, “婦孺老幼, 迅速疏散”。
2. 特種宣傳
防空展覽會。1935年2月, 航空署在南京舉辦中國首次防空展覽, 因效果不錯, 向全國推廣。同年10月23日, 重慶市首次舉行大規模防空演習, 進行了反空襲和普及防空知識的宣傳, 內容分軍防、民防、防空情報三大部分。以后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防空防毒展覽, 參展的器材有航空器、防空兵器、炸彈、防空配備、防空監視、防空情報、防空通信、防空警報、消防、防毒、救護、交通管制、燈火管制、偽裝及煙幕、防空建筑設備等。影響較大的有以下幾次:1941年10月19—21日, 中蘇文化協會舉辦防空展覽, 因參觀人數眾多, 延長3天;1942年4月10日, 中蘇文化協會舉辦了為期5天的防毒展覽大會, 觀眾3萬人以上。鑒于展覽效果甚佳, 決定在各區分期巡回展覽。每區展覽2~4天, 晚上放映防毒電影。在19個地區巡回展覽共68天, 觀眾達20余萬人, 放映電影17次, 觀眾9萬余人[];1943年4月1日, 重慶防空司令部舉行防空擴大宣傳周, 在夫子池新運服務所舉行防毒展覽, 展出防毒器材、圖書、照片及統計表等, 前往參觀者達5 700余人。4月5日—8月12日先后在北碚、朝天門、江北彈子石、化龍橋等10處以及北溫泉和青木關舉辦3期巡回防毒展覽, 參觀者共計6萬余人。
防空演習。“防空事務在平時雖有相當之準備, 如至戰時敵機空襲, 民眾究竟應如何應付仍是盲然”, 組織防空演習是提高訓練水平的重要形式, “既可審視設施情形, 并可喚起民眾覺悟”[16]。1937年10月23日舉行重慶第一次全市防空演習, 午前12時半至午后2時25分為演習敵機空襲渝城, 午后6時50分至8時10分為演習燈火管制。此晝夜二次演習, 成績均異常良好[17];1938年1月24日, 日機首次轟炸宜昌后, 重慶市政府于2月16日舉行了第二次全市防空演習, 側重消防方面, 計演習3日, 演習內容包括消防人員接到警報后集中待命, 假設敵機在碼頭、市區等地投下炸彈, 消防隊救護情形[18]。1940年8月, 重慶防空司令部以“對敵空軍陸戰隊及防止奸宄暴動”為主題舉行幕僚演習, “使各級幕僚及部隊干部熟練非常時期之作業, 并相互間之聯系, 為爾后實戰時之準備”[19];1941年5月9日, 重慶市警察局在都郵街廣場舉行防火大演習……此外在川師操場、江北覲陽門河壩、南岸獅子河壩、沙坪壩磁器口河壩等地同時舉行防火演習, 并定10日下午3時起至6時舉行防火游行[20];1942年2月, 重慶市還舉行了“空軍驅逐部隊與防空全體機構協同運作以擊退空襲敵機之攻防演習”, “教練監視哨發現識別飛機判斷飛行高度報告情報所”, “教練情報所關于驅逐機動作及指揮高射武器以便隨時應戰”[21]。防空演習以逼真的場景給人們以身臨其境的感覺, 對于群眾切身感受空襲的威脅有著直觀的體驗。
防空節。為紀念1934年11月21日在南京的首次防空演習, 1940年7月25日國民政府將11月21日定為防空節。陪都共舉辦過九屆防空節, 前五屆防空節因重慶作為陪都, 紀念活動較為隆重。隨著抗戰結束, 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后, 重慶第六屆至第九屆防空節雖仍舉行活動, 但規模大不如前。1949年11月3日重慶即將解放, 第十屆防空節就此作罷。前幾屆防空節紀念都受到國民政府的重視, 除了黨、政、軍要人, 如黃鎮球、賀國光、劉峙、吳國楨等紛紛出席防空節紀念大會外, 還有英美駐華大使、空襲防護機關和團體代表等計5 000人左右, 為期3天。每逢防空節, 均通過散發傳單、張貼標語、舉辦展覽、廣播演講、放映影片等方式進行防空宣傳。防空節宣傳要點每一屆雖各有側重, 但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揭露日機空襲罪行;宣傳防空工作的重要性及防空節意義;講解抗日戰爭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通報陪都防空建設情況和急需解決的問題;傳授防空襲及防毒常識;動員社會各界人士協助防空建設, 參加防護工作[9]363。
學校教育。國民政府的防空教育分為干部教育和社會教育。1934年1月1日, 國民政府在杭州筧橋成立防空學校, 這是中國第一所培養防空事業人才的專業學校, 由留學德國考察學習防空的黃鎮球任校長。中央防空學校召集地方公務人員、人民團體職員受訓, 學習飛機槍炮、情報、救護等知識, 受訓結束之后, “凡去防空學校受訓人員分別到各基層單位、團體、學校等進行防空知識的宣傳教育”。同時, 還在普通學校增加防空課程, 各級學校有相應的防空課本, 防空總監部民防處主編《中學防空讀本》《高小防空讀本》《國民防空讀本》《兒童防空講演》[22]2等教材下發各級學校, 使小學生知道空襲的慘禍、避難的方法、服從紀律等, 使中學生知道救護及防毒消防等各種常識, 擔負一部分的防空責任, 使大學生知道各種科學中研究防空的方法如毒氣、防毒、防空兵器、飛機制造等, 以貢獻給政府和民眾[23]2。黃鎮球等人還撰文詳細介紹了防空與地理、歷史、算學、公民、理化、建筑、文學、植物、醫學等學科之間的關系, 以豐富防空知識的研究[23]2。通過對國民進行防空教育, “建立起心理的防空”, “提高存亡生死的奮斗精神”, “負荷起生存自衛的神圣責任”[24]73。戰前的人民防空研究班召集各省市的在職人員施以防空教育, 以應對戰時的需要, 但隨著戰局日益惡化, 交通困難, 采取召集一地施教的方式有諸多不便, 國民政府決定開辦民防游教班, 采取游動教育的方式, 到川、滇、黔、陜、甘、寧、青、桂、粵、湘、贛、閩等省施教[22]2。
其他方式。除此之外, 國民政府還通過口頭宣傳、繪制防空防毒圖片或掛圖、播放防空電影、排練防空戲劇、編寫防空歌謠等藝術宣傳方式, 因時因地進行宣傳。例如, 1941年國民黨重慶市黨部責令有關部門, 利用敵機空襲時在防空洞內宣傳防空秩序、防空防毒知識、公民衛生常識和國民精神、抗日英雄故事、歷史愛國故事、國內外時事等防空教育內容。
三、重慶防空教育與宣傳的意義
(一) 客觀上減少了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
抗戰初期, 不少重慶市民在空襲時因好奇而駐足觀看, 因之喪命的人不在少數。到1938年2月18日, 日機首次空襲重慶, 一般重慶民眾皆“以為建設防空, 全是政府或軍警的事”, 與自己“漠不相關”。鑒于此, 防空司令部深知由于“防空舉辦未久, 人民對于防空知識尚屬淺薄”, “關于宣傳事項, 最為重要”, 于是組織了“宣傳隊十大隊”, 每周“輪流在市區宣傳, 用以普及防空知識與意識”[25]。1939年“五三”“五四”轟炸后, 空襲的慘烈讓民眾心理震動, 大部分人開始聽從政府命令, 鎮靜有序, 積極補救。“六五大隧道慘案”后, 國民政府各防空部門開始積極整改, 同時加大力度對民眾進行防空知識的宣傳教育, 使廣大民眾認識到:“一旦發生事變, 不致慌張, 若遇敵機投擲炸彈, 能從容避難。遇房屋著火, 能迅速撲滅, 遇毒瓦斯, 亦能設法消毒、防毒, 無論當時情形如何慘酷, 均能從容應付, 以減少損害。”
據統計, 在1939年日機1枚炸彈要炸死或炸傷市民5個半人, 1940年1枚炸彈炸死或炸傷1人, 1941年是3個半炸彈炸死或炸傷1個人[26]。這樣的統計數據雖不能直接表明防空宣傳教育的良好效果, 但是生命財產損失的減少是官民合作的結果, 增強民眾防空意識, 至少能減少因無知帶來的不必要損失。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在戰時到重慶采訪, 曾對重慶防空有過記載:“重慶防空, 世界無出其右者”, 因為“民眾一聞警報, 即進入防空洞, 一如學校上課, 魚貫而入, 秩序井然”。即使言語或有夸張, 但多少也反映了這樣的事實。
(二) 激發抗戰熱情, 支援抗戰
防空宣傳教育不僅是教會民眾在空襲災難來臨時保全自己及他人的方法和技能, 而且使人們明白空襲的危害, 深諳這場戰爭的性質, 認識罪魁禍首, 從而激發抗戰熱情, 積極投身抗戰大業中。
1940年春, 廣大市民響應防空當局開展的擴大防空洞運動, 僅3月份就同時有120處動工興建防空洞、壕, 防空洞容量成倍增長, 逐漸與市民的防空要求相適應[24]157。1941年11月, 重慶市政府通過《重慶市市民自建防空洞辦法大綱》, 決定立即著手籌建“市民自建防空洞委員會”, 負責辦理增建防空洞, 籌劃向市民和商家“攤認”“樂捐”建筑防空洞經費等事項。12月22日, 重慶市政府召開發動市民修建防空洞會議, 決定立即發動市民增建總容量為10萬人的防空洞[9]220。截至1943年11月, 重慶市防空洞管理處統計:全市共有各類防空工事1 823個, 總長度8.4萬米, 總容量445 000人;其中公共防空工事有282個, 長度共計1.9萬米, 容量共計112 600人;私有防空工事有1 541個, 長度共計6.5萬米、容量共計332 400人[9]221。重慶防空工事的大量增加離不開廣大市民的積極支持參建。
開展獻金、獻機運動是抗戰大后方人民反轟炸的一個創舉。日軍的狂轟濫炸使廣大民眾認識到建設積極防空, 才是消除敵機轟炸的根本方法。“獻機運動”是從1939年3月中國空軍出版社建議將義賣金捐款購買“義賣號”飛機開始的, 先后有“兒童號”“劇人號”“記者號”“榮譽號”“新軍人號”“青年號”“婦女號”等各界捐購的飛機。大后方廣大民眾發起的“獻機運動”極大地調動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 有力地支持了防空建設。
(三) 培養民眾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
防空宣傳教育是國民政府消極防空建設中的重要舉措, 是抗戰動員中的一環, 同時也是官民合作的重要體現, 若依教育的理念, 國民政府可稱作施教者, 民眾便是受教者, 施教者與受教者的良性互動才能創造出最佳的教育效果。如果說民眾從最開始的“漠不關己”到后來響應政府指令, 一時間“遷往鄉間者甚眾”, 是因為空襲慘象的刺激而出于趨利避害的本能反應, 那后來許多主動積極投身挽救民族危機的抗戰大業之行動便超出了這個層次, 是政府和人民的一次良性溝通, 也是艱難戰爭時局下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積聚的結果。正如在重慶只住了3個月就遭受了40余次轟炸的林無雙寫下她在重慶的觀感:“奇怪的是當戰爭拖下去時, 中國的士氣越來越高了。當收復了一座城池, 在空襲后就有提燈會和游行來慶祝。端午節照樣有成千的人觀看龍船比賽。我們依然舉行慶祝, 照樣生活著。孩子們在解除警報后, 立即拿起書包到學校去。夜襲以后人們又在第二天六點或七點鐘起身工作。還有的孕婦在防空洞里生產孩子。空襲不能破壞我們的幸福。炸彈怎能摧殘我們的士氣, 怎能摧毀我們的精神?它可以落下而且爆炸, 但我們無論如何卻要抗戰到底。”[27]
重慶的防空宣傳事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也面臨許多困難。一方面國民政府各管理機構重疊, 體制混亂, 貪污腐敗現象嚴重, 令防空事業的推進多受干擾;另一方面是民眾防空意識薄弱, 教育落后, 受傳統觀念束縛, 覺悟程度有限。這些都使得防空宣傳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參考文獻
[1]王杰人.現代防空之必要[J].防空雜志, 1935 (1) :256.
[2]黃鎮球.中國之防空[Z].1935:2.
[3]蔣中正.國民與航空[M].上海:中國文化學會出版社, 1934:2.
[4]黃鎮球.我國防空建設之動向[J].防空, 1935 (1) :8-9.
[5]前田哲男.重慶大轟炸[M].李泓, 黃鶯, 譯.成都: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 1989:59.
[6]本市防空問題[N].國民公報, 1937-11-20 (1) .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