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于地區高質量發展會隨時間變化及政策調整而呈現不同層次,因此,文章基于速度特征視角來測評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水平。依據五大發展理念及區域發展特點,從創新能力、產業活力、經濟實力、城鄉合力、保障能力、生態潛力六個維度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利用熵值法、具有速度特征的動態綜合評價模型,對2015—2019年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靜態、動態測評。結果表明: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總體趨勢良好,但各區縣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其中江蘇最為凸顯而安徽最不明顯;高質量發展水平高的區縣多集中在蘇浙兩省,而高質量發展水平增速快的區縣主要集中在安徽;通過對靜態、動態評價結果進行綜合分析,可將各區縣劃分為“標桿型、潛力型、衰退型、后進型”四大類,并提出了相應的差異化發展策略。
關鍵詞: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動態測評;速度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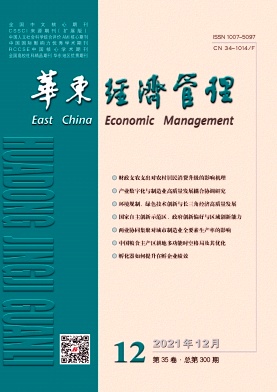
項寅; 李琳歆; 張佳玥; 韓琳; 劉天雯; 丁曉文 華東經濟管理 2021-12-22
一、引 言
我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既是適應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必然要求,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躋身發達經濟體的關鍵舉措。長三角作為我國經濟最發達、創新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如何率先實現高質量發展并對其他地區起到示范引領作用,成為該地區面臨的重要問題[1]。從區域結構看,縣域是支撐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單元,縣域高質量發展不但關乎區域高質量發展全局,也關乎鄉村振興、小康建設等國家戰略實施[2]。雖然當前長三角縣域經濟領跑全國其他地區,但仍存在產業同構[3]、區域發展不平衡[4]、生態環境相對脆弱[5]等問題。為此,如何科學測評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水平,對制定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相關政策意義重大。
作為當前社科研究熱點,高質量發展測評已有較多研究。第一,在評價指標方面,學者們依據高質量發展的不同內涵來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其中,少數學者從宏觀、中觀和微觀視角解析高質量發展內涵,并圍繞社會、產業和要素三大層面構建我國區域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6-7];多數學者將新時代五大發展理念作為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要求和評價準則,主要圍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維度,依次構建和完善我國各大區域、省域、市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8-11]。第二,在實證測評方面,已有學者主要采用靜態評價方法,如潘桔和鄭紅玲(2020)[12]圍繞新時代五大發展理念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采用TOPSIS 方法對區域高質量發展加以測評,發現其呈現“東高西低”的空間分布特征;凌連新和陽國亮(2020)[13]圍繞經濟、創新、協調、綠色等方面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熵值法對粵港澳大 灣 區 11 大 城 市 進 行 測 評 ;鄭 耀 群 和 葛 星(2020)[14]從經濟、科技、民生、社會、綠色五大維度構建指標體系,運用投影尋蹤法測評我國省域高質量發展水平。目前采用動態評價方法的研究還很少,韓永輝和韋東明(2021)[15]結合省域面板數據,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GPCA)研究了省域高質量發展的動態趨勢及發展指數排名變化。
已有研究雖已取得豐碩成果,但仍有不足: ①評價對象上,現有高質量發展測評研究集中在區域、省域、市域和產業層面,鮮有涉及縣域層面,事實上縣域作為區域高質量發展的神經末梢與重要環節,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鑒于縣域數據獲取難度較大,目前僅王薔等(2021)[2]從理論層面探討了我國縣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構建,但并未開展實證研究,也未在指標體系中凸顯區域特色。②評價方法上,已有研究多采用靜態評價方法,雖能得出各地區高質量發展的排序情況,卻難以揭示被評價對象動態發展變化的特征與趨勢。由于高質量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因此還需采用動態評價方法:例如某些地區發展水平連續4年小幅增長,卻在第5年出現大跌,這就需要通過計算變化速度的狀態來綜合測度該地區在連續5年內的總體發展水平究竟是升還是降,繼而制定相應的發展對策;又如經常會有一些發展水平偏低的地區,在短期內呈現加速發展并成為領先發展地區,這就需要通過計算變化速度的加速度來評估其發展趨勢及后勁,繼而給予相應程度的政策與資金扶持。特別地,若將靜動態評價方法聯合使用,還能識別被評價對象的發展類型(有些地區當前評價值高,卻有快速下降趨勢;有些地區當前評價值低,卻有良好發展趨勢;等等),可為政府制定差異化發展策略提供決策支持,有助于全面推進區域高質量一體化發展。
不同于已有研究,本文以長三角城市群 26 市 104個縣域單位(包括蘇浙皖3省年鑒所列的全部縣級市、縣和部分郊區;因上海年鑒中的區縣數據缺失過多,故不包括上海所屬區縣)為研究對象,首先基于 2015—2019 年面板數據,采用熵值法計算縣域高質量發展的各年靜態評價結果;隨后結合具有速度特征的動態綜合評價模型測算速度變化狀態和趨勢;最后對靜態、動態測評結果進行綜合分析,為相關政策制定提供有價值參考。
二、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
由上述可知,已有研究大多圍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維度構建我國區域、省域、市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為契合自上而下的評價要求,本文仍將新時代五大發展理念貫穿于縣域指標體系的始終,在借鑒已有省域、市域指標體系[6-11]的基礎上,充分考慮長三角區域特色,瞄準當前產業同構、區域發展不平衡、生態環境相對脆弱等重點矛盾。因此,基于系統性和全面性原則,從創新能力、產業活力、經濟實力、城鄉合力、保證能力、生態潛力六大維度構建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的一級評價指標。其中,創新能力是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的驅動力,產業活力是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經濟實力是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考量,城鄉合力是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路徑,保障能力是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生態潛力是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進一步圍繞上述6個一級指標構建二級指標,鑒于縣域數據的獲取難度,本文在兼顧數據可獲取性、指標體系完整性的前提下對評價指標體系加以完善,具體見表1所列。創新能力采用專利指標反映;產業活力通過各產業占GDP的比重反映;經濟實力通過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經濟密度反映;城鄉合力從消費、收入、建城區面積三方面反映;保障能力從醫療、交通、公共預算支出三方面反映;生態潛力用綠化覆蓋率、空氣質量加以反映。
數據來源方面:指標X8、X13相關數據從2016— 2020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鑒》獲取;指標X14相關數據從國家生態環境部數據中心獲得;其余指標數據從 2016—2020 年《中國縣域統計年鑒》《江蘇省統計年鑒》《浙江省統計年鑒》《安徽省統計年鑒》獲得。整個數據收集過程耗費兩個多月,特別是安徽縣域數據(指標X1、X2、X8、X9、X11、X12、X13)缺失嚴重,需要從各市統計年鑒、政府工作報告中逐一查詢。對少數缺失的縣域數據,用所屬地市數據或相關縣域數據的平均值替代。
三、速度特征視角的動態綜合評價模型
縣域高質量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相關特征可通過變化速度的狀態和趨勢反映。在此通過變化速度的狀態來描述連續時間段內被評價對象的高質量發展總體變動究竟是升還是降;通過變化速度的趨勢來反映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變化的速度究竟為勻速、增速還是減速。采用文獻[16]提出的具有速度特征的動態綜合評價方法:首先用熵值法測得歷年縣域高質量發展的靜態評價值;其次在速度、加速度定義基礎上,測度變化速度的狀態和趨勢值;最后依據狀態與趨勢算出動態綜合評價值。
(一)靜態評價
基于各年截面數據,采用熵值法對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指數進行靜態測評。
(二)變化速度狀態分析
對p個待測評縣域對象S1,S2,…,Sp,采用熵值法測得各區縣 Si在 tj時期的靜態評價值 r(ij i=1,2, …,p;j=1,2,…,n+1)后,可得到評價結果的時序矩陣R如下: R = [ rij ] p ( n + 1 ) =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r11 r12 ⋅ ⋅ ⋅ r1( n + 1) r21 r22 ⋅ ⋅ ⋅ r2 ( n + 1) ? ? ? rp1 rp2 ? rp ( n + 1) (1)矩陣R包含了長三角縣域歷年高質量發展水平的靜態評價值。若用v(ij i=1,2,…,p;j=1,2,…,n)表示第i縣在相鄰時序[tj,tj+1]內的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速度,則在靜態評價矩陣R基礎上,進一步得到變化速度的時序矩陣V,具體如下: V = [ vij ] pn =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v11 v12 ⋅ ⋅ ⋅ v1n v21 v22 ⋅ ⋅ ⋅ v2n ? ? ? vp1 vp2 ? vpn (2)矩陣 V 反映了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相鄰“離散”時段的變化速度,其中:vij =( ri, j + 1 - rij) / ( tj + 1 - tj);i=1,2,…,p;j=1,2,…,n。vij >0表示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呈增速狀態;vij <0表示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呈減速狀態;vij =0表示相鄰兩年的高質量發展水平無變化。
然而,任意相鄰且“連續”的時段內,縣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變化速度并非某一固定值,而是具有時變特征,并在該時段內形成某“運動軌跡”,這就使得上述vij無法系統全面地反映變化速度在相鄰 “連續”時段內的累積變化狀態。為此,借鑒物理學中的速度定義,從信息集結視角構建變化速度狀態的表達式: Si v ( tj,tj + 1 ) = ∫tj tj + 1 [ vij + ( t - tj )( vi, j + 1 - vij ) ( tj + 1 - tj ) ]dt (3)其中,變化速度狀態Si v ( tj,tj + 1 )表示第i縣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變化速度在相鄰時段[tj,tj+1]內的累積狀態。Si v ( tj,tj + 1 )>0表示該時段內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總體變動狀態為“增加”;Si v ( tj,tj + 1 )<0表示該時段內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總體變動狀態為“減少”。
(三)變化速度趨勢分析
進一步結合物理學中的加速度定義,構建被評價對象i在時段[tj,tj+1]內變化速度狀態的加速度表達式,具體如下: aij = ì í î ï ï 0, tj + 1 = 1; vi, j + 1 - vij tj + 1 - tj , tj + 1 > 1 (4)其中:i=1,2,…,p;aij表示第i縣在時段[tj,tj+1]內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速率的線性變化率。aij>0 表明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變動呈增速趨勢;aij<0表明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變動呈減速趨勢;aij=0表明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變動為勻速。由于被評價對象的變化速度狀態將在不同時段內呈現出不同水平,因此還需要結合激勵控制線的動態理論來進一步修正 aij,才能使最終評價結果中包含進步、退步等增量信息,以更好地實施動態測評。為此,進一步通過構造式(5)來測度變化速度的趨勢。 η( aij ) = σ ( 1 + e ) -aij (5)其中,η ( ⋅ )是關于aij的單調遞增函數,其值域大于零且存在上下界。aij趨近正無窮時,η ( aij)趨向σ;aij趨近負無窮時,η ( aij)趨向0;aij取值為0時, η ( aij)=σ 2。因此,通過式(5)就可實現不同變化速度狀態的獎勵與懲罰修正。參考文獻[16],設σ=2 時有:若aij>0,存在η ( aij)>1,表明速度變化趨勢呈上升狀態并給予“獎勵”;若aij<0,存在η ( aij)<1,表明速度變化趨勢呈下降狀態并給予“懲罰”;若aij= 0,存在η ( aij)=1,表明速度變化趨勢穩定故而不給予獎勵或懲罰。
(四)動態綜合評價
縣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動態綜合評價結果取決于變化速度狀態、變化速度趨勢兩者的共同作用。為此,結合物理中的力學理論,可將第i縣在時段[tj,tj+1]內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變化速度狀態 Si v ( tj,tj + 1 )視為物體的“質量”,并將與之對應的變化速度趨勢η ( aij)視為物體的“加速度”,則根據物理學定律可構建出第i縣在時段[tj,tj+1]內動態綜合評價值的表達式Zi j。 Zi j = Si v ( tj,tj + 1 ) η( aij ), i = 1, 2,…, p; j = 1, 2,…, n - 1 (6)將第i縣在各時段[tj,tj+1]的動態綜合評價值Zi j 加總后,可得到整個時段內的評價值Zi 。公式如下: Zi =∑ n j = 1 Zi j , i = 1, 2,…, p; j = 1, 2,…, n - 1 (7)其中,Zi >0表示第i縣在連續時段內的高質量發展水平總體上呈上升態勢;Zi <0表示第i縣在連續時段內的高質量發展水平總體上呈下降態勢; Zi =0表示第i縣在連續時段內的高質量發展水平很平穩。
四、實證分析
基于上述評價指標體系,首先采用熵值法對 2015—2019年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靜態測評;進一步依據上述動態評價模型測算縣域高質量發展變化速度的狀態和趨勢;最后從靜、動態兩方面綜合分析縣域高質量發展水平,劃分類型并提出對策。
(一)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的靜態測評
利用熵值法進行靜態測評,通過對表2測評結果進行分析,可初步展示各年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的實際水平及區域內的差異性。
(1)從縣域尺度看。地處滬寧杭都市圈內的昆山、江陰、張家港、鄞州和余杭歷年靜態評價值最高,始終占據高質量發展前5名,該結果與歷年百強縣榜單較接近,原因是這些地區依托便利的交通和靈活開放的政策,憑借外向型經濟和本土民營經濟的共同發展,較其他縣更快實現了經濟強、百姓富、社會文明程度高等目標;而地處皖南的懷寧、宿松、望江、定遠和樅陽則始終位列高質量發展的末 5位,原因可能是安徽省內資源與政策過多傾向合肥,同時地理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這些地區的外貿發展和人才集聚,因此政府需加強對這些地區的政策或資金扶持,以免阻礙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全面推進。
(2)從區域尺度看。2015—2019 年長三角地區中,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縣域靜態測評的整體平均值分別為0.275 0、0.320 4、0.164 1,說明該5年中浙江縣域高質量發展的整體平均水平高于江蘇和安徽,原因可能是江蘇蘇北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蘇南地區的貢獻值,而浙江則依靠各地民營企業帶動全省經濟發展,近幾年更是形成了以大數據為核心的科創特色。對數據進一步分析發現,在創新能力、城鄉合力、生態潛力這三個維度方面,浙江縣域得分均值明顯高于江蘇縣域,但江蘇縣域在經濟實力維度方面的平均得分則明顯高過浙江縣域。此外,區內高質量發展存在不平衡性,其中江蘇最為凸顯而安徽最不明顯,僅以2019年為例,蘇浙皖縣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數的標準差分別為 0.125、0.081和0.027。對江蘇而言,其原因主要由江蘇南北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所造成,蘇南地區憑借外資企業拉動經濟大幅增長,而蘇北地區則面臨人才流失、經濟發展受限等問題。因此,如何縮小蘇南與蘇北發展差異,通過蘇南帶動蘇北地區高質量發展,仍是意義重大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的動態測評
由于表2僅為不同時段下的截面評價結果,無法全面表現出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的動態變化特征,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對縣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變化速度狀態、趨勢進行測評。
(1)基于表 2 靜態評價結果,依據公式(2)、公式(3)并結合文獻[16]的計算方法,計算出各區縣 i在時段[tj,tj+1]內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變化速度狀態 Si v ( tj,tj + 1 ),見表 3 所列。評價值有正有負,正值表示被評價對象在特定時段內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總體變動狀態為“增加”,負值則相反。由表3可知,長三角104個被測評區縣中,共有21個區縣(淺灰色)在評價周期內的變化速度狀態始終為正,其中江蘇7個、浙江2個、安徽12個,說明其在不同時段內較之自身而言,其高質量發展水平始終保持上升狀態,具有良好發展勢頭;相反,共有16個區縣(深灰色)在評價周期內的變化速度狀態始終為負,其中江蘇3個、浙江10個、安徽3個,說明其在不同時段內較之自身而言,其高質量發展水平始終保持下降狀態,對高質量發展的全面推進起到阻礙作用,須加大扶持力度以提升發展水平。總體上看,表中被標注淺灰色的區縣數量多于深灰色的區縣數量,表明考察期內高質量發展水平總體變動狀態為“增加”的區縣多于為“減少”的區縣,說明近幾年高質量發展相關政策起到一定效果;此外,被標注淺灰色的區縣中,安徽省內區縣數量占比 51%,說明安徽縣域在高質量發展中的潛力較大。
(2)由于變化速度狀態僅能反映特定時段內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總體變動狀態為“增長”還是“下降”,無法測得該時段內高質量發展水平究竟為“均速增長”“增速增長”還是“減速增長”等,因此還需在表2靜態評價結果基礎上,依據式(2)和式(4)測度各區縣i在時段[tj,tj+1]內高質量發展水平速度變化的加速度aij,進一步依據式(5)測得變化速度趨勢η ( aij),結果見表4所列。評價值大于1時,表明被評價對象在特定時段內高質量發展水平的速度變化呈“增速”趨勢(增速增長、增速下降);評價值小于1時,表明速度變化呈“減速”趨勢(減速增長、減速下降);評價值等于1時,表明均速增長或勻速下降兩種情況。
由表4可知,長三角104個被測評區縣中,共有巢湖、來安、鳳陽、東至和太湖5個縣(淺灰色)在評價周期內的變化速度趨勢評價值始終大于1,說明其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變化速度始終呈“增速”狀態。進一步對應表3可知,由于巢湖、來安、鳳陽3縣的速度變化狀態值均大于0,繼而表明3縣在評價周期內高質量發展水平始終保持“增速增長”狀態,表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和潛力。一方面,巢湖位于合肥、蕪湖兩市之間,受兩市經濟輻射帶動作用強,加之其擁有安徽第一大內河港口巢湖港,因而具有較好發展潛力;另一方面,來安、鳳陽均是南京“一小時都市圈”主要成員,區位條件優越,又在旅游業、生態農林方面具備發展優勢,故保持著高質量發展的持續增速狀態。相反,僅有新昌、東陽2縣(深灰色)在評價周期內變化速度趨勢評價值始終小于1,說明其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速度始終呈“減速”狀態。雖然2縣均處于浙江丘陵地帶,在區位和交通方面優勢并不明顯,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其工業發展,但可依托得天獨厚的自然風景,圍繞“文旅融合”等主題進一步開發旅游資源,以加速實現高質量發展。
(3)將速度變化的狀態、趨勢進行聯合考慮,依據式(6)、式(7)測得各區縣i在整個評價周期內的動態綜合評價值Zi ,排名結果見表5所列。綜合評價值為正,表明對應區縣在評價周期內的高質量發展水平總體呈上升態勢;綜合評價值為負則相反。總體來看:①綜合評價值為正的區縣有56個,評價值為負的區縣為48個,表明評價周期內高質量發展呈上升態勢的區縣多于呈下降態勢的區縣,整體發展態勢較好;②動態評價排名前 10 的區縣(鳳陽、海門、來安、海安、明光、全椒等)多是在靜態評價(表2)中排名靠后的區縣,表明這些區縣雖然當前高質量發展水平偏低,但已開始不斷發力和追趕,將有助于區域內發展不協調的改善。對于這些區縣,須繼續保持其發展優勢,把握國家發展政策,穩中求變。靜態評價中排名第1的昆山,在動態排名中僅位列第74,表明昆山在經歷過去20年快速崛起的階段后,已逐漸進入邊際增長率遞減的階段,需進一步拓寬發展路徑,提高發展質量。由此可見,利用具有速度特征的動態綜合評價模型測評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水平,得到了傳統靜態評價模型所無法獲得的結果,較好地彌補了傳統靜態測評研究的局限性。
(三)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的靜態、動態綜合分析
為綜合全面分析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狀況,將靜態、動態評價值反映在二維坐標圖中,橫縱軸分別用水平和垂直的粗點劃線表示。如圖1所示,橫軸表示動態綜合評價值,原點為 0,從左至右動態測評值依次遞增;縱軸表示各年靜態評價的平均值,原點設為平均水平,從下至上靜態評價值依次提升。不難發現,位于橫坐標上方的區縣數量遠小于橫坐標下方的區縣數量,表明大部分區縣的高質量發展水平尚未達到整體平均值,昆山等個別縣的高質量發展水平遙遙領先,兩極分化現象尤為明顯;位于縱坐標右側的區縣數量略多于縱坐標左側的區縣數量,表明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上升態勢的區縣數量略多于呈下降態勢的區縣數量。
根據圖1,坐標系的兩個維度將104個區縣分布在四個象限。第一象限僅包含鄞州和余杭,表明其高質量發展水平高且呈現增長態勢,這2個區縣表現出“標桿型”特征,引領其他地區共同實現高質量發展;第二象限包含區縣數量最多,均為高質量發展水平低但增速快的區縣,表現出“潛力型”特征,需對其進行大力扶持與培育,其中安徽的大部分區縣處于該象限內,反映出安徽縣域高質量發展的良好態勢和巨大潛力;第三象限也包含較多區縣,均為高質量發展水平低且發展水平呈下降趨勢的區縣,表現出“后進型”特征,需利用各種方式實現保質增效,以避免其成為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的阻力;第四象限包含昆山、江陰、張家港、常熟、太倉、嘉善等高質量發展水平高但存在下降趨勢的區縣,表現出“衰退型”特征,特別地,這些區縣的經濟高度發達并集中在蘇錫、杭嘉兩地,尤其是嘉善和常熟的高質量發展水平下降趨勢較明顯,須加以重點關注。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構建了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利用2015—2019年統計數據,對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評,得到以下結論:①由靜態測評可知,長三角已形成一批發展質量較高的區縣,包括昆山、江陰、張家港、鄞州、余杭等,主要集中于滬寧杭都市圈內,而位于皖南地區的定遠、懷寧、宿松、望江和樅陽等則排名靠后。此外,浙江縣域高質量發展的整體平均水平高于江蘇和安徽,省內各縣的高質量發展仍存在不平衡性,其中江蘇最為凸顯而安徽最不明顯。②由動態測評可知,近年來長三角縣域高質量發展整體態勢良好,說明相關政策實施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別是鳳陽、來安、巢湖、明光、全椒等安徽部分高質量發展水平相對偏低的縣,已呈現出全力追趕和相關指數增速增長的良好勢頭;而昆山等當前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的縣,近幾年邊際增長率呈下降趨勢,需要打破發展的“天花板”,實現更高質量發展。針對上述結論,本文認為全面實現長三角縣域高質量一體化發展,還需充分考慮靜態、動態測評結果的不同特征,有針對性地實施差異化發展戰略:①針對同時具有較高靜態、動態測評結果的“標桿型”地區,如余杭、鄞州等,這些地區當前發展良好且具有較強的自我調節能力,應進一步落實新發展理念,全方位融入長三角,結合區域發展特色并重點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保持已有增長態勢; ②針對靜態測評結果高但動態測評結果低的“衰退型”地區,如昆山、常熟、張家港、太倉等,這些地區曾憑借地理、人才優勢和政策便利,通過招商引資實現經濟騰飛,為高質量發展打下良好基礎,但隨著積累量增加,逐漸出現邊際增長率遞減的狀況,同時存在關鍵技術不強、創新水平不高等局限,應在外資引入和利用的同時大力培育本土企業及新興產業,提高創新能力并形成地方性發展特色,以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③針對靜態測評結果低但動態測評結果高的“潛力型”地區,如鳳陽、來安、明光、海門、海安等,近幾年通過承接長三角發達地區產業轉移拉動經濟增長,雖然發展指數進入增幅模式,但所承接產業大多附加值低且不利于環境治理,因此其發展理念須逐步從“數量增長”轉為“質量提升”,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加強環境建設與治理、優化城鄉布局及縮小城鄉差距,以更好地實現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④針對靜態、動態測評結果均較低的“后進型”地區,如石臺、諸暨、東至、豐縣、沛縣等,這些地區經濟基礎較薄弱,且發展動力不足,需要政府給予特殊的引導與扶持,包括與領先發展地區開展商業合作模式、挖掘本土資源潛力、發展地方特色經濟等,以避免其成為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的阻力。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