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包容性綠色發展倡導包容性與綠色化共存,是實現經濟、社會、生態三大系統協同發展,促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基于 2004—2017 年長江經濟帶 108 個城市的面板數據,運用定基極差熵權法、耦合協調度模型和面板分位數回歸等計量手段,對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的時空異質特征及影響因素等問題進行測度與識別。結果表明:1)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整體呈逐年上升趨勢,其空間格局表現為從長江下游地區到長江上游地區逐級遞減的階梯性差異,同時還具有全局空間正自相關性,形成了以省會城市為集聚地的“多中心”發展格局;2)與均值回歸估計結果不同,面板分位數模型進一步發現,經濟發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資和環境規制對包容性綠色發展中等水平城市影響較大,人口分布情況、科研投入水平對包容性綠色發展較低或較高水平城市影響程度更強,而產業結構僅對包容性綠色發展低水平城市有顯著影響。以上研究結論,可為促進不同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城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益的實證參考和政策建議。
關鍵詞:包容性綠色發展;時空異質;耦合協調發展;面板分位數模型;長江經濟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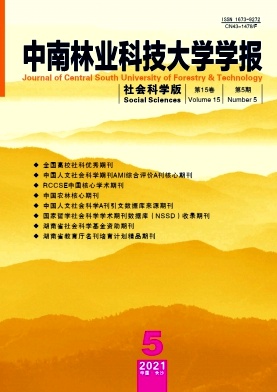
鄧淇中; 秦燕絲; 何曉慧 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2-01-07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是關系國家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2020 年 11 月 14 日,習近平在全面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指出,“要使長江經濟帶成為我國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主戰場、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主動脈、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主力軍”。近年來,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均取得歷史性進展。然而,長江經濟帶仍面臨區域發展不協調、經濟發展效益不高、居民收入差距懸殊、生態環境保護成效不顯著等問題。這一系列社會和環境問題,預示著經濟增長需向綠色化與包容性轉變。 2012 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首次提出了包容性綠色發展理念,其目的在于建立全球利益、包容性發展和綠色發展之間的密切聯系,聚焦經濟、社會、環境之間的可持續發展。在聯合國公布 2030 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后,包容性綠色發展逐漸成為多數國家實現其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戰略選擇。事實上,我國早在“十二五”規劃中就提出走包容性綠色發展之路的愿景。包容性綠色發展理念不僅是我國新發展理念中“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綜合體現,還把握了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以及未來發展的內涵,為實現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目標提供了新的路徑方向 [1-2]。在這一背景下,如何引導經濟增長向包容性與綠色化轉型,從而進一步提高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成為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從現有研究進展看,包容性綠色發展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內涵界定和量化評價兩方面。 1)關于包容性綠色發展內涵界定方面。多數學者從發展經濟學范疇定義包容性綠色發展,認為它是一種追求經濟增長、生態環境和社會公平相互促進的可持續發展方式,主要強調經濟增長必須同時具備對生態環境友好與社會包容性的特征 [3-5];還有學者從福利經濟學范疇界定包容性綠色發展,強調經濟增長的目的在于提高當代人和子孫后代的社會福利,關注“人”在環境、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尤其強調對窮人和弱勢群體的包容 [6-8]。2)關于包容性綠色發展量化評價方面。現有文獻對包容性綠色發展的量化評價成果較少,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根據包容性綠色發展的內涵和外延構建評價體系,并采用不同評價方法對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進行評價。如徐寶亮和鐘海燕 [9]、王宇昕等 [10]、吳武林和周小亮 [11] 基于包容性綠色發展的內涵,選取經濟發展、機會公平、民生福利、生態環境等不同維度構建評價體系,分別采用因子分析法、熵權 TOPSIS 法、熵權法,對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進行了綜合評價。二是基于數據包絡分析法,從投入產出角度對包容性綠色發展的效率進行度量。如李政大和劉坤 [12]、趙林等 [13] 構建了不同包容性綠色效率投入產出體系,分別采用 EBM (Epsilon-Based-Measure) 模 型、Super-SBM (Slacks-Based-Measure)模型對中國包容性綠色發展的效率進行了測度。
綜上所述,學術界對包容性綠色發展的相關研究成果為我們系統分析這一問題提供了重要參考,但仍有如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第一,鮮有文獻運用新發展理念,立足經濟、社會和環境多維度構建包容性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第二,已有文獻暫未分區域探索各類導致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趨勢化和異質性的關鍵因素,以及如何科學估算其影響因素、方向和大小等問題。第三,現有文獻中往往對指標選取存在一定主觀性,且其研究對象大多停留在全國、省級層面,忽略了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在城市間的差異特征。鑒于此,本研究將長江經濟帶 108 個城市作為研究對象,在充分挖掘包容性綠色發展內涵的基礎上,重構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通過多種統計與計量方法進行測度評價,并在時空雙重維度下,深入探究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差異化特征及其影響機制,以期為實施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倡議,完成自身經濟轉型升級,并推進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實證、經驗支持和策略參考。
一、評價指標體系構建(一)構建思路
包容性發展著重強調經濟與社會層面之間的有序發展,要求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關注社會公平、增進民生福祉 [14];綠色發展則注重經濟與環境層面之間的協調共生,要求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15]。而包容性綠色發展理念有機結合了這兩大發展觀點,它要求經濟發展的結果既要體現經濟個體平等參與、共享,又要強調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效率提升 [3]。由此可見,包容性綠色發展理念不僅要求經濟增長水平、社會福利水平和生態環境水平的共同提升,更強調三者之間協調發展狀態的改善,這正反映了新發展格局下中國經濟發展轉型的新方向。同時,習近平強調長江經濟帶發展要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堅持“保護和發展協同推進”等原則,其目的在于強調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互動關系,以及發展過程中應更注重經濟成果的社會共享,最終形成經濟、環境和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基于此,本研究試圖從經濟增長、社會福利、生態環境三個維度著手,構建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并以三者之間的耦合協調發展程度來衡量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
(二)指標選取
通過中國知網(CNKI)對“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等主題進行檢索、閱讀和分析,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期刊文獻,進行評價指標頻數統計,進而遴選成本研究的經濟增長、社會福利、生態環境三個子系統統計指標①。具體選取結果如下:
1)經濟增長應包括一定程度的經濟規模、全面協調的經濟結構以及平等共享的經濟效益。其中,經濟規模反映區域經濟發展的基礎水平,采用地區國民生產總值等 4 個指標表征;經濟結構是經濟穩定發展的根本條件,采用第二、三產業生產總值在地區生產總值中的占比表征;經濟效益是全社會投入產出的效率和結果,應體現人人共享原則,采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等 3 個指標表征。
2)社會福利是“以人為本”理念的具體體現,反映了包容性綠色發展的價值取向。本研究擬從文化教育、基礎設施、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四個方面構建社會福利子系統,體現社會包容性水平。選取每萬人在校大學生人數、每百人公共圖書館藏書表征文化教育機會公平;醫院、衛生院數等 3 個指標表征醫療衛生機會公平;人均城市道路面積等 3 個指標表征基礎設施條件公平;失業保險參保人數等 3 個指標表征社會保障機會公平。
3)在環境容量、資源約束范圍內的經濟增長能有效促進包容性綠色發展進程。本研究依據 PSR 理論,從生態基礎(State)、生態壓力(Pressure)、生態響應(Response)三個層面建立生態環境子系統(OECD)[16],以反映經濟增長的綠色化水平。生態基礎呈現了生態系統的自然資源總量以及發展現狀,用人均綠地面積等 3 個指標表征;生態壓力表現了人類經濟活動給環境造成的影響,選取工業 SO2 排放量等 3 個指標表征;生態響應反映了人類面對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時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措施,用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等 3 個指標表征。在此基礎上,最終建立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如下: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一)耦合協調度模型
借鑒姜磊等的做法 [17],建立物理中的容量耦合模型如下: {[ ] } 3 3 (,) ( ,) (,) ( , ) ( , ) ( , ) /3 f xt g yt hzt C f xt g yt hzt × × = + + 。 (1)式中:C 為耦合度,f(x,t)、g(y,t)、h(z,t) 分別為經濟增長、社會福利、生態環境三個子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①。耦合模型雖能反映系統間相互作用的強弱,但無法反映系統間協調水平的高低。因此,進一步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以考察經濟增長、生態環境、社會福利子系統之間的協調性,公式如下:U CT T a βγ f xt g yt hzt = × = + 。 (2)式中:U 為耦合協調度即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T 為經濟增長、社會福利、生態環境三個子系統綜合評價指數之和,α、β、γ 為待定系數,由于三個子系統重要程度相同,確定其取值為 α=β=γ=1/3。
(二)面板分位數回歸模型
面板分位數回歸模型反映了不同分位數上的邊際影響,能得到條件分布的全面和細節信息,從而提高回歸結果的穩健性,彌補了傳統靜態面板模型只能反映條件均值影響的弊端。面板分位數回歸模型如下:若條件分布 y|x 的總體 τ 分位數 Quant X( ) τ 是 X 的線性函數,即: ( ) Quant Y X X it it it τ τ = β 。 (3)式中:Xit 為解釋變量的向量; ( ) Quant Y X τ it it 代表對于給定 X,Y 與分位點 τ τ (0 1) < < 相對應的條件分位數; τ β 表示 τ 對應的系數向量,可由最小化絕對離差得到,即: , , { | (1 ) } i i i i iY X iY X i i i i arg min Y X Y X τ β β β τβ τ β < = ∑ ∑ − + −− ≥ 。 (4)
(三)研究區域與數據來源
長江經濟帶覆蓋上海、浙江、江蘇、江西、安徽、湖南、湖北、重慶、四川、云南和貴州 9 省 2 市。由于 2011 年地市級行政區劃調整,安徽省巢湖市并入合肥市,貴州省撤銷畢節、銅仁地區設立畢節市、銅仁市 2 個地級市,因此,目前長江經濟帶總計含 110 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以下簡稱“城市”)①。考慮數據的可獲取性,貴州省畢節市、銅仁市數據缺失嚴重,故將兩市給予剔除,最終選取長江經濟帶 108 個城市作為研究對象。本研究的時間跨度為 2004—2017 年,數據主要來源于各年份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及各省級、市級統計年鑒和各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并將 2011 年以前安徽省巢湖市數據逐年歸入到合肥市數據,其他個別缺失數據采用算術平均或幾何平均方法補齊。
三、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時空異質特征(一)時間序列特征
從長江經濟帶經濟增長、社會福利與生態環境子系統綜合評價指數變化趨勢來看,如圖 1a 所示,三個子系統綜合評價指數總體呈逐年增長趨勢。2004 年經濟增長子系統綜合評價指數為三個子系統中最低值(0.1),由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以及產業結構優化持續為長江經濟帶經濟發展注入活力,促使經濟增長子系統以 16% 的年均增長率不斷上升,在 2017 年時達到峰值(0.68)。社會福利子系統綜合評價指數由 2004 年的 0.13 增長至 2017 年的 0.22,年均增長率為 4%;生態環境子系統綜合評價指數在 2004 年時為 0.12,在 2017 年時達到 0.21,仍屬于三個子系統中的最低值。總體來看,2004—2017 年長江經濟帶經濟增長子系統發展迅猛,但社會福利和生態環境子系統發展存在滯后,為促進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還需要進一步優化社會福利、改善生態環境。從長江經濟帶及三大地區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變化趨勢來看,如圖 1b 所示,2004—2017 年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平均水平由 0.2 增加到 0.36,整體呈現緩慢上升趨勢,且表現出從長江下游地區到長江上游地區逐級遞減的階梯性差異,這與宓澤鋒等 [18]、江孝君等 [19]、李雪松等 [20]、王宇昕等 [10] 的結論較為一致。
(二)空間異質特征
綜上可知,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可能存在空間分異現象,可進一步通過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方法來研究其空間分布特征 [21]。本研究采用 ArcGIS 10.5 繪制了長江經濟帶“十五”~ “十三五”時期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的空間分布圖,并依據自然斷點法將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分為高水平、次高水平、中等水平、次低水平、低水平五個等級(圖 2)。
在城市層面,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在四個時期均呈現由東向西遞減的態勢,且都顯現出“核心—邊緣”特征。1)高水平城市主要有上海市、杭州市、南京市、蘇州市、武漢市等 12 個中心、副中心城市,由于它們資源豐富,發展機會多,經過不斷發展進步,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跨越了 0.5 的門檻,明顯優于長江經濟帶其他城市。其中,上海市作為我國大陸地區外貿金融最發達的城市,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始終保
持領先,在 2016 年達到樣本期間內最大值(0.95)。 2)次高水平城市包括南通市、常州市、紹興市、南昌市、重慶市、徐州市、鎮江市、溫州市等 12 個城市,多屬于鄰近中心、副中心的城市,其經濟發展受到中心城市經濟溢出的影響,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得到明顯提升,2004—2017 年均達到 0.4 以上。3)中等水平城市有昆明市、連云港市、揚州市、貴陽市、淮安市、宿遷市、安順市等 55 個城市。這些城市大多離經濟中心、副中心城市較遠,經濟發展受中心城市影響較小。4)次低水平、低水平城市主要包括宜賓市、曲靖市、張家界市、亳州市、池州市、瀘州市、玉溪市等 29 個遠離中心、副中心城市,大部分屬于流域內邊緣城市,這些城市早期經濟基礎不佳,經濟社會資源匱乏,2004—2017 年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雖有提升,但仍低于 0.3,與高水平城市差異明顯。
(三)空間關聯特征
本研究利用 ArcGIS 10.5 和 GeoDa 1.14 軟件對長江經濟帶 108 個城市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進行全局自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2 所示。樣本期間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的 Moran’s I 指數介于 [0.200,0.266] 之間,均大于 0,表明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存在空間正相關性。為進一步分析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的空間集聚情況,對數據進行局部空間自相關處理,其局部空間集聚統計結果見表 2。從數量上看,長江經濟帶局部空間自相關類型基本穩定,以 HH 集聚類型、LL 集聚類型為主,二者合計占長江經濟帶 108 個城市總量的 35.2% ~ 41.7%。由此可知,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較高或較低水平城市的數量較多,且在空間上集聚。空間分布格局總體規律是,HH 集聚類型的城市主要分布于長江經濟帶下游沿海地區,以上海市、杭州市、南京市、蘇州市為典型,該類型城市的空間集聚特點鮮明,受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明顯。LL 集聚類型城市主要分布在長江經濟帶上游的四川、貴州、云南等省區,這些地區受先天自然條件與后天發展動力不足的影響,經濟發展緩慢。相對而言,LH 集聚類型、HL 集聚類型的城市分布較為分散,LH 集聚類型城市主要分布于長江經濟帶下游沿海地區周邊的淮安市、麗水市、馬鞍山市、銅陵市、安慶市、黃山市以及滁州市; HL 集聚類型城市數量穩定,2017 年為重慶市、成都市、安順市和昆明市等 4 個城市,該類城市皆為長江經濟帶上游地區中心城市,這說明該地區中心城市輻射能力較弱。
四、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影響因素識別
(一)變量選取
為了更全面地揭示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空間差異形成的原因,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研究將主要從以下六個方面來考查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的影響因素:1)人口分布情況(pop),用人口密度來衡量。密集的人口分布一方面使城市更具活力,另一方面可以緩沖人類對環境的影響,因此可能影響城市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2)經濟發展水平(rgdp),用人均生產總值來衡量。倒“U”型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闡明了人均收入和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經濟發展水平勢必會影響經濟、社會和環境之間的協調狀態。3)科研投入水平(tec),用科學技術財政支出來衡量。一般來說,技術創新不僅能提高勞動效率,還能減少環境污染。4)環境規制(er)倒逼企業進行技術革新,是保護生態與發展經濟協同并進的政策手段 [22],采取趙霄偉研究中的計算方法來衡量 [23]。5)產業結構(str),用非農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來表示。產業結構升級促使經濟增長方式向綠色低碳轉型,對包容性綠色發展具有正面效應。6)外商直接投資(fdi)能夠增加對外貿易額、優化貿易結構,用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來表示。
(二)FMOLS 估計結果分析
本研究對所有原始數據進行了對數變換以消除異方差問題,對各變量進行了面板單位根檢驗和協整分析以保證檢驗結果的穩健性①。FMOLS 估計檢驗結果如表 3 所示,其中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水平、科研投入水平在 1% 的顯著性水平下與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正相關;人口分布情況對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具有促進作用,且在 10% 的水平下顯著;而外商直接投資和環境規制均未呈現顯著性影響。
(三)面板分位數估計結果分析
本研究共選取了 0.1 ~ 0.9 九個分位點,進一步分析各個變量在不同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下的差異化影響,分析如下。
1)人口分布情況在每個分位點處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其對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具有促進作用。另外,人口分布情況對包容性綠色發展的影響在 0.1 ~ 0.4 分位點處逐漸減小,而在分位點 0.5 ~ 0.9 處逐漸增強。這說明人口分布情況對包容性綠色發展較低及較高水平城市的影響力度較大,這可能是由于經濟增長初期人口分布對經濟增長具有集聚效應(溢出效應),隨著時間推移會發生人口對經濟增長的擁擠效應(負外部性)。
2)經濟發展水平在不同分位點上均對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有正向影響,表明經濟發展水平可以促進包容性綠色發展。由表 3 可知,這種促進作用在分位點 0.1 ~ 0.7 處逐漸增強,而在分位點 0.8 ~ 0.9 處逐漸減弱。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僅提高了人民生活質量,還促進了技術水平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減少了污染物排放、資源浪費,經濟發展、社會福利、資源環境之間協調水平得到上升。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不斷地提高,資源緊張、人口密集、交通擁堵等問題使得社會生產效率低下,經濟、社會和環境系統出現失調狀況。
3)科研投入水平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分位點 0.8 處除外),表明科研投入水平對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具有促進作用。且其回歸系數在分位點 0.1 ~ 0.7 處呈現遞減趨勢,而在髙分位點 0.9 處又增大,這表明科研投入水平僅在包容性綠色發展較低和較高水平城市中起著較大的正面影響。
4)環境規制在各個分位點處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且在 0.1 ~ 0.8 分位點處,環境規制的回歸系數呈逐步增大趨勢;但在 0.9 分位點處,環境規制的回歸系數逐漸減小。這意味著環境規制對包容性綠色發展中等水平城市的影響力度更大。
5)產業結構與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僅在分位點 0.1 和 0.2 處呈顯著正相關,且其回歸系數在 0.1 ~ 0.2 分位點處影響力逐漸減弱。這可能是由于長江經濟帶近年來工業化進程逐步加快,在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伴隨著環境破壞;也可能是長江經濟帶產業結構尚待優化,因此其促進效應尚不明顯。
6)幾乎在每個分位點處,外商直接投資都對包容性綠色發展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由表 3 可知,其回歸系數從低分位點至高分位點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趨勢,這說明對于包容性綠色發展中等水平城市來說,外商直接投資的促進效應較強。通常來說,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效應存在時滯性,因此該因素對包容性綠色發展的影響程度會表現出由弱至強的增長趨勢。
五、結論與建議(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構建了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從時序演變、空間異質等方面實證分析了 2004—2017 年長江經濟帶 108 個城市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并運用 FMOLS 和面板分位數模型識別了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的關鍵影響因素,研究表明:
從時空異質特征來看,2004—2017 年,長江經濟帶各城市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總體上呈逐年增長趨勢,且經濟增長子系統的發展速度快于社會福利和生態環境子系統,經濟增長的包容性和綠色化程度較低。在空間相關性特征方面,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形成了以各省省會為集聚地的“多中心”發展格局。具體體現為高水平城市主要集中在各省會城市并不斷向鄰近地區擴散,多分布于長江經濟帶下游地區;次高水平、中等水平城市散布于長江經濟帶中游、下游地區;次低水平、低水平城市主要集中在長江經濟帶上游地區。
就影響因素而言,FMOLS 回歸與面板分位數回歸的結果均表明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分布情況對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面板分位數回歸顯示,產業結構僅在低分位點處影響顯著,科研投入水平在髙分位點處影響不顯著,環境規制對中等水平城市的影響程度更深。另外,FMOLS 回歸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包容性綠色發展影響不顯著;面板分位數回歸結果則顯示,外商直接投資除在髙分位點處影響不顯著外,在其它分位點處均顯著,且表現出先增后減的趨勢。
(二)政策建議
研究結論顯示,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存在顯著的空間異質性,長江下游地區到長江上游地區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逐級遞減的階梯性差異明顯,本研究認為應分地區制定促進長江經濟帶包容性綠色發展的政策建議。第一,長江上游地區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較低,人口分布情況以及科研投入水平等因素對其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影響強度大。因此,長江上游地區應該優先發展經濟,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并通過大力發展第二、三產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進而加快城市化進程,并且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此外,各城市應充分結合自身特色,發揮產業發展優勢,加強區域科技創新經費的投入,充分發揮其引導作用,激勵科技成果的產出。第二,長江中游地區包容性綠色發展狀態處于中等水平,應著重從環境規制、外商投資水平等因素著手,將工作重心轉變為提升經濟增長質量上,改變以往髙投入、髙能耗的粗放式發展模式,逐步向集約型且高效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另外,各地區需因地制宜,注重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城市空間布局的優化,在加大資源開發的基礎上改善區域投資環境。同時需加快“走出去” 的步伐,促進人才、市場、資本、資源等要素的重組與流動,并大力吸引國外先進技術與外商投資、加速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區域經濟持續較快發展。第三,長
第三,長江下游地區包容性綠色發展水平較高,人口集聚和科研投入都對其有正向促進效應。因此,應充分發揮資金優勢、區位優勢,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并吸引人才集聚為城市發展帶來活力;進一步根據各城市發展現狀,優化經濟布局,合理安排產業,以提升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并合理制定人才引進和就業促進政策,以實現人口分布和產業布局形成相互促進、協調共生局面;此外,政府仍需增加科學技術財政支出,合理分配科研投入,促進城市技術創新水平提升和實現產學研深度融合,把創新作為城市發展的第一動力,培養一批高水平科技人才,增強城市的技術硬實力。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