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農民城市化的發展樣態是學界極為關注的研究主題,而城市化對象本身也存在差異。由于大城市郊區農村的獨特性,使得其城市化必然與一般中西部農村城鎮化存在截然不同的規律和特點。通過對武漢市近郊農村的實地調研發現,當地農民家庭并不止步于原有的低度城市化,在居住環境、就業選擇以及生活方式等三個方面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追求,可以認為城郊農民家庭正在經歷一場深度城市化。因此,通過對其表現形式、動力來源以及實現方式進行相應的分析和解釋,以揭示城郊農民深度城市化的實踐邏輯,從而深入理解城郊農民家庭的城市化行為,進而對中國城市化進程與發展進行更為深入和細致的探索與推進。
關鍵詞:深度城市化;城郊農民家庭;教育投資;代際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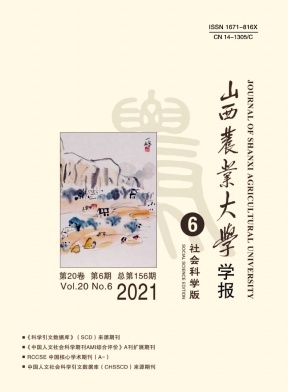
甘穎 山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2-01-07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綜述
據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統計,我國城市化水平正在快速提升,從 1978 年至 2018 年,我國城市化率由 17. 92% 上升至 59. 58%,面對快速發展的城市化,李克強總理提出,當前我國城市化要義在于“人的城市化”,即人可以順利進入城市進行生活、生產,截至 2018 年,有 9000 多萬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落戶[1]。可以說,農民城市化不僅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也是幾千萬農民家庭的奮斗根本,那么,城郊農民作為 9 億農民中的一員,在已經實現城市化的目標后,其城市化樣態是止步不前還是繼續發展?是否因為特殊的城郊區位使得他們的城市化軌跡與普通的中西部地區農民有所不同?這成為本研究想要討論的問題。
城市化在學界已經有很長時間的研究歷史,吳友仁在 1979 年發表 《關于我國社會主義城市化問題》 的文章后,中國的城市化研究就得到了快速發展與推進。此后,學界從國家城市化戰略出發,對城市化進程進行了大量的研究[2],可以說,當前學界對于城市化類型的研究主要有兩種視角。第一,宏觀政策視角。所謂的“農村城市化”是指農村人口向大中城市轉移的“城化”過程,即通過城市來吸納農村人口、農村人口向大中城市轉移積聚、城市不斷擴大的三個過程[3]。其中,半城市化被認為是當前我國城市化發展最明顯的一種樣態,即農民并未完全嵌入城市,在體制、社會生活和社會認同上均未完全整合的狀態[4],其結果導致農民工無法真正融入城市,搖擺于城鄉之間[5]。于是,厲以寧在“半城市化” 的背景下,認為想要真正促進農民城市化,就要從根本上改革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6],建立城鄉融合的城市化發展模式。第二,農民家庭策略視角。漸進式城市化被譽為極具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7],而漸進式城市化得以實現的基礎在于家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父代為子代在城市立足提供了經濟資源和家庭照顧,讓年輕人可以順利進入城市,減少經濟和家庭負擔,從而更好地適應城市生活[8]。因此,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農村自發地形成以家庭為單位的城市化發展秩序,通過“新三代家庭”接力式代際支持的方式,為子代城市化提供經濟和代際資源支持[9]。可以說,農民城市化的實現機制,一方面可通過相關的地方發展需要和政策倡導得以實現,另一方面以農民家庭為單位自發地“恩往下流”,幫助子代順利實現城市化[10]。
綜上可知,學界主要從宏觀的政策視角與微觀的農民家庭視角對城市化的整體樣態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與解釋,并對中國現有的城市化發展狀況進行了很好地表述。但是以上研究都是關于一般中西部地區城市化的研究和表述,并未注意到一些特殊農村,如城郊村的具體城市化樣態。我們一般對城市化類型或者樣態的理解,可以認為它是由表現形式、動力來源以及實現方式這三個部分共同形塑而成[11],可是城郊村和一般農村的城市化在這三個因素上卻存在明顯的差異。首先,中西部地區農民的城市化在居住、就業和生活三方面是被切割的,年輕人一般就業在大城市,居住在縣城,生活面向在城市;而中年人一般就業往返于縣鄉與村莊、居住在村里,生活面向在村。但是城郊村農民的城市化在居住、就業和生活上是一體的,是在同一場域下完成他們的城市化目標。其次,中西部地區農民城市化的動力主要在于婚姻和教育,但是對于城郊農民而言,區位優勢使其成為婚姻高地,同時城鄉一體化使之擁有比中西部地區農村更好的教育機會。最后,中西部地區農村代際支持中的經濟支持主要體現在婚姻、教育等階段性大事上,但是,城郊地區農民家庭為子代提供的經濟支持是日常性的,生活化的,并不局限于某一事件或時間段。可以認為,因為城郊村的獨特性,使得它的城市化必然會存在與一般農村城鎮化迥然不同的規律和特征。因此,本研究認為要全面理解中國城市化進程,就要對城郊村城市化的規律和特征進行一個單獨認識,所以,本研究以大城市郊區農村作為研究對象。這也表明本研究的創新之處在于城市化研究對象的創新。
所以,基于對已有文獻的梳理和思考,認為大城市郊區農民的城市化應當要被作為一種單獨的城市化樣態進行討論,并結合在武漢東西湖區的實地調研發現,大城市郊區 (以下簡稱城郊)的城市化不同于中西部地區的淺度城市化,其呈現出一種深度城市化的樣態。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農村家庭發展普遍以家庭再生產作為主要目標。在中西部地區,一般家庭的發展目標只需要在縣城里買房、就業和生活就可以實現。但是城郊地區的農民家庭尤其是年輕群體,不僅要在城里買房、就業和生活,他們還會對住房區位、就業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可見,城郊農民在完成一般城市化目標之后,并沒有停止城市化的步伐,相反,還表現出繼續城市化的趨勢。本研究通過對其深度城市化的表現形式、動力來源以及實現方式進行描述和討論,以更好地理解城郊農民家庭的城市化行為,從而對中國城市化進程與發展有更深入的探索和推進。本研究的實地調研案例來源于武漢東西湖農場 S 大隊。其幅員 266 公頃,14 公頃宅基地,人口 1157 人,319 戶,其中勞動力 (18 歲以上 60 歲以下) 585 人,基本農田有 247 公頃,以種養殖為主,農田種植主要是水稻、玉米和葡萄,養殖則以四大家魚為主,有 22 公頃魚塘,蝦蟹養殖有 13 公頃。大隊年輕人在城里或者村里擁有一份穩定的 工 作 , 收 入 大 約 為 每 個 月 3000~5000 元/人 ,而中老年人大多是農場職員,退休后收入也有 2000 元/人,呈現出個體收入不高,但是家庭收入不低的特點,并且隊內的農民家庭大多已經實現了城市化,房子地處區政府的所在地 W 街道。
二、從“淺度城市化”到“深度城市化”:城郊農民的城市化變遷
對于城郊農民而言,他們雖然已經實現了居住、就業和生活在城市,但其本質是一種“淺度城市化”,即居住位置邊緣、就業方式低端以及低限度消費[12]。
(一) 淺度城市化的典型特征
1. 居住區位邊緣化。居住城市化是當前城市化的基本門檻,任何人想要進入城市生活,都必須要有房子作為安居的前提。因此,進城買房成為城市化的基礎性配置。那么,農民要想進入城市居住,一般都有兩條路徑,一條是城市擴張,農民失地進入城市居住;另一條是農民通過半耕半工的家庭生計模式在城里購房、定居。對于城郊地區的農民而言,由于其特殊的區位和城市建設擴張的需要,農民在政府的引導下,通過集中征地拆遷、土地換社保和安置房建設等方式,可以整體性、集中性地實現農民進城。于是,依托于土地城市化,被迫失地的農民家庭可以輕松地實現進城居住,實現居住城市化。但由于城市空間有限,農民無法通過土地置換的方式進入城市中心區居住,相反只能居住于城郊等偏遠地帶。因此,農民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存在著一系列的 “空間困擾”。一方面,征地拆遷社區基本位于城市的邊緣位置,屬于城鄉一體化中的“鄉”,具體表現為在居住環境、周邊公共配套設施以及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上的欠缺。另一方面,由于安置社區統一的空間布局,社區的空間范圍相比農村來說大幅縮小,很多農民在原有生活方式未轉變的情況下,出現隨意占用公共資源、爭奪公共空間等現象[13]。
2. 低端非農化就業
農村城市化的起點和外在形式是農民職業的非農化[14],而農民非農化的原因在于城鎮有大量就業機會可以吸納和轉移農村勞動力。實際上,城郊農民很早就已經實現了非農化。一方面,城郊地區的務農收入低于務工收入,因此,很多城郊農民很早就將土地承包出去。如東西湖區雖然作為武漢的農副產品供應地,但是農民的就業方式卻不是農業,他們以每公頃 10 500 元的價格承包給安徽省和浙江省等外地人,自己則選擇務工,即使還存在部分農民種地的情況,這些人要么是有農業生產技術,可增加收入,要么是進行輔助性的農業生產,滿足家庭的自給自足需求。另一方面,大城市郊區的就業市場發達,能提供包括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內的一系列產業機會,而這些產業的發展又能為城郊農民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隨著產業發展和流動人口增加,在城郊地區也催生出了大量低端、靈活的就業方式,如流動小吃攤、臨時菜攤等“地攤”產業應運而生。這些非正式就業既解決了低技能、年齡大等不具備競爭優勢的老一代農民工的生計問題,又對本地家庭剩余勞動力有很好地吸納,從而實現城郊地區農民的就業非農化。
3. 低層次消費水平
對于城郊農民而言,安居、樂業已經可以得到保障,那么如何適應城市的生活,其生活方式的轉變是其城市認同感強弱的重要指標。農民進入城市后的歸屬感越強烈,其習得城市和現代化生活方式的能力越強,進而形塑出他們的消費需求和消費特征[15]。雖然,城郊農民很早就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城市融入感較強,但其消費能力還處于較低的消費層次。以武漢市的漢陽區為例,農民工主要以基礎性的衣食住行開支為主, 90% 進城農民在基礎生活支出占月實際支配收入的一半以上,而用于交友、人情及娛樂方面的消費支出在 10% 以下,用于學習技能培訓的自我發展型消費在 5% 以下,可見,進城農民的生存性消費支出所占比例偏大,而發展和享受性消費支出過少[16]。同時,農民家庭雖已在城里買房,但子代還未完成家庭再生產,父代受階段性人生任務的影響,他們在潛意識里以節省的生活方式為子女成家積累資源,以家庭積累作為日常城市生活開支的底線。
總體來看,城郊地區農民較為容易地實現了居住、就業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但是,農民城市化不僅僅是獲得城市戶籍,也包括在城市的穩定就業、收入與支出匹配等農民市民化的指標。而從市民化的角度來看,城郊農民也并未徹底融入城市,這就導致其仍然處于“半城市化”的狀態,即農民進城只是實現了較為低層次的城市化水平[17]。
(二) 深度城市化的表現形態
1. 居住空間的改善:從邊緣區到中心區
對于農民家庭而言,進城購房不僅僅是他們城市化的重要目標,也是就業、子代發展以及經濟能力提升等因素導致的結果,而對于在城市已經擁有一套房的城郊農民而言,他們在順利購房成為新市民后,不僅會繼續購置房產,還對房子所在的區位有一定要求。例如 6 組王某的女兒在 2008 年時已經在 W 街道購買了一套 120㎡房子,買房的原因在于離公司近,比較方便。但是他們現在卻在 Q 區又購買了一套房子,雖然面積不足 100㎡,價格也要近 2 萬/m2 ,但勝在環境和教育質量比 W 街道強。農民對房子的區位要求不僅在于有一個居住的處所,更在于周邊輻射的公共服務,尤其是年輕人對于教育、日常生活消費的需求較高,因此,他們對于周圍環境的要求也高于老一代人。“很多外地人都羨慕我們是武漢人,雖然是郊區,是農村,但是我們大多數都能買房,我們組 (一組) 幾乎一大半都在 W 街道買了房,我自己覺得挺滿足的,但是,(兒子) 有點能力,還是愿意往漢口和武昌去,畢竟老城區,各方面發展都比我們好。”(20190823?CWD) 可以看到,城郊地區農民居住城市化的重點并不在城郊,城郊的房子只是作為暫住地和過渡站,他們的最終目標是向著更靠近市中心的區域轉移。
2. 就業方式轉變:從非正規就業到正規就業城郊地區農民的經濟模式不同于中西部地區半工半耕的生計模式,受當地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的影響,當地存在大量的就業崗位可供勞動力群體選擇,但這些工作大多以非正規就業為主,而非正式就業有其收入較低、時間不固定和相應就業保障不到位等特征,這也讓很多年輕人不安于現有的工作現狀。因此,他們的就業方式就從非正規就業向正規就業轉變。在本地,年輕人一般會選擇進入工廠、企業或者機關部門就業,這樣整體的就業質量就有一定的保障。首先,就業時間充分。不同于非正規就業,正規就業時間不受市場和天氣等因素的影響,基本能達到 300 天/ 年的就業時間,朝九晚六的單位制就業時間,就可以保障年輕人單位時間內的基本收入高于非正規就業。其次,收入穩定。非正規就業的就業時間決定了其收入較低,而正規就業的收入較為穩定,是按照政府制定的最低收入制度來發放工資,還會疊加相應的績效收入,并且收入水平與就業者所擁有的技能和學歷水平相掛鉤,條件好者收入則優。最后,社會保障的相應供給。正規就業單位一般會為職工購買五險一金,即使是單位的非編制人員,也會為他們購買四險一金或五險一金,充分的社會保障也讓他們在家庭發展需要以及發生意外事故時,可獲得相應的經濟補貼。
3. 生活方式的升級:從基礎性消費到享受、發展性消費農民在城市的生活與消費模式是與其立足于城市內在的需求方式相對應,當前其消費方式已經由簡單的“賺票子、娶妻子、生孩子”的消費方式向更好適應城市生活節奏的娛樂、享受型消費特征轉變[18]。其中,年輕人的消費內容與消費水平變化最大。一方面,消費的內容擴大,他們以前的消費內容主要是基本的吃穿住行,但現在的消費大部分向個體的休閑娛樂以及子代的教育開支等方面擴展開,尤其是子代教育開支的占比越來越高。目前我國城市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消費已占家庭總消費的 35%,占家庭總收入的 30%[19]。另一方面,隨著消費項目的增多,消費金額也在上漲,城郊年輕人的剛性消費開支基本達到 15 萬~20 萬,已然達到城市中產階級的消費水平。例如,陶某,武漢 D 區 S 大隊干部,年收入 9 萬,每年的生活開支有 20 多萬元。這主要包括 9 個方面。一是買衣服。每件 1000 元,每年 2 萬~3 萬元;二是小孩教育費用。學費 6000 元,培訓班 1 萬元;三是化妝品每年 1 萬元;四是兒子和老公保險費 2 萬元;五是房貸 6 萬元;六是車子花費 2 萬元;七是人情開支 1 萬元;八是聚餐吃飯 1萬元;九是旅游花銷 2萬元 (20190816?DP)。可以看到城郊農民在進入城市后,已然實現了居住、就業和生活方式的淺度城市化,并很快適應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節奏,成為城市“新市民”。可即便他們已經實現城市化,但仍用發展的眼光來不斷提高當下的城市生活質量。于是,在就業方式、居住空間和消費方式等三方面都產生相應的遞進,最終形成以年輕人為導向的城郊家庭城市化,從居住邊緣到中心,從非正規到正規就業,以及生活方式從基礎性消費到享受性、發展性消費的三位一體城市化質量不斷提升的樣態。
三、深度城市化的動力:以城市優質的教育服務為核心
農民進入城市生產、生活受到不同因素的驅動,而城市化的驅動力會轉化為農民家庭的發展目標,不斷促使農民家庭調整家庭策略以實現目標。不同家庭對于城市化的定義不同,其城市化的目標會存在差異,結果是所追求的城市化水平會存在明顯分化。而城郊農民家庭的城市化動力從原初的階層競爭向階層流動轉變,進城不僅為面子,還為享受城市內部優質的教育服務和資源。
(一) 以面子競爭為基礎的農民城市化目標
城市化作為當代農民家庭極其重要的一項家庭發展目標,對于一般的農民家庭而言,實現家庭再生產是農民家庭城市化的基礎性目標,其中,父代進城購房,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場中的競爭力成為大部分中西部地區城市化最首要的動力。但是對于城郊農民而言,由于經濟發展的優勢,其本身就處于婚姻市場的高地,不愁兒子找不到媳婦,所以,家庭再生產的目標并非作為城郊農民進城的主導目標。但農民即使不為子代成家買房,他們也存在進城買房的需求。對他們而言,進城買房是一種滿足村莊階層競爭的體現[20],買房并非剛需,但卻并非充分條件,因為別人進城買了房子那我也要買,房子成為日常村莊競爭的標的物。這源于村莊是農民生產生活、價值評判的重要場域,如果農村男性能夠在城市購買一套房子,就意味著他和城市男性一樣,從農民階層轉變為城市階層。其階層身份的優越性也讓他們在村莊面子競爭中占據一定的優勢,熟人社會的輿論傳播會讓其階層之間的差異被不斷拉大。于是,趨于階層競爭壓力和面子競爭,農民家庭很容易出現“盲從”行為,進城買房就成為農民非剛需、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
城市本身對農民的吸引力促使農民選擇進城購房,受地區城市化發展規劃的影響,時空高度壓縮的城市化進程為農村青年群體的現代化生活方式提供了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再加上城鄉之間便利的交通,使得其較早地習得城市的生活氣息,因而他們的城市化沖動是在城市生活的浸染中萌芽出來的。進而城郊農民或者新市民的城市化實際上就被卷入到城市發展系統之中。
(二) 以教育為導向的公共服務需求是農民深度城市化的根本
就當前的城市而言,城市化的發展軌跡不僅在于讓農民成為市民,更重要的是要為他們解決就業、安居、教育、醫療和交通等問題,并為其提供相應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基本公共服務[21]。通過對城郊農民的多次訪談發現,對于大多數農民而言,進城買房成為市民不是最關鍵的,下一代能夠在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才是其真正城市化的關鍵。對于農民家庭而言,城市不僅意味著有更好的教學質量,在學校管理方式、班級環境以及課業輔導等方面都比在城郊地區要強。那么,家庭為子代追求更高層次教育質量的背后,實質為職業選擇存在差異性,優質的就業崗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教育水平決定的,并且崗位的好壞還會影響其社會地位。布迪厄認為,教育作為文化資本的重要構成部分,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一方面,在同等工作崗位的基礎上,學歷越高收入就越多;另一方面,越是體面的職業越能彰顯社會地位。可是當下的教育培養并非精英化的培養,而是平民化的培養,但是教育資源并非拉平化,而是逐步走向市場化。之所以會走向市場化,在于有限的優質就業機會和龐大的人口基數存在張力,而教育是普通人通向優質就業機會的唯一有效渠道。如果子代無法在學校獲得良好的受教育機會,不僅很有可能變成問題青年,還會在社會競爭中被淘汰。同時,哪怕他們進入社會之后再參與競爭,但競爭的對象卻變成了資本,成功的概率更為渺茫,這就可以解釋很多農民家庭從農村遷移到城市就是為了讓子代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么,教育作為公共服務的重要內容,自然成為很多家庭重點關注的對象,尤其是已經實現城市化的家庭,對于教育的作用更為重視,這是其可以獲得優質職業并且實現階層流動的開放渠道。因此,農民家庭對于教育等公共服務的追求成為其深度城市化的動力以及階層躍升的重要基石。可以說,農民城市化的動力都是圍繞其生活需求和階層需求而展開的,在農民已經實現市民化之后,他們就開始追求更高質量的城市化。城市化不僅是一代人的進入,也是下一代人的融入,所以他們會更加在意教育,追求本身的階層晉升意義。由此可見,我國的城市化是一種吸引性的城市化,中西部的農民以農村作為保障,以進城作為階段性目標而產生漸進式遷移。而城郊農民則以中心城區作為方向,以城市內部的優質教育服務作為發展性的目標,以實現家庭下一代中產化的遞進式躍升。
四、深度城市化的實踐機制:從房產投資到教育投資
對于農村家庭來說, 進城買房和重視教育這兩個目標, 是家庭追求階層流動的短期目標,也是階段性目標[22]。而家庭發展目標卻無法通過一代人的力量來實現,在家庭經濟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只有通過代際支持的方式方能幫助子代實現城市化。
(一) 代際支持與子代城市化
代際支持是當前我國農民家庭城市化最為直接和有效的途徑,在中國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中,“家庭本位”賦予中國家庭更大的能動性和自主性,形成了“個體—家庭—社會”的結構模式。家庭不僅是資源、權力和倫理等要素的拼湊疊加,而且還是一個有機實體:家庭不僅具有超越于家庭成員個體之上的價值,且具有相對獨立于社會系統的自主性[23]。基于此,家庭在面對現代性的沖擊之下,不僅沒有呈現出家庭結構消解的樣態,相反還在家庭內部自發地形成一套家庭發展秩序,來應對家庭再生產、擴大化家庭再生產等家庭發展目標,以代際支持來實現家庭向上流動的目標和任務。因此,以傳統中西部地區農村為代表的新三代家庭,和以城郊農村為代表的新聯合家庭就成為農民家庭城市化的重要支持,而家庭成員的支持既包括經濟支持,也包含勞動力支持,父代不僅需要在經濟上支援子代在城里買房、安家,還要成為“老漂”幫助帶孫子,為子代的城市化減輕經濟壓力和生活負擔。
(二) 家庭房產投資與城市化實現
無論是城郊農民還是中西部地區農村男性,僅憑借自己外出打工到城里買房已超出其經濟承受能力,這客觀上需要父代進行代際支撐才能完成,于是,父代就成為子代進城買房的重要力量。城郊農民進行房產投資主要是依靠家庭收入不低的本地務工機會,高家庭積累是城郊農村家庭可以順利城市化的保障。由于本地就業市場的優勢,可以很好地吸納本地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工作,實現城郊農民家庭的就業非農化。所以,家庭可支配勞動力的務工收入就高于一般的中西部地區,年輕人一般都會進入企業、工廠或者 機 關 單 位 工 作 , 每 個 月 有 3000~6000 元 的 收入;對于四五十歲的勞動力可以選擇做保安、聯防 隊 員 或 者 進 廠 做 一 線 工 人 , 也 有 3000~4000 元/月的收入;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也有工作機會,比如綠化、保潔、環衛等工作,一個月也有 2000 多的收入;即使是 70 歲的老人,也可以從事和水泥等散工,收入也有 100 元/天。雖然個體所能獲得的收入與年齡、性別與勞動技能等多重因素相關,但是整體的家庭收入卻是個體收入的整合。城郊地區農村依靠于本地務工市場,整體家庭成員可以被完全嵌入到勞動力市場中,每一份就業機會,都能幫助子代順利進入城市,實現城市化。這也是他們與中西部地區農民“半城市化”的不同之處,本身家庭經濟積累能力能為子代的城市化提供源源不斷的支持與保障,從而實現子代家庭的完全城市化。因此,城郊村農民進城購房的比例較高,如東西湖區農民進城購房率可能達到 80%~90%,父母都會為子女購置一套房子,雖然地理位置比較偏,但子代在城市就有了一處安身立命的地方,生活不至于太窘困。
(三) 家庭教育投資與城市化實現
如 果 將 城 市 階 層 劃 分 為 貧 弱 階 層 、 普 通 階層、中產階層和富裕階層,那么農民所實現的城市化主要是一種初級城市化。進城農民只是成為城市普通階層,如果進城農民對子女的期待只是過普通階層的生活,只要能夠在城市找到一份可以支付生活開支的工作就可以了。如果進城農民還想進一步城市化,即中產化,那么他們就會存在三筆開支,自住房的房貸開支、城市生活開支和教育投資。那么,父代的支持并沒有隨著子代結婚和進城購房而結束,父代仍然要在日常生活中支持子代,即產生“啃老”現象。
在 S 大隊調研時發現,當地農民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投資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日常課業輔導。該地區的學生從小學開始便參與正規的市場化培訓,一般的家庭都會為孩子選擇輔導班。在訪談時不少家長都表示,送孩子上輔導班實屬無奈之舉,畢竟周圍人都在補習,誰也不想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并且,每年給孩子上輔導班的費用并不低,這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以一個初中生為例,每年投入在他身上的補習班費用就需要 1 萬~2 萬元,其中補習的內容包括應試教育考試的科目,就連作文寫作都被納入到補習的范疇。在訪談時,一個初中生向我們“訴苦”:除了政治,所有的科目他都補習過。而補習的時間除去正常的寒暑假,孩子在周末也要參加補習班,密集的補習不僅讓農村家庭的教育競爭愈演愈烈,也成為家庭一筆不小的開支。另一方面,興趣、特長班培訓。如果說孩子在上初中之后主要的輔導來自課業輔導,那么在小學、幼兒園階段,則以興趣班、特長培養的方式開展教育投資,因為興趣、特長可能會讓孩子在未來的入學考核、評獎中增加勝出。因此,特長培養和學業輔導成為當地家庭最為重要的兩項教育投資,由此當地家庭一年花在教育上的費用高達 2 萬元左右。同時,教育環境同樣重要,這決定了孩子的教育學習環境和學習氛圍,所以,這也是很多家庭選擇優質學區的重要因素。可以看到,農民家庭對于子代教育的投入是巨大的,而教育投資不僅需要為子代提供一個良好的教育環境,還要為孩子提供各種課業輔導與興趣培養,教育投資的巨大費用,這對家庭經濟實力有一定的要求。同時,孫代實現中產的目標是全部嵌入于整個家庭的發展目標之中,因此,父代有“義務”幫助子代家庭減輕一部分的經濟負擔。而父代能夠提供的教育投資分為大額的一次性開銷和小額的日常開銷。
一方面,學區房的首付。對于子代而言,優質的學區房價格遠比一般地區的房價要高,東西湖的房價在 1萬左右,但是在其他中心城區的房價遠不止 2萬,而僅憑子代的工資收入難以在短時間內支付首付。因此,很多城郊地區的農民家庭,都由父母支付首付,由孩子支付貸款,以雙方共同承擔一部分的方式購買優質教育資源的房子。另一方面,日常撫育的不間斷經濟支持。父代除了本身務工積蓄外,土地流轉費、養老金以及房租都能成為農民家庭的經濟收入來源。首先,土地流轉收入,在本地,農民每年獲得的土地流轉費為 10 500 元/公頃,每戶至少有 1. 3 公頃承包地①,每個農戶家庭的土地流費用至少有 1. 4 萬。有的農民會保留 0. 1 公頃地,在 60 歲之前 “一邊拿退休金,一邊種地”,減少生活開銷。其次,養老金收入。東西湖是農場體制,1993 年之前,國家為每一個農場成員都購買了社保,雖然在 1993 年農場改革后,新進成員都是自然人,但是他們也會選擇自行購買社保。所以,每個職工的退休工資都在 2000~3000 元/月不等,兩個老人一年的退休金就有 7 萬元左右。最后,房租收入。由于城郊地區距離城市的空間距離近,通勤時間短,深受沒有能力進城買房的外來務工人員青睞,有一些小組甚至有 60% 的來漢務工者,他們大都選擇租一居室,面積大約是 30m2 左右,價格大約為 800~1000 元/月。因此,郊地區農民家庭父代的收入情況較好,一般有土地收入、多份打工收入 (五口之家可以有 3~4 份打工收入)、地租收入和退休金收入等多重收入。而他們會將一部分收入用來支持子代家庭的生活開支。筆者在調研時發現,不少父代都或明或暗地為子代提供經濟支持,有的父母每個月會給孩子打錢,多則 3000 元,少則 1000 元,作為一種經濟資源輸入給子代;有的父母則選擇間接給孩子錢,通過為孫子繳納補習班、興趣班費用的方式,間接減輕子代的經濟負擔。
五、結論
隨著我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當前我國已經從“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轉變。相較于普通中西部農村,城郊農民依托于特有的文化和經濟基礎可以輕易實現居住、就業和生活方式的淺度城市化,但城郊農民的城市化并未由于已達到基本城市化目標而停止,相反還存在“二次”城市化的傾向,這種特有的大城市郊區農民家庭城市化類型和樣態可以被稱之為深度城市化。本研究通過對其表現形式、動力來源以及實現方式等三方面的分析和論述來解釋城郊農民家庭的城市化邏輯。首先,居住城市化、就業城市化和生活方式城市化并非農民城市化的終極目標,他們還存在居住空間從邊緣到中心,就業方式從非正規就業到正規就業以及生活方式從低消費到高消費的三重提升。其次,觸發城郊年輕人深度城市化的根源在于,優質的教育資源向城市中心集聚,而教育資源是決定子代階層躍升的重要工具。因此,形成了以城市優質公共服務需求為核心的深度城市化動力。最后,城郊地區之所以可以滿足子代家庭的深度城市化目標,在于父代能為子代提供的代際支持,而代際資源更多是以教育投資的名目向下傳遞給子代。父代由于較為豐富的經濟收入,可以為子代提供關鍵大額和瑣碎小額的經濟資源,讓子代家庭逐步地向更高階層邁進,從而更好地實現他們高品質的城市夢。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