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jì)中國出現(xiàn)的一批有影響力的紀(jì)錄片在敘事方式和技巧上已經(jīng)不同于以往的直接宣教模式,開始呈現(xiàn)出獨(dú)特的敘事張力,創(chuàng)造了一次次敘事的神話。從重構(gòu)民族情感經(jīng)驗(yàn),到注重紀(jì)錄片本身的各種張力組合,再到利用有儀式感的敘事技巧,當(dāng)代紀(jì)錄片將宣教潛移默化于民族情感中,通過儀式的形式和技巧打造新的文化表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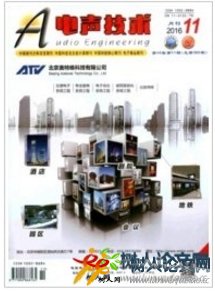
《電視技術(shù)》(月刊)創(chuàng)刊于1977年,由中國電子科技集團(tuán)公司第三研究所主辦。系信息產(chǎn)業(yè)部主管的我國電聲專業(yè)中文核心期刊及引文源刊物。以應(yīng)用技術(shù)為主、兼顧學(xué)術(shù)與科普,以技術(shù)交流為主、兼顧市場信息與產(chǎn)品商情,在電聲專業(yè)領(lǐng)域起技術(shù)向?qū)Ш彤a(chǎn)品推廣作用。
在當(dāng)下日益追求視覺盛宴和奇觀感受的媒介環(huán)境里,真實(shí)記錄使紀(jì)錄片本性里的精英姿態(tài)在面對市場需求時(shí)似乎顯得底氣不足。在中國紀(jì)錄片處于頸瓶發(fā)展時(shí)期,創(chuàng)作者和理論界曾動搖過試圖使其轉(zhuǎn)向“娛樂化”,但是在對紀(jì)錄片本體發(fā)展和紀(jì)錄片市場狀況的平衡分析中我們發(fā)現(xiàn)一味地迎合觀眾的需求并不是紀(jì)錄片的最終走向。 不同于電影、電視劇等帶有明顯大眾色彩的媒介消費(fèi)品,紀(jì)錄片的精英特性使其在考慮其本性特征與市場現(xiàn)實(shí)之間的差異問題時(shí),尋求市場的最大化與堅(jiān)守紀(jì)錄片本身特性之間的平衡,成了考驗(yàn)紀(jì)錄片發(fā)展的一個(gè)重要問題。《舌尖上的中國》 兩季的播出猶如神話一般的持續(xù)發(fā)酵給處于發(fā)展中的中國紀(jì)錄片探尋出了一些新的啟示,在這場由紀(jì)錄片發(fā)起的文化狂歡里,中國
新世紀(jì)紀(jì)錄片的敘事和文化表征轉(zhuǎn)向匯聚于此。 在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國際合作的背景下,伴隨著現(xiàn)代西方真實(shí)記錄理念的深入影響和對早期格里爾遜“ 畫面 +解說”模式的進(jìn)一步升華,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者開始帶著個(gè)人視角的引入、對等的話語言說和影像空間感受的強(qiáng)化等敘事手法將紀(jì)錄片的敘事和文化傳達(dá)推向一個(gè)新的高度。
符號學(xué)大師羅蘭· 巴特對神話的界定:“ 神話是一種言說方式。” [1] 作為神話言說方式的載體廣泛存在于各種文字信息、照片、電影、廣告、表演等內(nèi)容中,在不同場合中“ 表達(dá)著一個(gè)民族或一種文化的基本價(jià)值觀” [2]8 。 早在 20 世紀(jì) 80 年代《 話說長江》熱播,到90 年代《 望長城》 掀起的新紀(jì)錄運(yùn)動,紀(jì)錄片的言說神話已經(jīng)初見端倪。 再到新世紀(jì)之后
《舌尖上的中國》受到熱捧,從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紀(jì)錄片作為一種言說方式在將傳統(tǒng)的畫面、解說以及音樂等敘事元素重新鍛造打造出自己的時(shí)空場形成神話效果。這里的神話不是某種神話傳說文本,而是在紀(jì)錄片的話語體系里建立起來的各種合理崇高的價(jià)值系統(tǒng)和文化表征。 這種價(jià)值系統(tǒng)和文化表征是蘊(yùn)含在影像畫面和話語之內(nèi)的,而不是裸露在解說、畫面、音樂之外的。如在《話說長江》《 再說長江》《絲綢之路》《 新絲綢之路》《河之南》《 美麗中國》《春節(jié)》《 舌尖上的中國》《 大黃山》 等系列紀(jì)錄片里通過長鏡頭和蒙太奇的切換,加上充滿抒情意味的解說詞,將祖國的大好河山和人文景觀完美地建構(gòu)在觀眾的記憶之中。通過影像技術(shù)、解說話語等敘事表現(xiàn)技巧的變化,當(dāng)代電視紀(jì)錄片的文化表征也在發(fā)生轉(zhuǎn)向,從對民族情感的強(qiáng)化,對民族公共記憶的回憶,到對當(dāng)下個(gè)體生活形態(tài)的關(guān)注、記錄和升華凝練,集聚在電視紀(jì)錄片里的不再是沒有經(jīng)過緩沖過濾過的強(qiáng)烈意識形態(tài)教化,而是通過生活化的同期聲和具有審美性的影像表達(dá)傳達(dá)出親切而又宏大的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其中,紀(jì)錄片《 舌尖上的中國》利用食物帶來的感官刺激通過精美的鏡頭畫面和理性的解說語言挑逗起來的不僅是觀眾的味蕾,更是對基于食物這一本體基礎(chǔ)上的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共同體的重構(gòu)。從當(dāng)代一系列紀(jì)錄片成功播出之后我們還可以看出,紀(jì)錄片可以通過重構(gòu)民族情感經(jīng)驗(yàn)、形成神話張力、彰顯儀式力量等方式在內(nèi)在敘事和外在接受機(jī)制里建立起一套能強(qiáng)化文化力量的敘事模式,在堅(jiān)守紀(jì)錄片真實(shí)的精神家園的同時(shí),尋找到與市場的最大契合。
1 重構(gòu)民族情感經(jīng)驗(yàn)
隨著電視拍攝技術(shù)的進(jìn)步,機(jī)器對影像的留存可以突破時(shí)間和空間的限制,紀(jì)錄片在影像的敘事中將全國各地關(guān)于歷史的、自然的、日常生活的,甚至是美食的某一主題拼湊在一起,為觀眾打造出一場場激蕩在心靈上的盛宴。而與此同時(shí),大量的解說也在釋放著濃烈的民族情感,從上下五千年朝代帝王更換到被歷史封存許久后露出神秘面紗的古代文物,再到歷史變幻后先賢智慧在今日中國文化中閃耀的民族光輝;從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多樣化到各種生物精靈的生命歷程對自然的依賴,再到自然對人類的饋贈;從廣闊土地對多樣食材的賜予到勞動人民在勤勞和智慧中對各種食物的駕馭,再到中華民族對家文化的尊崇,解說將所有有關(guān)中華民族的情感經(jīng)驗(yàn)投射在每個(gè)觀眾個(gè)體心中。
1.1 民族的集體記憶
在社會的發(fā)展進(jìn)程中,人類的情感帶有一定的社會繼承性,呈現(xiàn)出一種經(jīng)驗(yàn)式的集合。分析心理學(xué)創(chuàng)始人榮格在其老師弗洛伊德的個(gè)體無意識理論基礎(chǔ)上反駁提出了集體無意識學(xué)說,他認(rèn)為“ 種族記憶或集體無意識是潛藏在每個(gè)人心底深處的超個(gè)人的內(nèi)容” [2]4 。 個(gè)體在群體的環(huán)境中生存,個(gè)體的情感及其衍生出來的行為受群體意識的影響,這種群體意識包括現(xiàn)實(shí)集體的偶然情感、思維方式和思想傾向等,還包括往時(shí)傳統(tǒng)的記憶以及形成的集體情感經(jīng)驗(yàn)。
“ 在歷史記憶里,個(gè)人并不直接去回憶事件:只有通過閱讀或聽人講述,或者在紀(jì)念活動和節(jié)日的場合中,人們聚在一塊兒,共同回憶長期分離的群體成員的事跡和成就時(shí),這種記憶能被間接地激發(fā)出來。” [3] 在群體社會里,人們通過回想和回憶來對某一民族或某種文化產(chǎn)生追思和認(rèn)同,在不斷延續(xù)和繼承下產(chǎn)生的民族記憶里使每個(gè)個(gè)體在群體或群體
其他個(gè)體的影響下或潛藏或浮現(xiàn)起濃烈的民族情感,于是個(gè)體與回憶之間的虛構(gòu)關(guān)系才有機(jī)會重構(gòu)成現(xiàn)實(shí)的民族情感經(jīng)驗(yàn)。 “ 無論時(shí)序如何轉(zhuǎn)換,春節(jié)總是牽動著每一個(gè)中國人的心” ( 紀(jì)錄片《 春節(jié)》解說詞);“ 為了尋找長江的來龍去脈,中國人在長江沿線默默探索了 2000 多年”( 紀(jì)錄片《 再說長江》第一集《大江巨變》),紀(jì)錄片通過全知全能的解說將“ 中國”“ 中國人” 的民族情感召喚化解在解說的文本內(nèi)容里,集體記憶和民族情感在恢弘的畫面和解說渲染下不斷暗示著電視機(jī)前的觀眾,讓其感受到相同的情感。紀(jì)錄片作為真實(shí)記錄的忠實(shí)堅(jiān)守者,影像的時(shí)間和空間共存性使它在傳達(dá)民族的集體記憶上比文字和圖片都要直觀和豐富,因此,當(dāng)代紀(jì)錄片在延續(xù)民族記憶和傳承民族文化方面承擔(dān)著更多的責(zé)任。
1.2 從集體記憶到個(gè)體情感
人類社會中的集體記憶可以通過神話、宗教、儀式以及各式信息技術(shù)等傳播給個(gè)體,個(gè)體并不單獨(dú)地進(jìn)行回想和回憶,往往需要借助他人的回憶或講述來完成自己對歷史的拼貼并形成對集體的情感經(jīng)驗(yàn)。
紀(jì)錄片是經(jīng)由媒介傳達(dá)出來的有關(guān)過去時(shí)空的信息傳播,在它所涉及到的有關(guān)集體的記憶回想里,受眾往往是在共同的歷史、文化、社會等因素影響下體會到紀(jì)錄片里的某種情感呼喚或命運(yùn)經(jīng)歷。個(gè)體在社會大他者的長期熏陶下極易對歷史和社會的這些集體記憶產(chǎn)生情感認(rèn)同,進(jìn)而產(chǎn)生了某些集體意
2 形成神話張力
當(dāng)代紀(jì)錄片受眾在多元化媒介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影響下,大多已不再能接受帶有明顯主旋律意味或意識形態(tài)指引的宣教內(nèi)容。 從1990 年拍攝的《 望長城》開始,宏大敘事的鏡頭開始轉(zhuǎn)向了個(gè)體生活的當(dāng)下現(xiàn)場,個(gè)人話語開始在紀(jì)錄片中普遍出現(xiàn)。雖然在《再說長江》《新絲綢之路》《故宮》《森林之歌》《美麗中國》《舌尖上的中國》 等當(dāng)代紀(jì)錄片身上溫情表達(dá)方式并不能夠完全遮掩它所透露出來對民族自豪感的主旋律贊嘆,但十分可貴的平民視角已經(jīng)在盡可能地規(guī)避宏大敘事模式。不同于硬性的意識形態(tài)灌輸,當(dāng)代紀(jì)錄片通過呈現(xiàn)各種人文地理的、歷史的宏大場景與現(xiàn)實(shí)生活中難以企及的矛盾形成紀(jì)錄片身上特有的神話張力來引爆觀眾對紀(jì)錄片內(nèi)容本身的感知刺激。
2.1 宏大場景的肅然起敬感與現(xiàn)實(shí)生活的空缺感之間的沖突
如同戲劇的結(jié)構(gòu)敘事一樣,矛盾和沖突是將情節(jié)內(nèi)容推向高潮的助推器。只是在像戲劇這樣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里,矛盾和沖突發(fā)生在內(nèi)容,而在紀(jì)錄片中,對真實(shí)記錄本質(zhì)的要求使之較難有機(jī)會主觀地安排情節(jié)內(nèi)容的沖突和對抗。 正因?yàn)槿绱耍o(jì)錄片震撼性的體現(xiàn)經(jīng)常發(fā)生在紀(jì)錄片內(nèi)容本身與觀眾現(xiàn)實(shí)個(gè)體體驗(yàn)之間的差距沖突上。無論是歷史類題材紀(jì)錄片中某一歷史片段的還原對觀眾現(xiàn)實(shí)碎片化記憶的沖擊,還是自然類題材紀(jì)錄片中被放大了的生物植物生存狀態(tài)的記錄對觀眾現(xiàn)實(shí)模糊認(rèn)識的補(bǔ)缺,還是社會類題材紀(jì)錄片中對邊緣人物別樣生活和文化的展現(xiàn)與主流大眾生活狀態(tài)的對比,都在表明紀(jì)錄片內(nèi)容表現(xiàn)與受眾個(gè)體觀看感受之間存在某些差距,它們是紀(jì)錄片文本內(nèi)容存在沖擊性的體現(xiàn),是紀(jì)錄片以特有的言說方式形成某種神話張力并使之產(chǎn)生普適化傳播效果的一種方式。
當(dāng)代中國紀(jì)錄片在受到觀眾熱烈追捧的時(shí)候,也有人看到了它背后的主旋律意味,只是不同于以往的宣教紀(jì)錄片,它正在積極尋求通過對個(gè)體個(gè)性化記錄的方式來打破宣教模式里的宏大敘事,以潛移默化的形式讓人產(chǎn)生民族認(rèn)同。以《 再說長江》為代表的祖國山河系列紀(jì)錄片中將在麗江古城經(jīng)營積沙的李實(shí),對故鄉(xiāng)充滿留戀的三峽移民胡志滿,以及給南京城墻拉琴的市民張福榮等通過個(gè)人話語的表述表達(dá)了對各自所在土地的熱愛,觀眾在紀(jì)錄片封閉的觀賞空間里對他者的認(rèn)同感油然而生,彌補(bǔ)了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中有限的生存體驗(yàn)下對民族認(rèn)同感的不足。紀(jì)錄片《 舌尖上的中國》 中對家場景的描繪和對勞動豐收喜悅場景的描繪通過特寫、俯拍、拉伸鏡頭的方式展現(xiàn)出一幕幕令人肅然起敬的宏大場景,如第二季《 心傳》 中對黃土高原上張世新家曬掛面的特寫,《家常》中太行山懸崖邊緣趙小有家玉米地的俯拍,還有散落在紀(jì)錄片結(jié)尾的各種推拉搖移等鏡頭都給紀(jì)錄片在視覺上提供了牽引力,它們與受眾有限的現(xiàn)實(shí)體驗(yàn)是不同的。
3 彰顯儀式力量
對現(xiàn)實(shí)真實(shí)的追求是紀(jì)錄片的靈魂,攝像技術(shù)對當(dāng)下發(fā)生的事情可以同期記錄,但問題卻是觀眾不需要一個(gè)流水賬似的影像呈現(xiàn),他們需要聆聽類似于故事式的轉(zhuǎn)述和再現(xiàn)。對于今天的紀(jì)錄片來說,蒙太奇技術(shù)、攝像特技技術(shù)和解說詞的藝術(shù)賦予了紀(jì)錄片更多的表現(xiàn)方式,它們在現(xiàn)代觀眾日益增多的媒介接觸體驗(yàn)下變得一點(diǎn)也不造作。 形式的創(chuàng)新似乎還沒來得及被普通觀眾所質(zhì)疑就堂而皇之地走進(jìn)了紀(jì)錄片的陣地,以前沿的姿態(tài)為真實(shí)記錄提供變幻莫測的形式,構(gòu)建出一種關(guān)于時(shí)間、關(guān)于文化、關(guān)于情感的隱秘神話系統(tǒng),在有關(guān)于紀(jì)錄片的深層結(jié)構(gòu)里埋設(shè)許多儀式的精神。
“ 儀式是人的一種有目的的活動,它以無意識的外在形態(tài)反映著人的有意識的行為,以非理性的舉動為理性的目的服務(wù)。” [2]129 在紀(jì)錄片中,轉(zhuǎn)述和再現(xiàn)出來的故事需要人為等待或意外獲得,它無法像電影或其它藝術(shù)樣式那樣經(jīng)歷虛構(gòu)來完善結(jié)構(gòu),因此,現(xiàn)代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者們在恪守真實(shí)記錄的本質(zhì)前提下,開始挖掘真實(shí)記錄的內(nèi)容,以賦予其崇高感的方式將它們儀式化,使它們變得有意義,甚至成為某種精神紀(jì)念。儀式感的突出在當(dāng)代紀(jì)錄片中通常主要通過以下路徑:有力量的解說,有意義的影像表征,以及儀式性的過渡和結(jié)尾。
這些有儀式感的敘事特征在《 話說長江》之后的大型紀(jì)錄片里表現(xiàn)明顯,而在《 舌尖上的中國》 里表現(xiàn)尤為突出。 隨著《 舌尖上的中國》 第二季的陸續(xù)推出,“舌尖體”開始在網(wǎng)絡(luò)上紅火,如“蜂蜜 80%的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作為早期人類唯一的甜食,蜂蜜能快速產(chǎn)生熱量、補(bǔ)充體力,這對我們的祖先至關(guān)重要。和人工提取的蔗糖不同,蜂蜜中的糖不經(jīng)過水解,就可以直接被人體吸收。 在中國的廚房,無論烹飪菜肴,還是制作甜點(diǎn),蜂蜜都是其他糖類無法替代的。”(《舌尖上的中國》 第二季第一集《 腳步》)類似的“舌尖體”僅在第一集中就多達(dá)五處,令觀眾耳目一新。 “舌尖體”采取全知全能的解說姿態(tài),以理性的方式傳達(dá)信息,用客觀性因素支持主觀性話語,產(chǎn)生強(qiáng)勢基調(diào)。不同于前幾年紀(jì)錄片娛樂化敘事的傾向,《舌尖上的中國》 在原本通俗的題材上構(gòu)建理性的姿態(tài),將普通人的日常飲食、勞動通過有力量的解說轉(zhuǎn)化為一場意識,形成權(quán)威的力量。
4 結(jié)論
當(dāng)代中國紀(jì)錄片無疑取得過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從中可以摸索出對中國紀(jì)錄片發(fā)展有益的一些敘事經(jīng)驗(yàn)。 重構(gòu)民族情感經(jīng)驗(yàn)是一項(xiàng)可以拉近觀眾與紀(jì)錄片距離的重要內(nèi)容,紀(jì)錄片自身與觀眾之間存在的神話張力無形中能使紀(jì)錄片找到一條親近觀眾的渠道,而紀(jì)錄片中彰顯出來的儀式力量則為紀(jì)錄片的神話言說提供了各種方式和途徑,這三者的結(jié)合一定程度上能使觀眾擺脫對紀(jì)錄片的距離感,同時(shí)又能產(chǎn)生肅然認(rèn)同的莊嚴(yán)感。紀(jì)錄片敘事神話的構(gòu)建為紀(jì)錄片在今天媒體市場中贏得觀眾的喜愛找到了一個(gè)新的方向,然而重構(gòu)民族情感經(jīng)驗(yàn)、形成神話張力、彰顯儀式力量并不是構(gòu)建紀(jì)錄片敘事與文化表征僅有的三種方式,在未來的紀(jì)錄片發(fā)展進(jìn)程中,關(guān)于紀(jì)錄片的內(nèi)在敘事和外在接受機(jī)制里建立起來的敘事神話或許還將有新的突破。
參考文獻(xiàn):
[ 1 ]羅蘭· 巴特.神話修辭術(shù)批評與真實(shí)[ M].屠友祥,溫
晉儀,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69.
[ 2 ]葉舒憲,編選.神話———原型批評[ M].西安:陜西師范
大學(xué)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2.
[ 3 ]莫里斯· 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 M].畢然,郭金華,
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3.
[4 ]塞奇· 莫斯科維奇.群氓的時(shí)代[ M].許列民,薛丹云,李繼紅,譯.南京:鳳凰出版?zhèn)髅郊瘓F(tuán),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6.
[ 5 ]波德里亞.消費(fèi)社會[M].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
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4:2.
[ 6 ]劉燕.鮑德里亞的后現(xiàn)代傳媒理論與媒介現(xiàn)實(shí)的構(gòu)建
[J].國際新聞界,2005(3):62.
[ 7 ]鐘大年,雷建軍.紀(jì)錄片:影像意義系統(tǒng)[M].北京:北
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6:200.
[ 8 ]石屹.電視紀(jì)錄片———藝術(shù)、手法與中外關(guān)照[ M].上
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0:122.
[9 ]尚必武.當(dāng)代西方后經(jīng)典敘事學(xué)研究[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3:86.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