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時(shí)期蒙古族就開始參加科舉考試,由于元代統(tǒng)治者重武輕文的理念,因此與清朝相比,蒙古族科舉考試在規(guī)模和水平等方面相當(dāng)落后。早在八旗入關(guān)以前蒙古旗人就已經(jīng)參加后金汗國(guó)舉行的科舉考試,但此時(shí)的八旗科舉還未定型,相關(guān)記載也較少。伴隨著清王朝的建立及鞏固,八旗蒙古科舉制度也逐漸發(fā)展,并最終形成了一定規(guī)模。在清軍入關(guān)以前,皇太極為了大規(guī)模選拔人才,進(jìn)行了三次科舉考試,為大量選拔優(yōu)秀人才,其積極鼓勵(lì)滿族以外的漢族及蒙古族人士應(yīng)試,一些為了博取功名的蒙古人便積極參加,部分人順利入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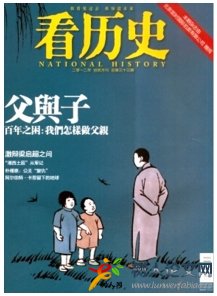
《看歷史》是中國(guó)第一本‘以新聞方式發(fā)現(xiàn)歷史’的新銳歷史雜志。由成都先鋒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運(yùn)營(yíng),采編團(tuán)隊(duì)為來(lái)自國(guó)內(nèi)主流媒體的資深編輯記者,同時(shí)約請(qǐng)國(guó)內(nèi)外知名專家學(xué)者及社會(huì)名流為本刊供稿。讀者群:通常為25~45歲的城市中堅(jiān)力量。具有一定經(jīng)濟(jì)基礎(chǔ)之后而欲求真相、求知識(shí)、開眼界的中產(chǎn)階層;具有一定閱讀興趣和閱讀品位的白領(lǐng)、企業(yè)經(jīng)營(yíng)管理人員、黨政干部、知識(shí)分子、大學(xué)生等。
清朝入關(guān)以前,由于連年戰(zhàn)爭(zhēng)及政權(quán)不穩(wěn),統(tǒng)治者并沒(méi)有采取較為系統(tǒng)的選拔官吏的方法,加之努爾哈赤起兵后,長(zhǎng)期處于戰(zhàn)爭(zhēng)狀態(tài),根本無(wú)暇顧及對(duì)人民的文化教育,而且努爾哈赤對(duì)知識(shí)分子恨之入骨,這些均造成了重武輕文的社會(huì)風(fēng)氣。皇太極繼位后,參閱歷代王朝治世經(jīng)驗(yàn),認(rèn)為文治與武治同等重要,開始改變努爾哈赤時(shí)期的重武輕文政策,關(guān)注文治并舉行科舉考試進(jìn)行知識(shí)分子的人才選拔。
后金具有科舉性質(zhì)的考試始于天聰元年( 1627年) 八月。此次中式者的基本情況史籍中沒(méi)有記載,八旗蒙古中式者的情況自然也就無(wú)從知曉了。天聰三年( 1630 年) ,皇太極提到: “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貝勒等包衣下,及滿洲、蒙古家為奴者,盡皆拔出。”[1]由此可見(jiàn)皇太極選拔人才范圍之廣,積極鼓勵(lì)蒙古旗人及家奴參加科舉。但這次考試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舉考試。后金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科舉考試是在天聰八年( 1634 年) 三月。在此次考試中,采取了正規(guī)考試形式,參加者不僅有滿人、漢人還有蒙古旗人。“禮部考取通滿洲、蒙古、漢書文義者為舉人。十六人各賜衣一裘,免四丁,宴于禮部。”[2]意在從滿族、漢族以及蒙古族當(dāng)中選拔優(yōu)秀的人才。
后金歷史上第二次科舉考試是在崇德三年( 1639 年) 八月。此次考試與以往有些不同: 禮部明確規(guī)定滿洲、蒙古、漢人普通諸生( 非家奴身份者)可以參加“生儒考試”[3],但是家仆身份者一律不準(zhǔn)參加考試。盡管祖可法、張存仁就此上奏皇太極,望能讓家仆亦參加科舉考試,最終被駁回,此次科舉考試具有重要意義。早在 1642 年,大學(xué)士范文程等就奏請(qǐng): “于滿、漢、蒙古內(nèi)考取生員舉人。”[4]皇太極欣然接受,滿洲統(tǒng)治者在崇德六年( 1642 年) 六月舉行了入關(guān)前最后一次科舉考試。在此次考試中滿洲人鄂謨克圖、蒙古人杜當(dāng)、漢人崔光前等七名中式舉人,除蒙古旗人杜當(dāng)中舉外,也有幾名蒙古旗人中秀才。
清朝入關(guān)以前,滿洲統(tǒng)治者還沒(méi)有取得全國(guó)政權(quán),舉行的科舉考試也只是小范圍的,參加人數(shù)極其有限。雖然蒙古族是滿洲的重要同盟者,限于當(dāng)時(shí)的條件,蒙古舉人、生員數(shù)量很少,但是它畢竟使蒙古旗人開始接受教育,八旗蒙古人不僅學(xué)習(xí)了滿、蒙文字還接受了漢族傳統(tǒng)的儒學(xué)教育,其作用與意義不容忽視。通過(guò)接受教育,八旗蒙古已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礎(chǔ),為他們?nèi)腙P(guān)后大規(guī)模參加科舉考試積累了經(jīng)驗(yàn),創(chuàng)造了條件。
一、文科
隨著清王朝的建立,清政權(quán)趨于穩(wěn)定,為全國(guó)性科舉考試的開展提供了良好條件,故順治八年( 1651 年) 詔令八旗開科取士。在這一年,也允許駐京八旗蒙古子弟參加考試。有關(guān)八旗蒙古科舉制度的一些規(guī)定開始建立起來(lái)。每項(xiàng)制度從建立到完善需要根據(jù)具體情況做出相應(yīng)變化。八旗蒙古科舉制度經(jīng)歷了不斷完善和發(fā)展的過(guò)程。
( 一) 童生試
清代科舉制度承明代科舉之制,其童生三級(jí)試與科舉三級(jí)考試均仿明制。清代童生考試包括縣試、府試與院試三個(gè)層面。清代的童生與明代一樣,不論年齡大小,只要沒(méi)有取得縣、州、府學(xué)資格,即為童生。清代童生縣試一般在二月舉行,其考試童生要在試前向所屬縣署報(bào)名,并具寫姓名、年齡、籍貫和上三代已仕未仕等相關(guān)履歷,并取具同考五人之互相保結(jié)。清代童生的第二階段考試為府試,各省直隸州廳考試亦與此同。府試時(shí)間一般在四月,如有考生因故未參加縣試,則需補(bǔ)考一場(chǎng)后再行府試。
府試第一場(chǎng)亦為正場(chǎng),取錄者可直接參加院試; 第二場(chǎng)以后則憑自愿原則; 第三階段考試為院試,由各省負(fù)責(zé)教育事務(wù)的最高長(zhǎng)官學(xué)政主持。院試于各府或直隸州廳治所進(jìn)行,設(shè)有貢院,其考試規(guī)程也較為嚴(yán)格。院試一般分兩場(chǎng)進(jìn)行,正場(chǎng)考試前要先考經(jīng)古一場(chǎng),正場(chǎng)之后有復(fù)試一場(chǎng)。
順治八年( 1651 年) 三月,吏部言: “滿洲、蒙古、烏真超哈各旗子弟,有通文藝者,提學(xué)御史考試,取入順天府學(xué)”。[5]可見(jiàn)順治年間對(duì)于蒙族八旗子弟在應(yīng)考資格方面的限制還比較小。考試內(nèi)容也較容易,只試一場(chǎng),蒙古生童通滿文者作滿文文章一篇。到康熙年間有了一些新規(guī)制,康熙十年( 1671年) 提出“滿洲、蒙古既做漢文一體考試”。[5]康熙二十八年( 1689 年) ,兵科給事中能泰奏疏“考取滿洲生員,宜試騎射”。又諭曰“騎射本無(wú)礙學(xué)問(wèn),考取舉人、進(jìn)士亦令騎射。倘將不堪者取中,監(jiān)箭官及中式人,一并治罪”。[5]康熙二十八年( 1689年) 增加的騎射直到乾隆二十二年( 1757 年) 才停止。不僅如此,在考試規(guī)制方面也逐漸走向制度化,例如增加歲科兩試,蒙古生童參加童生試之前必須先通過(guò)佐領(lǐng)、參領(lǐng)考試。
對(duì)于童生試中式的蒙古生員也有了一些新規(guī)制。“從雍正年間開始,全部集中到順天府學(xué)習(xí),月給銀米,特設(shè)滿洲教授一人管教。”[6]此前則可以入順天府學(xué)習(xí),也可以留在八旗營(yíng)伍中披甲當(dāng)差。八旗蒙古被允許參加科舉考試的時(shí)間也不盡相同。駐防在盛京地區(qū)的蒙古旗人大約于康熙十二年( 1673 年) 開始參加考試。其他駐防地區(qū)大約在嘉慶四年( 1799 年) 才開始。是年,準(zhǔn)各地駐防旗人就近本省參加童生試。
( 二) 鄉(xiāng)試
鄉(xiāng)試每三年為一科,在子、午、卯、酉年舉行的為正科,遇上各種慶典下詔加開的稱為恩科。清萬(wàn)壽恩科始于康熙五十二年( 1713 年) ,登極恩科始于雍正元年( 1723 年) ,自后沿以為例。鄉(xiāng)試又被稱為秋試因?yàn)樗诎嗽鲁蹙拧⑹⑹迦炫e行。清代的鄉(xiāng)試內(nèi)容多以八股程文作為寫作要求。
八旗蒙古參加鄉(xiāng)試也始于順治八年,與童生試不同,它不只限于京旗駐防其他駐防也可以參加順天鄉(xiāng)試。《欽定大清會(huì)典事例》記載道: “遇到鄉(xiāng)試應(yīng)考年分,錄取滿洲人五十名,蒙古人二十名,漢人五十名。還規(guī)定各衙門無(wú)頂戴筆帖式也可以應(yīng)試。
如果滿洲、蒙古人中有通曉漢文的,則翻譯漢文一篇; 不通漢文的,則寫清字文一篇。順治年間對(duì)參加科舉考試的八旗蒙古人規(guī)定較寬。主要是統(tǒng)治者意識(shí)到滿蒙入關(guān)不久,漢文水平較低,所以規(guī)定較其他應(yīng)考者寬松許多。隨著滿蒙旗人漢文水平的提高,康熙六年( 1667 年) 改為與漢人同題考試。這意味著以前對(duì)蒙旗士子有利的規(guī)定不復(fù)存在。清政府做出這一改革,是因?yàn)槊晒牌烊腙P(guān)二十多年,通過(guò)清政府設(shè)立的各種學(xué)校,蒙古旗人已對(duì)傳統(tǒng)儒學(xué)有了一定的了解,可以與漢人同題考試。另一方面清政府想要通過(guò)改革抑制蒙古旗人中尚文輕武的趨勢(shì)。對(duì)于應(yīng)試者的資格要求,最初規(guī)定各衙門無(wú)品筆帖式可同生員應(yīng)鄉(xiāng)試,但到康熙八年( 1669 年) 筆帖式參加鄉(xiāng)試的優(yōu)待廢止了。八旗蒙古舉人的數(shù)量也有一定的變化。順治八年定額取蒙古舉人二十名,從康熙八年( 1669 年)起,原定蒙古舉人數(shù)額減為十名,至乾隆二十七年( 1762 年) 定為滿蒙二十七名,同治年間以輸餉增滿蒙六名,滿蒙副榜定取五名。
各省駐防生員、供監(jiān),起初必須去北京參加鄉(xiāng)試,考生必須取得京旗本管佐領(lǐng)圖片報(bào)名。嘉慶十八年( 1813 年) 開始準(zhǔn)于各駐防省份另編旗字號(hào)隨同鄉(xiāng)試。
( 三) 會(huì)試
會(huì)試是在鄉(xiāng)試之后的次年舉行,會(huì)試由禮部主持,逢辰、戌、丑、未年舉行,也是沿襲明代做法。清初會(huì)試一般在二月,雍正以后改為三月進(jìn)行,會(huì)試亦分三場(chǎng)進(jìn)行,首場(chǎng)初九日,二場(chǎng)十二日,三場(chǎng)十五日。順天府屬之舉人由該府尹給文,各省舉人取得本省長(zhǎng)官咨部文書者,八旗舉人取得本管佐領(lǐng)圖片者,候補(bǔ)京外官與教官之舉人取得省部文書者,功勛子弟及特殊賞給舉人準(zhǔn)其一體會(huì)試取得同鄉(xiāng)京官印結(jié)者,皆可向禮部投呈報(bào)考。《欽定大清會(huì)典事例》記載道: “滿洲、蒙古應(yīng)試者中有通曉漢文的人則翻譯漢字文一篇,作文章一篇; 不會(huì)漢文的人,作滿文兩篇。”康熙九年改為與漢人同試四書五經(jīng)。
對(duì)應(yīng)試者的資格要求,起初被允許參加會(huì)試的會(huì)試者范圍較寬泛,如蒙古舉人、部院蒙古博士、有品筆帖式均可參加會(huì)試。但順治十一年( 1654 年)開始,停止博士、有品筆帖式參加會(huì)試,只準(zhǔn)舉人參加。關(guān)于中式者定額,八旗自順治九年( 1652 年) 行會(huì)試,于進(jìn)士定額外,取中蒙古十名。康熙九年( 1670 年) 中額為四名,康熙三十二年( 1693 年) 為六名,此后就根據(jù)應(yīng)試人數(shù)的多寡,臨時(shí)決定,沒(méi)有具體定額。
二、武科
清王朝建立后,武舉考試基本沿襲歷代的程序和方法,統(tǒng)治者對(duì)其極為重視。八旗蒙古武試開始的時(shí)間要晚于文試,因?yàn)榍逭J(rèn)為騎射是八旗所長(zhǎng),無(wú)須應(yīng)試。故在雍正元年 ( 1723 年) 開設(shè)了八旗蒙古武科考試,武科考試也設(shè)有童生試、鄉(xiāng)試、會(huì)試三級(jí)。
( 一) 武童試
“初試士子稱為武童,但無(wú)幼童之名,以騎射技勇非成年不能有此體力,無(wú)幼慧之可言也。”[7]武童報(bào)名填寫履歷、需廩生認(rèn)保、需身家清白、不得頂替冒籍及考試程序、縣府試后送院考取進(jìn),均同文童。三年一試,學(xué)政于歲試考文童后考武童,科試之年不試武。雍正元年( 1723 年) 京師開設(shè)了滿蒙武科,不與漢人同試。凡蒙古步甲、炮甲、馬甲、九品筆帖式、庫(kù)使、養(yǎng)育兵及閑散人員皆可報(bào)名應(yīng)試。考試由兵部武庫(kù)清吏司主持。考試分內(nèi)外場(chǎng)。外場(chǎng)有三場(chǎng),第一場(chǎng)騎射、第二場(chǎng)步射、第三場(chǎng)硬弓、刀石。嘉慶十八年( 1813 年) 以后取消刀石。內(nèi)場(chǎng)考試《五經(jīng)七書》。外場(chǎng)合格才允許考內(nèi)場(chǎng)。武童試于雍正十二年( 1734 年) 停試,嘉慶十八年( 1813 年) 重新恢復(fù)考試。
( 二) 武鄉(xiāng)試
武鄉(xiāng)試是為了選拔武備人才在省城舉行的考試。考試每三年一次,與文科鄉(xiāng)試一樣,正科在子、午、卯、酉年舉行,逢慶典之年舉行恩科。武鄉(xiāng)試放寬了對(duì)應(yīng)試者的資格要求。規(guī)定“凡八旗蒙古武生員、護(hù)軍、驍騎校、領(lǐng)催、馬甲、千總、把總、七八品筆貼式、蔭生、監(jiān)生,均可應(yīng)試武鄉(xiāng)試。”[8]雍正年間,還允許蒙古文生員、翻譯生員應(yīng)試武鄉(xiāng)試,可見(jiàn)雍正年間對(duì)應(yīng)試武鄉(xiāng)試人員的資格要求更加寬松。
武鄉(xiāng)試外場(chǎng)考試內(nèi)容主要是馬射、步射、開硬弓、舞大刀、掇石。八旗蒙古武鄉(xiāng)試外場(chǎng)考試第一場(chǎng)是馬射。在武舉考試中騎射的考試方法不斷被調(diào)整。順治二年( 1645 年) 定,考生縱馬三次發(fā)九箭,中兩箭為合格; 順治十七( 1660 年) 年規(guī)定,中四箭為合格。到了康熙七年( 1668 年) 又做了一定調(diào)整改為中三箭為合格。八旗蒙古武鄉(xiāng)試考試中第二場(chǎng)是步射。豎大侯,高七尺,寬五尺。康熙十三年( 1674 年) 定,步射的距離為八十步,考生發(fā)共九箭,中布侯二者為合式。康熙三十三年( 1694 年) 定,步射的距離八十則,善射者不能多中,嗣后改為五十步,以中二者為合式。[9]( 卷七百十八)武鄉(xiāng)試內(nèi)場(chǎng)考試主要內(nèi)容: 順治二年( 1645 年)規(guī)定,鄉(xiāng)試內(nèi)場(chǎng)主要考策問(wèn)兩篇,論一篇,題目出自《四書》《武經(jīng)》。康熙年間對(duì)內(nèi)場(chǎng)考試內(nèi)容有所變動(dòng),康熙皇帝認(rèn)為,《武經(jīng)七書》內(nèi)容較為繁雜,而《孟子》中的多數(shù)內(nèi)容比較符合國(guó)情。因此,康熙四十八年( 1709 年) 定,鄉(xiāng)試內(nèi)場(chǎng)考試內(nèi)容改為作論兩篇。時(shí)務(wù)策一篇,其論第一篇題目選自《論語(yǔ)》《孟子》,第二篇題目選自《孫子》《吳子》《司馬法》。嘉慶年間清政府對(duì)武舉內(nèi)場(chǎng)考試內(nèi)容又進(jìn)行了調(diào)整,內(nèi)場(chǎng)策論改為了默寫武經(jīng),相較于順治康熙年間考試內(nèi)容簡(jiǎn)單了許多,主要是因?yàn)槎鄶?shù)應(yīng)試者文化基礎(chǔ)較差,往往在外場(chǎng)考試中成績(jī)優(yōu)異者到了內(nèi)場(chǎng)考試成績(jī)卻偏低,所以清政府不得不進(jìn)行調(diào)整。
( 三) 武會(huì)試
武會(huì)試是武科最高層次的考試。在辰、戌、丑、未年舉行。武會(huì)試對(duì)應(yīng)試者資格要求較為寬松,規(guī)定蒙古武舉人、文舉人、駐防、在京蒙古旗人都可報(bào)名參加應(yīng)試,主要目的是為了選拔出真正優(yōu)秀的武備人才。
八旗蒙古武會(huì)試外場(chǎng)考試內(nèi)容主要是馬射、步射、開硬弓,與武鄉(xiāng)試內(nèi)容不同的是取消了舞大刀、掇石,取消時(shí)間為雍正元年。弓箭射習(xí)是武會(huì)試外場(chǎng)考試的重要內(nèi)容,因此對(duì)其考試方法要求極為嚴(yán)格。乾隆二年( 1737 年) 議準(zhǔn),馬射、步射,各少中一個(gè)箭者,不準(zhǔn)入內(nèi)場(chǎng)。若馬射少中一個(gè)箭,步射合式: 步射少中一個(gè)箭,馬射合式者,再試技勇。若技勇一等者,亦準(zhǔn)其合式,缺一者不準(zhǔn)。若有勇力過(guò)人,技藝出類,準(zhǔn)一同選入好字號(hào)。[9]( 卷七百十八)有關(guān)八旗武會(huì)試內(nèi)場(chǎng)考試內(nèi)容基本與鄉(xiāng)試相同,在這里就不詳加贅述。
三、翻譯科
翻譯科主要包括滿洲翻譯與蒙古翻譯,滿洲翻譯應(yīng)試方法是用滿文翻譯漢文或者用滿文作論,蒙古翻譯應(yīng)試方法是用蒙文翻譯滿文,但不翻譯漢文,由于應(yīng)試的方法不同,所以中式者錄取名額也有差別。清末入關(guān)前,于蒙古文字外,創(chuàng)制清書,天聰八年曾以此試習(xí)清書與蒙古書者,順治以后仿傳統(tǒng)三級(jí)考試,有童試、鄉(xiāng)試、會(huì)試。
( 一) 滿文翻譯科
滿文翻譯科在雍正元年開始。清代滿語(yǔ)是八旗人的一門必修語(yǔ)言,特別是清前期,所以蒙古旗人參加滿文翻譯考試是十分自然的。凡京旗、直隸、奉天、各省駐防蒙古翻譯生員、文生員、貢生、監(jiān)生、蔭生、中書、七八品筆帖式、小京官等能翻譯漢文者均可報(bào)名參加翻譯鄉(xiāng)試,先經(jīng)試步、騎射,合格者由順天府學(xué)錄科后始準(zhǔn)應(yīng)試。由順天府承辦,只試一場(chǎng)。道光年間,駐防旗人允許在各省應(yīng)試。至于滿文翻譯鄉(xiāng)試題目,初為《四書》滿文論一篇,翻譯漢文《四書》題一道。乾隆時(shí)改為《性理》
《小學(xué)》內(nèi)出題。對(duì)于鄉(xiāng)試中額人數(shù),“初無(wú)定額,乾隆十三年定為三十三名,道光八年改為七八名,道光十七年僅為四五名。”[8]在翻譯會(huì)試方面規(guī)定,凡蒙古翻譯舉人、文舉人及舉人出身的筆帖式、小京官經(jīng)各旗都統(tǒng)、兵部考試步、騎射合格者均準(zhǔn)會(huì)試。
( 二) 蒙文翻譯科
蒙文翻譯科設(shè)于雍正九年( 1731 年) ,它不同于滿文翻譯,一是只限蒙古旗人參加,滿洲人不能參加。二是以蒙文翻譯滿文而不是翻譯漢文。蒙文翻譯科童生試試題初于滿文《日講四書》內(nèi)出題,乾隆元年改于滿文《性理》《小學(xué)》內(nèi)出題翻譯。錄取生員,乾隆初年錄取比例大體上十取一。乾隆十三年( 1648 年) 定額為九名。道光以后逐漸減少。鄉(xiāng)試試題,乾隆以前出題二道。一道出自《日講四書》中,另一道出自滿文奏疏中,均以蒙文譯出。乾隆以后題出自滿文《性理》《小學(xué)》中。蒙文鄉(xiāng)試原無(wú)中額,乾隆十三年( 1648 年) 前取中舉人或五六名、或八九名不等。乾隆十三年( 1648 年) 定額為六名。
會(huì)試題目較為簡(jiǎn)略,只有翻譯,不試文論。首題選自滿文《四書》《性理》,次題出自滿文奏疏中,均譯蒙文。蒙文會(huì)試中額,乾隆初定為二名,后改為臨時(shí)欽定。[8]八旗蒙古科舉制度作為清代科舉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曾對(duì)八旗蒙古人產(chǎn)生過(guò)重要影響。在八旗蒙古科舉制度的影響下,一些蒙古人開始主動(dòng)學(xué)習(xí),大大提高了八旗蒙古人的文化水平,同時(shí)也造就了大批蒙古族學(xué)者,他們通過(guò)著書立說(shuō),大大豐富了蒙古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另外,八旗蒙古科舉制度為蒙古族人民進(jìn)入清代政治生活開辟了一條道路,使蒙古族人民也能廣泛地參與到清代政治決策中。最后,八旗蒙古科舉制度也推動(dòng)了蒙古族與滿族和漢族的文化交流,使更多地蒙古族人民了解到漢族和滿族的文化,促進(jìn)了各民族間的友好往來(lái)。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jiàn)問(wèn)題 >
SCI常見(jiàn)問(wèn)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