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代文學批評可大致劃分為兩種類型。其一是學院批評,自上世紀90年代發(fā)展至今,經(jīng)歷了由興盛到爭議的過程,其特征是理論性、客觀性、價值中立。其二是學院批評以外的文學批評,其內(nèi)部分支眾多、種類復雜多變。這類文學批評的共同特征是個性化、主觀性、價值判斷,因此可統(tǒng)稱為價值批評。這兩類批評的根本區(qū)別在于它們是兩套話語系統(tǒng),即批評對原文(作品)闡釋的兩種方式,也是作為所指的批評與作為能指的原文之間的兩種意指關(guān)系。兩套話語的分化形成既受學院的封閉式環(huán)境影響,也受批評家對創(chuàng)作實踐話語權(quán)的影響。
關(guān)鍵詞:學院批評;價值批評;話語
中圖分類號:1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29(2019)0l一0053—07 doi:10.19742/j.cnki.50一1164/c.190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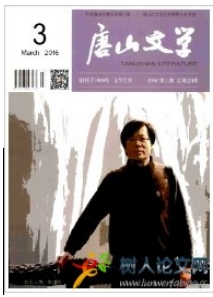
《唐山文學》(雙月刊)1950年創(chuàng)刊,屬于文學期刊。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和“雙百方針”,理論聯(lián)系實際,開展教育科學研究和學科基礎(chǔ)理論研究,交流科技成果,促進學院教學、科研工作的發(fā)展,為教育改革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做出貢獻。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涉及作品廣泛、批評文本豐富、批評家眾多,可謂洋洋大觀。從上世紀80年代的印象批評,到90年代的學院批評,再到2000年以后的網(wǎng)絡(luò)批評,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經(jīng)歷了一個復雜的發(fā)展過程。對于當今的文學批評現(xiàn)象,研究者眾說紛紜,有二分法、三分法等分類,有學院批評、作家批評、專業(yè)批評、媒體批評、印象派批評等概括。因此,面對著紛繁復雜的文學批評現(xiàn)象和各執(zhí)一詞的理論觀點,有必要對當代文學批評進行細致梳理、重新分類和深入探討。
一、學院批評
如果說當今中國文學批評存在著主流流派,那當是學院批評。這不僅僅是學院自己的看法,也是官方和媒體都承認的觀點。這一情況從魯迅文學獎和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的評選中可見一斑。魯迅文學獎是由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辦,最具影響力的的文學類獎項之一,代表著官方和主流的聲音。魯迅文學獎設(shè)立包括短篇小說、中篇小說、詩歌等在內(nèi)的7個獎項,其中包含“文學理論評論獎”。可以說,這一獎項代表著官方層面對于文學批評的選拔和認定標準。從1997年第一屆評獎開始,可以看到獲獎的理論評論家除雷達、李敬澤等個別隸屬作協(xié)和雜志的評論家外,多數(shù)是學院派的成員,樊駿、錢中文、朱向前、陳曉明、南帆等知名教授、研究員都在獲獎名單中。另一個有力的證明是《南方都市報》主辦的“華語文學傳媒大獎”,號稱年度獎金含金量最高的純文學大獎,這可以被視作媒體的聲音。“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從2003年第一屆至今已歷經(jīng)16屆,每屆設(shè)立年度杰出成就獎、年度小說家、年度詩人等6個獎項,其中包
括“年度文學評論家”獎項。每個獎項每年度只頒發(fā)給一位獲獎者。“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所選出的“年度文學評論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評論家在媒體眼中的影響力。2003年第一屆的“年度文學評論家”頒給了北京大學的學院派評論家陳曉明,此后王堯、張新穎、陳超、郜元寶、張清華、孟繁華等評論家紛紛獲獎。除2005年的李敬澤和2011年的李靜外,其余14屆的“年度文學評論家”都頒給了學院派評論家。
可以說,今天的學院批評是排斥主觀性的,顯露明顯主觀判斷的批評會被認為“不專業(yè)”。在干預創(chuàng)作現(xiàn)實和理論批評這一點上,今天的學院批評對于后者的成果是非常豐富的,但是對于前者卻悄無聲息。既然學院批評已有了“評論為理論服務”的傾向,那么學者們致力于孜孜不倦地生產(chǎn)新的理論、新的概念、新的批評方法也成為必然之途,因此在理論批評領(lǐng)域往往熱火朝天,學者們不停地添磚加瓦。但另一方面,在干預創(chuàng)作現(xiàn)實領(lǐng)域,學院批評家們似乎興趣寥寥;他們往往只是討論作家的作品,卻不對現(xiàn)實創(chuàng)作提出建議;而作家也似乎不再將這些批評放在心上,有些作家甚至直言“看不懂”【3 J。學院批評家雖然討論的是作家及其作品,但二者卻并行不悖,互不干涉。
二、價值批評——另一類批評
無論采取哪種劃分方式,我們都可以看出,大家對于“學院批評”達成了共識。這當然有學院批評命名明確、源流清晰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學院批評同其他批評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而其他批評之間往往相互混淆、相互牽涉。如雷達所說的“專業(yè)批評”,他原意是指以作協(xié)為代表的專業(yè)批評家,同高校里兼具學者與批評家二職的學院批評家予以區(qū)分;但從當下中國的實際情況看,這些專業(yè)批評家也逐漸在向?qū)W院和媒體分化。再如“媒體批評”和“網(wǎng)絡(luò)批評”,在當今媒體已高度網(wǎng)絡(luò)化的環(huán)境下,媒體和網(wǎng)絡(luò)往往是同時出現(xiàn)的。雖然媒體評論同真正的自發(fā)性讀者批評確實存在區(qū)別,但隨著通過網(wǎng)絡(luò)媒體發(fā)布的民間高水平的匿名批評和讀者批評的逐漸增加,媒體批評和網(wǎng)絡(luò)批評的界限也在逐漸模糊。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原有的文學評論分類體系作出調(diào)整。
上文我們已經(jīng)總結(jié)過學院批評的特征,如理論性、客觀性、規(guī)范性、價值中立,這些確實是學院批評的優(yōu)勢所在,但也正是學院批評被詬病的地方。其他批評被一部分批評家所提倡,也是因為它彌補了學院批評的不足。比如趙勇批判學院批評由于過于專業(yè)化、制度化而導致的缺乏思想的個性和深度;杜國景批判學院批評缺乏對于現(xiàn)實批判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丁帆批判學院批評缺乏價值立場等等。這些正是另一些批評家所所倡導的特質(zhì):如姚曉雷倡導批評應包含自我經(jīng)驗¨6J憾2—83;賀仲名、張學昕等人強調(diào)的心靈、主體性和情感¨6]186—97;何言宏強調(diào)對現(xiàn)實的“介入的批評”[16]209等等。由此我們便可總結(jié)出另一類批評的特征,即個性化的、主觀的、感悟的、價值判斷的。根據(jù)以上特征,對上述批評做一個整體上的概括,可將其概括為“價值批評”。
但問題還不止于此。從邏輯上看,學院批評同價值批評應形成相反或互補關(guān)系,但實際二者之間并不相通。前文提到吳亮、羅四鎢等批評家批評學院批評使用學術(shù)“黑話”,讓人難以理解:“整個對話的話語方式更可以說是學術(shù)繞口令的典范,其文字之晦澀、拗口,幾乎令人無法卒讀。”∞1而學院批評家對價值批評的語言也是頗有微詞,如批判印象主義批評:“如果收集一批印象主義批評的論文,提煉出批評家反復使用的幾個有限的關(guān)鍵詞,那么,人們就可以察覺到,這種批評的視野多么狹小,闡釋的內(nèi)涵多么單調(diào),批評家的思想多么乏味。”[171兩類批評家彼此之間不但不認同,而且不能理解彼此的批評語言,否認對方的表述方式。由此可見,學院批評同價值批評使用的是兩套話語。
三、兩套話語
福柯通過對考古學、臨床醫(yī)學等學科話語構(gòu)成的分析,探討了系統(tǒng)話語理論的建構(gòu)方式。在他看來,話語同語言一樣都是由符號序列構(gòu)成,以語言為基礎(chǔ),但不止是語言,它超出語言。最初的話語派生于索緒爾對語言的種種二元對立的劃分,但又超越于此。羅蘭·巴特說:“話語有自己的單位,自己的語法;它超越句子,然而又特別由句子所構(gòu)成;話語就本質(zhì)而言將成為第二種形式的語言學的研究客體。”[18]89因此,學院批評話語和價值批評話語也可以作為語言學的研究客體。
在學院批評話語體系里,在其理論的作用下,作為能指的原文和作為所指的學院批評之間產(chǎn)生了張力,同樣的能指因不同理論的關(guān)聯(lián)而最終生產(chǎn)出新的知識。在作為意指系統(tǒng)的學院批評內(nèi)部,其形式具有重大意義:學院批評形式中大量的術(shù)語、概念對他人形成了拒斥,將“外行”排除在話語系統(tǒng)之外。進入話語系統(tǒng)的唯一手段就是理論。只有掌握了關(guān)鍵性的理論,才能進入這個話語系統(tǒng)。另一方面,在價值批評話語體系里,在經(jīng)驗的作用下,作為能指的原文和作為所指的價值批評之間產(chǎn)生了張力,這種個人經(jīng)驗(情感、感悟、心靈、閱讀、審美)幫助對能指的價值判斷的形成。由于經(jīng)驗主要用于判斷作為能指的原文,作為所指的批評內(nèi)部的能指形式就坍縮了,為的是集中力量進行價值判斷,因此就形成了價值批評往往所指大于能指,能指相對匱乏的現(xiàn)象。這是從符號學層面對兩套批評話語予以分析。
福柯的“系譜學”理論能夠?qū)W院批評的形成與迅速發(fā)展提供合理解釋。在《知識考古學》一書中,福柯談到知識型話語的特點:“認識閾(即知識型)是指能夠在既定的時期把產(chǎn)生認識論形態(tài)、產(chǎn)生科學、也許還有形式化系統(tǒng)的話語實踐聯(lián)系起來的關(guān)系的整體;是指在每一個話語形式中,向認識論化、科學性、形式化的過渡所處位置和進行這些過渡所依據(jù)的方式,指這些能夠吻合、能夠相互從屬或者在時間中拉開距離的界限的分配;指能夠存在于屬于鄰近的但卻不同的話語實踐的認識論形態(tài)或者科學之間的雙邊關(guān)聯(lián)。”[21]24“249福柯認為,現(xiàn)代科學依賴于包括實驗室、大學制度等在內(nèi)的體制,它為生成新的知識領(lǐng)域打開空間。在知識生成的過程中,科學構(gòu)建成一個完整的思維和話語體系,同時產(chǎn)生了權(quán)力關(guān)系。如此,知識體系就成為了集體向個體實施權(quán)力的工具和媒介,而個體在使用知識和產(chǎn)生知識的同時也加固了這種權(quán)力體系。當代學院批評話語的形成同福柯所描述的“知識型”話語的產(chǎn)生非常相似。
從現(xiàn)實層面而言,是什么觸發(fā)了這一權(quán)力批評話語的形成呢?如果我們把目光收回到20世紀80年代以前,會發(fā)現(xiàn)當時的評論家同作家、同政治的關(guān)系與今天的差異很大。從“左翼”文學到“文革”文學,評論家對于作家具有相當程度的話語權(quán)。茅盾、周揚、馮雪峰等大批評家的批評話語在當時極具分量,大多數(shù)作家確實會按照批評家的意見修改作品。茅盾在寫作《子夜》時,就按照馮雪峰的建議多次進行修改,楊沫的《青春之歌》、姚雪垠的《李白成》等作品的創(chuàng)作也參考了批評家的意見。同樣,批評家也以指導創(chuàng)作實踐為己任。到了十七年時期,評論家的權(quán)力達到了一個頂峰。很多政治運動正是以文學批評為發(fā)令槍,如對電影《武訓傳》和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評,雖然政治因素是幕后推手,但確是以文學批評的形式置于臺前。新時期開始,學院批評并未在初期便形成風潮。批評家在建構(gòu)新的話語形式的時候,進行了諸多嘗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20世紀80年代的印象批評。印象批評不僅提倡主體性,同時也寬泛地觸及了政治和文化方面。然而,一方面由于對于“文革”時期強政治性的反撥,另一方面由于對批評家強話語權(quán)傳統(tǒng)的反撥,印象批評僅憑強調(diào)個性主體和經(jīng)驗感悟的話語很難建構(gòu)成一個系統(tǒng)。此時學院批評異軍突起,憑借其學術(shù)性、客觀性、規(guī)范性迅速確立了陣地,逐漸建構(gòu)起了學院批評話語,批評家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如今學院批評家同作家各行其是,與20世紀80年代以前那種緊密相連的關(guān)系大不相同。學院批評家也不再為作家提出寫作建議,而是專心生產(chǎn)知識;作家也不再虛心接受批評家的批評,而是自由進行創(chuàng)作;他們都各自形成了新的話語。
作為同學院批評相互對立、相互補充的價值批評,其實也并未因為政治批評或是印象批評勢力的消退而完全消失。今天的部分作家批評、協(xié)會批評、媒體批評以及迅速增長的網(wǎng)絡(luò)批評,都呈現(xiàn)出價值批評的傾向。它們可以使用多種方法,如印象批評、實用批評、道德批評或政治批評,但最終都以價值為導向。只是由于價值觀念和價值形成的復雜性,價值批評呈現(xiàn)出眾聲喧嘩的態(tài)勢;但相對學院批評而言,它們?nèi)詫偻活惻u話語。
總體來看,學院批評由于其特殊的理論話語、專業(yè)的學科性等因素形成了穩(wěn)定的批評話語系統(tǒng),占據(jù)主流聲音。另一方面,由于價值批評中價值觀念和價值判斷的多樣性、個人經(jīng)驗的個性化特征等因素,價值批評很難形成如學院批評般系統(tǒng)規(guī)范穩(wěn)定的話語,導致其聲音分散零落。但這并不意味著價值批評沒有立足之地,相反,學院批評在感性層面的缺失,正是由價值批評來彌補。價值批評在經(jīng)驗、感受和主觀領(lǐng)域所進行的討論,將文學批評從文學研究層面拓展至社會生活乃至整個人類層面。可以說,學院批評與價值批評從不同角度覆蓋文學批評,二者都是各自批評話語發(fā)展和作家、批評家、讀者不同需求的共同產(chǎn)物。
[參 考 文 獻]
[1]趙勇.學院批評的歷史問題與現(xiàn)實困境[J].文藝研究,2008(2).
[2]王寧.論學院派批評[J].上海文學,1990(2).
[3]閻連科.作家與批評家[J].當代作家評論,2009(1).
[4]南帆,等.底層經(jīng)驗的文學表述如何可能[J].上海文學,2005(11).
[5]吳亮.底層手稿[J].上海文學,2006(1).
[6]羅四鎢.學術(shù)文章請勿“黑話”連篇[N].文學報,2005一12—22.
[7]南帆.底層問題、學院及其他[J].天涯,2006(2).
[8]高建平.論學院批評的價值和存在問題[J].中國文學批評,2015(1).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