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笛卡爾在尋求知識(shí)的阿基米德支點(diǎn)時(shí),提出了心靈比身體能更好地被感知的觀點(diǎn),但僅限于對(duì)自心的認(rèn)知,沒有拓展到他心上,這就可能提出一個(gè)懷疑主義的他心問題———我如何判斷他人是不是一個(gè)沒有心靈的自動(dòng)機(jī)?當(dāng)然這一問 題的產(chǎn)生與笛卡爾的哲學(xué)密不可分,心身二元論為他心問題的解決設(shè)定了本體論障礙,心靈與身體之間沒有邏輯的關(guān)聯(lián),使得直接認(rèn)識(shí)他心沒有可能。利用邏輯來證明他心不僅未能圓滿地解決問題,反而違反我們的生活常識(shí)。笛卡爾的確向人們提出了難題,但 也不是無解,解決之道在于破除心身二元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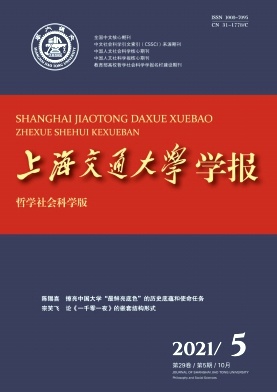
沈?qū)W君, 上海交通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 發(fā)表時(shí)間:2021-10-22
關(guān)鍵詞:笛卡爾;他心問題;心身二元論
笛卡爾對(duì)近現(xiàn)代哲學(xué)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其中包括對(duì)心靈哲學(xué)的影響。作為心靈哲學(xué)中的核心討論主題,他心問題的提出及其研究范式更是與笛卡爾密不可分。盡管笛卡爾因建立起一個(gè)可以引起他心問題的哲學(xué)框架而聞名,但他本人并沒有系統(tǒng)論述這一問題,學(xué)界亦少有人關(guān)注他在這一方面的著述。他是如何提出這一問題的,又是怎樣來解答的,對(duì)后世有何影響?這就需要我們作進(jìn)一步考察。
一、他心問題的提出
笛卡爾的哲學(xué)探索是由對(duì)他那個(gè)時(shí)代哲學(xué)的強(qiáng)烈不滿所推動(dòng)的。厭倦了陳舊的亞里士多德思想和經(jīng)院哲學(xué)教條,笛卡爾開始全新的哲學(xué)探索。他的工作圍繞著三個(gè)目標(biāo)展開:首先是發(fā)現(xiàn)確定性,為知識(shí)大廈奠定牢固基礎(chǔ);其次是實(shí)現(xiàn)普遍科學(xué)的夢(mèng)想;再次是調(diào)和當(dāng)時(shí)流行的機(jī)械論世界觀與人類自由的觀點(diǎn)。摧毀舊體系的武器是普遍的懷疑。在《探索真理》中,他寫道, “因此,我不僅會(huì)對(duì)你是否在世界上,是否有地球或太陽;而且對(duì)于我是否有眼睛、耳朵、身體,甚至我是否在對(duì)你說話,你是否在對(duì)我說話都不確定。簡 而 言 之,我 會(huì) 懷 疑 一 切”。① 笛 卡 爾 認(rèn)為,很多虛假的信念被人們從小就認(rèn)為是真的,但它們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礎(chǔ)之上。因此,必須運(yùn)用懷疑的方法去除虛假的知識(shí),凡 是 不能通過 懷 疑推 敲的,都要排除在知識(shí)之外,包 括 關(guān) 于 世界、身體和數(shù)學(xué)的觀念。在第二沉思中,通過普遍的懷疑,最后只剩下一種可能性:思想能否懷疑自身?笛卡爾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他不確定其他任何事情,他至少確定他在懷疑。當(dāng)他試圖懷疑“我在懷疑”這個(gè)命題時(shí),他實(shí)際上在證明它!這就是他要尋找的阿基米德支點(diǎn)。他把他的發(fā)現(xiàn)表述為“我思故我在”。當(dāng)?shù)芽栒f“我存在”,他的意思是他知道他的心靈存在。由此他得出結(jié)論,心靈比身體更實(shí)在,能更好地被感知。
但笛卡爾很快承認(rèn)這一結(jié)論可能看起來違反我們的直覺:在 日常 生 活 中,身體是看得 見、摸得著的,似乎能比心靈更好地被感知。為了證明事情不是它們看上去的那樣,笛卡爾要求我們考慮一下蠟的情況。
在正常情況下,蠟具有自己獨(dú)特的外部特征,如顏色、形狀、大小等。當(dāng)人們將一塊蠟放到火的旁邊后,蠟的這些特征發(fā)生了變化。很顯然,蠟融化了,不再保持先前的特征。盡管發(fā)生了這些變化,但我們會(huì)說在我們面前的還是同一塊蠟。笛卡爾問道,被火烤后,關(guān)于蠟的感官信息發(fā)生了變化,我們是如何得出“這是蠟”這個(gè)結(jié)論的?為了回答這個(gè)問題,笛卡爾在感官、想象力與理解之間做出了區(qū)分。根據(jù)笛卡爾所說,感官或想象力僅提供事物的最直接的印象,它無法解釋蠟可能發(fā)生的變化。蠟在經(jīng)歷變化之后仍然保持為蠟是“只憑心靈就能感知”的;這是我們理解或判斷的結(jié)果。②
笛卡爾指出,我們對(duì)此進(jìn)行反思,在這一點(diǎn)上我們很容易陷入錯(cuò)誤。他認(rèn)為,錯(cuò)誤的思維方式被日常語言所誘導(dǎo)。他寫道:“我們幾乎被日常的交談方式所欺騙。我們說我們看到了蠟本身,如果它在我們面前,不是根據(jù)顏色或形狀我們判斷它在那里;這可能導(dǎo)致我毫不費(fèi)力地總結(jié)一下關(guān)于蠟的知識(shí)來自眼睛所看到的,而不只是來自心靈。但是如果我從窗戶往外看,看見有人穿過廣場,就像我剛剛碰巧做的,我通常會(huì)說我看到人自身,就像我說看到蠟一樣。但是我看到的不是帽子和大衣可以掩蓋的自動(dòng)機(jī)?我斷定他們是人。”③
在這段文字中,笛卡爾表達(dá)了豐富的內(nèi)容。首先,笛卡爾談到在日常生活中,語言具有欺騙性。但從行文來看,這種欺騙性還是指通過感官所獲得的知識(shí)具有欺騙性。為此,笛卡爾比較了兩種情況:從窗戶看街上的人與蠟放到火旁邊所發(fā)生的變化。當(dāng)我們從窗戶看下去,真正看到的只是帽子和大衣,但我們通常說我們看到了人。笛卡爾以此來揭示感官視覺提供不可靠的信息。關(guān)鍵的是,盡管我們所看到的是帽子和大衣,但我們判斷這是一個(gè)人。類似地,盡管蠟的外在形式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我們判斷看到的是同一塊蠟。
蠟的外形變化可能導(dǎo)致對(duì)它產(chǎn)生錯(cuò)誤的判斷。類 似 地,衣服讓我們看不清人體的真實(shí)本質(zhì)。笛卡爾以此說明感官語言的使用,明顯具有欺騙性。④
其次,笛卡爾在這一段落提出了標(biāo)準(zhǔn)的他心問題表述。“如果我從窗戶往外看,看見有人穿過廣場……我通常會(huì)說我看到人自身……但是我看到的不是帽子和大衣可以掩蓋的自動(dòng)機(jī)?” 簡單地說,我如何知道我所看到的只是一個(gè)沒有心靈、被帽子衣服掩蓋、有著人的肉體形式的自動(dòng)機(jī)?這段話稍微變通一下就是,我如何 知 道他 人 有 沒 有 心 靈?這就是典型的他心問題的表述。笛卡爾之所以有這樣一種表述,跟他堅(jiān)持心身二元論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在笛卡爾看來,心靈與身體是兩種不同的實(shí)體,具有不同的屬性,并且兩者沒有邏輯的關(guān)聯(lián)。因此就可以合理地懷疑他人是一個(gè)沒有心靈的自動(dòng)機(jī)。
笛卡爾在這段話想說的是語言如何誤導(dǎo)了我們,他提供了兩個(gè)例子。第一個(gè)是關(guān)于蠟的情況,我們的理性能夠克服語言所帶來的迷惑;第二個(gè)例子是關(guān)于人的判斷,他告訴我們并不能根據(jù)服裝來判斷在我們面前的是不是人。笛卡爾的主要目的是討論人的情況,以蠟來類比,我們確實(shí)發(fā)現(xiàn),笛卡爾是在小心地選擇他的例子。讓我們進(jìn)一步分析,看看將蠟和人進(jìn)行類比會(huì)發(fā)生什么。
如果我們沿著笛卡爾的思路進(jìn)一步假設(shè),就會(huì)發(fā)現(xiàn)一些有趣的事情:當(dāng)我們無法從外形上區(qū)分“他”是人還是自動(dòng)機(jī)時(shí),如果讓他脫掉衣服,是否可以判斷呢?應(yīng)該說,還是難以判斷,因?yàn)槲覀兛梢约僭O(shè)人們的技術(shù)水平足夠高,做出的自動(dòng)機(jī)可以以假亂真,無法從外形上分辨。因此,問題仍然存在:所看到的“他”到底有沒有心靈?此外,我們還有進(jìn)一步的疑問,笛卡爾為什么把沒有心靈的人說成是自動(dòng)機(jī)而不是穿著衣服的直立行走的動(dòng)物?笛卡爾自己又是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的?我們需要進(jìn)一步考察。
二、人還是自動(dòng)機(jī)?
在第二沉思中笛卡爾將人與自動(dòng)機(jī)進(jìn)行了對(duì)比,認(rèn)為我們從窗戶上看到的這個(gè)形象是人,而不是自動(dòng)機(jī)。奇怪的是笛卡爾選擇了這種對(duì)比。他為什么不考慮在帽子和大衣下可能是直立的動(dòng)物?
笛卡爾以他的方式作對(duì)比與他接受以下兩個(gè)觀點(diǎn)有關(guān):(1)人與所有其他生物之間存在種類上的區(qū)別;(2)生物與單純的機(jī)械之間沒有區(qū)別。由于持有了這兩個(gè)觀點(diǎn),笛卡爾得出結(jié)論,所有的動(dòng)物都是機(jī)器。一旦了解了這一點(diǎn),我們就可以看到,當(dāng)?shù)芽枌⑷伺c自動(dòng)機(jī)進(jìn)行對(duì)比時(shí),他實(shí)際上將人與所有的動(dòng)物作了區(qū)分。
在寫給友人的一封信中,笛卡爾說,“因此,原 始人 可能 沒 有區(qū) 分 兩種 原則:一方面 是營養(yǎng)和成長的原則,在此我們無須思想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動(dòng)作,這一點(diǎn)上我們與野獸是相同的,另一方面,是我們的思維原則。因此,他使用了單個(gè)術(shù)語‘靈魂’于兩者;當(dāng)他隨后注意到思想與營養(yǎng)不同,我要說的是‘靈魂’這一詞語,當(dāng)它用來指稱這兩種原則時(shí),就混淆了……因?yàn)槲艺J(rèn)為心靈不是靈魂的部分,而是整體上的思維靈魂部分”。⑤
笛卡爾在這里清楚地表明,人與低等動(dòng)物之間分享一些功能,例如生長和營養(yǎng),另外一些功能是人類特有的,如思維。他想限制“心靈”一詞的使用范 圍,用它 來 特指 人的思維功 能:心靈是“整體上的思維靈魂”。各種低等動(dòng)物沒有心靈,沒有靈魂。盡管笛卡爾認(rèn)為它們沒有心靈或靈魂,但認(rèn)為這些低等動(dòng)物有活力。⑥
一旦靈魂與身體分離,單純的身體就被視為機(jī)器。這是笛卡爾關(guān)于身體的核心觀點(diǎn)———身體是脫離了心靈的被動(dòng)質(zhì)料。笛卡爾在《論人》中寫道:“我希望您考慮……我賦予這臺(tái)機(jī)器的所有功能 ———如食物的消化,心臟和動(dòng)脈 的跳動(dòng),四 肢 的營 養(yǎng) 和 成 長,呼 吸,清醒 和睡 眠,外部感覺器官對(duì)光、聲音、氣味、味道、熱量等質(zhì)量的接收……我希望您考慮這些功能,它們僅僅遵循機(jī)器器官的排列,就像時(shí)鐘或其他 機(jī) 芯一 樣,每一點(diǎn) 都像 自 動(dòng)機(jī) 遵 循其配 重和齒輪的 安排。”⑦ 笛卡爾在這里清楚地表明機(jī)器與活的生物屬于同一類事物。這種觀點(diǎn)與早期哲學(xué)家的觀點(diǎn)不同,他們主張生物與機(jī)器之間存在質(zhì)的區(qū)別,而人類與動(dòng)物之間則存在聯(lián)系。
根據(jù)笛卡爾的《論人》文本,人們可以這樣來定義自動(dòng)機(jī):自動(dòng) 機(jī) 是 具有 功能的 身體,無論它如何復(fù)雜,其功能從零件的排列可以看出來。按照這個(gè)定義,所有的動(dòng)物都是自動(dòng)機(jī)。人類 與動(dòng)物的區(qū)別是,前者擁有心靈而后者沒有。由于沒有心靈,動(dòng)物被歸類為自動(dòng)機(jī),屬于機(jī)器之列。當(dāng)?shù)芽栐诘诙了贾袑⑷伺c自動(dòng)機(jī)對(duì)比時(shí),他實(shí)際上是把一個(gè)心靈、身體結(jié)合在一起的人與一個(gè)沒有心靈的身體進(jìn)行對(duì)比。按照笛卡爾的觀點(diǎn),即便是能直立行走的狗和猴子,也屬于自動(dòng)機(jī)之列。通過這種方式,笛卡爾把人類和其他萬物區(qū)別開來。
三、只有人類才有心靈
笛卡爾相信所有人都有心靈。他也相信在所有肉體存在中,只有人類有心靈。所有的動(dòng)物以及自動(dòng)機(jī)沒有心靈。這樣一種結(jié)論是從以下幾個(gè)方面來進(jìn)行論證的:
首先是人類的獨(dú)特性,與其他動(dòng)物的不同之處在于人類擁有心靈。然而在笛卡爾的時(shí)代,這一主張?jiān)獾搅伺険簟?duì)笛卡爾的這一觀點(diǎn),即只有人類表現(xiàn)出特別復(fù)雜的行為,由此判斷人類擁有心靈,有哲學(xué)家提出質(zhì)疑。實(shí)際上笛卡爾從未否認(rèn)一些動(dòng)物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展現(xiàn)敏捷的行為。當(dāng)然,同樣可以觀察到動(dòng)物在某些情況下沒有敏捷性。笛卡爾認(rèn)為,動(dòng)作的敏捷性和準(zhǔn)確性并不是判斷的標(biāo)準(zhǔn)。他舉了時(shí)鐘的例子,“是自然根據(jù)它們器官的習(xí)性在其中起作用。只由齒輪和彈簧組成的時(shí)鐘,以同樣的方式,記錄小時(shí)和測量時(shí)間,比我們所有的有智慧的人要更準(zhǔn)確”。⑧ 基于這些理由,笛卡爾 認(rèn) 為 唯 有人類才 有 心 靈,“如 果 他 們 像 我們一 樣思考,[非人類動(dòng)物]像我們這樣擁有不朽的靈魂。這是不可能的,因?yàn)闆]有理由相信某些動(dòng)物卻不相信所有動(dòng)物,還有很多東西像牡蠣和海綿等太不完美而不可信”。⑨
從上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笛卡爾是從神學(xué)和道德的角度來否定所有動(dòng)物具有心靈的。他在《方法論》中的敘述進(jìn)一步 強(qiáng) 化 了這 一 點(diǎn):“對(duì)于那 些 否 認(rèn) 上帝 的 人 來 說,在犯了錯(cuò)誤之后…… 除了想象野獸的靈魂與我們的具有相同的本性,沒有什么可以引導(dǎo)虛弱的心靈沿美德的直路更進(jìn)一步,因此在今世,我們沒有什么可害怕或希望的,就像蒼蠅和螞蟻一樣。”瑏瑠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笛卡爾公開反對(duì)動(dòng)物具有永生性:“跟具有不朽靈魂的相比,蠕蟲、蒼蠅、毛毛蟲和其他動(dòng)物更可能像機(jī)器一樣運(yùn)動(dòng)。”瑏瑡總 之,笛 卡 爾 相 信,在 有 形 生 命 中,只有人類才被上帝賦予了心靈。
其次,笛卡爾相信上帝并沒有創(chuàng)造像人一樣的自動(dòng)機(jī)。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需要理解笛卡爾關(guān)于心靈和語言的觀點(diǎn)。在《方法論》中,笛卡爾提出了識(shí)別自動(dòng)機(jī)還是人的兩種手段。首先是真正的人能使用語言;其次是真正的人的行為表現(xiàn)出高度的敏捷性和適應(yīng)性。機(jī)器能不能說話?關(guān)于這樣一種可能性,笛卡爾持否定的態(tài)度。“無法想象這樣的機(jī)器應(yīng)該產(chǎn)生不同的單詞排列方式,以便對(duì)呈現(xiàn)的所說內(nèi)容適當(dāng)?shù)亟o出有意義的回答,就 像 最無 聊的 人 能做的 一樣。”瑏瑢在 給友人的信中,笛卡爾也多次強(qiáng)調(diào)語言對(duì)于判定心靈的重要性:“沒有人會(huì)如此不完美,以至于…… 不發(fā)明特殊的標(biāo)志來表達(dá)自己的思想。”“這樣的言語是隱藏在身體中的心靈的唯一確定標(biāo)志。所有人類都會(huì)使用它,無論他們多么愚蠢和瘋狂,即使他們可能沒有舌頭和聲音器官;但沒有動(dòng)物這樣做。”瑏瑣在《方法論》中,笛卡爾再次重申語言對(duì)人的心靈的重要性,“很明顯沒有人這么弱智和愚蠢———甚至包括瘋子———以至于他們無法將各種單詞組合在一起并形成發(fā)聲以使他們的思想得到理解”。
與此同時(shí),笛卡爾也承認(rèn)喜鵲和鸚鵡等動(dòng)物有時(shí)也能模仿人發(fā)出簡單的聲音,但它們不可能應(yīng)對(duì)無限的語境,靈活地作出有意義的回答。它們不會(huì)如我們所做的那樣說話,也就是說,它們無法表達(dá)自己正在思考的內(nèi)容。
很明顯,笛卡爾認(rèn)為,語言的使用標(biāo)志著那些有心靈的人不同于沒有心靈的人。在所有的動(dòng)物中,只有人類才有心靈。笛卡爾不相信上帝已經(jīng)制造了任何類似于人的機(jī)器。
當(dāng)?shù)芽枏乃拇皯艨吹浇值郎系男蜗髸r(shí),他斷定他們是人,而不是自動(dòng)機(jī)。我們現(xiàn)在可以知道人和自動(dòng)機(jī)之間的區(qū)別,它囊括了笛卡爾認(rèn)為的所有區(qū)別。他不需要單獨(dú)討論動(dòng)物的可能,因?yàn)樗鼈円彩菍儆谧詣?dòng)機(jī)之列。他也不需要考慮那是沒有心靈的人,因?yàn)樗幌嘈派系蹌?chuàng)造了這樣的人。
四、關(guān)于人的測試
前文已指出,笛卡爾關(guān)于從窗戶看到的人是不是自動(dòng)機(jī)的討論,可以看作關(guān)于他心問題的論述。在第二沉思中,笛卡爾將我們對(duì)蠟的感知與我們看到的人的情況作了類比。
關(guān)于我們對(duì)蠟的判斷,笛卡爾寫道,人類的心靈不僅能夠感知蠟的外在感官形式,還能將蠟與其外在形式分開。通過這種方式,人的心靈能夠把握蠟的本質(zhì)。類似地,我們也可以感知一個(gè)人。人不僅能夠感知一個(gè)人的外在形式,還可以把握一個(gè)人的真正本質(zhì)。問題是一個(gè)人的外在形式是什么?衣服和帽子并不是嚴(yán)格意義上的人的外在形式。
當(dāng)我們考慮一塊蠟時(shí),我們發(fā)現(xiàn)它是由顏色、形狀等構(gòu)成其外在形式的。當(dāng)蠟放在火旁時(shí),這些外在形式會(huì)發(fā)生變化。在考慮人的情況時(shí),人的外在形式不僅是通常所說的人的身高、膚色等,情況要更加復(fù)雜。笛卡爾所面臨的問題是: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gè)人還是自動(dòng)機(jī)?在《方法論》第五部分我們可以找到問題的答案。笛卡爾提到了存在某種復(fù)雜的自動(dòng)機(jī)的可能性。笛卡爾寫道:“在這里,我努力表明,如果有這樣的機(jī)器,它具有猴子或其他一些動(dòng)物的器官和外表形狀,沒有理性,我們應(yīng)該沒有辦法知道它們不具有與這些動(dòng)物完全相同的本質(zhì);但如果有這樣的機(jī)器與我們的身體相似并為實(shí)際目的而盡可能地模仿我們的行為,我們?nèi)匀粦?yīng)該有兩個(gè)非常確定的辨認(rèn)[測試]手段說他們不是真正的人。”瑏
第一項(xiàng)測試是關(guān)于語言的,只有真正的人才能使用語言。正 如 前 文 所 說 的,笛 卡 爾 認(rèn)為盡管可以造出能進(jìn)行口頭反應(yīng)的機(jī)器,但這樣的機(jī)器無法應(yīng)對(duì)一切環(huán)境而做出自如的 語言 反 應(yīng)。第二項(xiàng)測試是關(guān)于行為的,一個(gè)真正的人能夠應(yīng)對(duì)各 種環(huán)境,做出各種行為反應(yīng)。而一臺(tái)機(jī)器必須要有特殊部件才能適合某一特定的場合。因 此,盡管一臺(tái)機(jī)器在某些方面可能比我們?nèi)祟惐憩F(xiàn)好得多,但是總體上它達(dá)不到人類的水平,其行為缺乏適應(yīng)性和靈 活 性。
笛卡爾在《方法論》的第五部分結(jié)束時(shí)指出,心靈“不能以任何方式來源于物質(zhì),而是必須專門創(chuàng)建的”。此外,心靈必須緊密結(jié) 合 身體 而“構(gòu) 成一 個(gè) 真 正 的 人”。瑏瑦 只 有這 樣才能通過 兩個(gè)測試:一個(gè)真正的人會(huì)使用語言,并且能夠調(diào)整自己的行為以適應(yīng)環(huán)境。人通過使用語言和具備適應(yīng)能力而有別于單純的自動(dòng)機(jī)。因此,當(dāng)我們要判斷遇到的是不是一個(gè)人時(shí),我們所應(yīng)觀察的不是他的帽子和衣服,而是他的行為和他對(duì)語言的使用。在此基礎(chǔ)上,人們才能判斷在面前的是不是人。
根據(jù)笛卡爾所說,當(dāng)我們判斷在我們面前的形象是人時(shí),意味著我們判斷他是一個(gè)有心靈的人。這樣做時(shí),我們已經(jīng)將他與所有的動(dòng)物和其他自動(dòng)機(jī)區(qū)分開來了,并且我們只經(jīng)歷一步就做出了區(qū)分。笛卡爾并不認(rèn)為我們需要分兩步:先判斷我們面前的形象是一個(gè)人,然后再進(jìn)一步判斷該人有心靈。而是通過觀察外在形式———語言的使用、動(dòng)作的協(xié)調(diào)———并判斷這個(gè)形象是人。
五、笛卡爾的最終依靠
笛卡爾是以知識(shí)論的角度切入他心問題的,他需要應(yīng)對(duì)懷疑主義的質(zhì)疑。盡 管 他 找 到 了 “自我”這個(gè)重建知識(shí)體系的阿基米德支點(diǎn),但他的最終依靠是至善的上帝。
懷疑論者質(zhì)疑我們?nèi)绾文軌颢@得對(duì)存在事物的真正知識(shí)。用笛卡爾的話說,我們?nèi)绾沃雷约翰粫?huì)被惡魔欺騙,導(dǎo)致我的判斷不過是這個(gè)惡魔的產(chǎn)物,是虛假的認(rèn)知。根據(jù)笛卡爾所說,只有當(dāng)我們有能力回應(yīng)懷疑論者,我們才可以說有真正的知識(shí)。
笛卡爾認(rèn)為,他可以表明懷疑論者面對(duì)的情形不是我們的真實(shí)情形。在《哲學(xué)原 則》的 結(jié)尾,他寫道:“此外,還有一些事情是確定的,即便與自然中的事物相關(guān),我們認(rèn)為它是絕對(duì)的,而不僅僅是在道德上的(當(dāng)我們相信它是完全不可能的,除了我們判斷它是這樣的,還 出現(xiàn)了絕對(duì)確定性)。這種確定性基 于 形而上 學(xué),也就 是 說,上帝 至 善,絕 不是 欺騙者,因此他 給我們提供的區(qū)分真實(shí)與虛假的能力不會(huì)導(dǎo)致我們犯錯(cuò),只要我們正確使用它并由此明確地感知。數(shù)學(xué)展示具有這種確定性,物質(zhì)事物的知識(shí)也是如此;對(duì)于物質(zhì)事物的所有顯而易見的推理也是如此。”
笛卡爾認(rèn)為,一旦能夠證明存在著不欺騙的上帝,我們就可以從道德確定性出發(fā)到達(dá)絕對(duì)確定性。笛卡爾認(rèn)為他在第三和第六沉思中給出了這一證明。在笛卡爾看來,所有欺騙都是某種不完滿,而上帝是完滿的,由此可知上帝不可能欺騙。并且上帝給了我們區(qū)分真實(shí)與虛假的能力,使我們不會(huì)誤入歧途,前提是我們使用得當(dāng)。因此,上帝成為人類理智的堅(jiān)強(qiáng)后盾。
需要指出的是,笛卡爾的興趣在于展示知識(shí)是如何可能的,他并沒有專門論述關(guān)于他心存在的證明。然而,我們可以擴(kuò)展笛卡爾的相關(guān)論點(diǎn),從他對(duì)外部世界的了解來推斷他對(duì)他心的理解。前面提到了蠟的情況。根據(jù)笛卡爾所說,我沒有被蠟的外部形式欺騙,我判斷那是一塊蠟,我也相信那是一塊蠟。這個(gè)結(jié)論的得出是因?yàn)槲覀冏罱K有一個(gè)不欺騙的上帝。我們也可以把這種推理模式運(yùn)用到一個(gè)人的身上:我觀察了他的外在形式:他自由地使用語言,靈活地運(yùn)用行為。于是我判斷這是一個(gè)人,我相信這個(gè)人的存在。我們知道他心存在,當(dāng)然,這是上帝恩惠的結(jié)果。
笛卡爾當(dāng)然認(rèn)識(shí)到上帝也許沒有賦予他人以心靈,正如上帝可能選擇賦予動(dòng)物以心靈一樣。兩種可能性都與笛卡爾引入哲學(xué)的身心分離的觀念一致。笛卡爾也確實(shí)承認(rèn)了后者的可能性,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寫道:“但是,盡管我認(rèn)為這是確定的,即我們無法證明動(dòng)物有思想,我也認(rèn)為無法證明它們沒有思想,因?yàn)槿祟惖男撵`無法進(jìn)入它們的內(nèi)心。”瑏瑨笛卡 爾的觀點(diǎn)是,我們沒有理由認(rèn)為動(dòng)物有思想。為了知道這些動(dòng)物有沒有思想,我們的心靈需要深入到它們的內(nèi)心,但這是我們做不到的。當(dāng) 笛 卡爾 寫到 動(dòng) 物和 機(jī) 器 缺 少 思 想 時(shí),他 只 寫 了“道 德 上 的 不 可能”或出于實(shí)踐目的的不可能。瑏瑩 根據(jù)笛卡爾所說,想讓機(jī)器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像人一樣行為,這在道德上是不可能的。笛卡爾從未斷言這種事情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由于邏輯上有可能,笛卡爾就要考慮我們?nèi)绾稳ヅ袛嘟稚系男蜗笫遣皇侨恕"?/p>
在笛卡爾的哲學(xué)中,他將道德確定性提高到“絕對(duì)確定性”,只要我們有證據(jù)證明存在不欺詐的上帝。他向我們保證他心的存在,保證包括身體在內(nèi)的外部世界的存在。在笛卡爾的哲學(xué)體系中,在面對(duì)心靈與身體的邏輯鴻溝時(shí),由于有不欺騙的上帝所提供的橋梁,我們能夠跨越這一鴻溝。同樣由于上帝的存在,我們有能力跨越我的心靈與他心之間的雙重鴻溝。
六、簡 要 評(píng) 論
作為近代哲學(xué)的開創(chuàng)者,笛卡爾確立起主體哲學(xué)、意識(shí)哲學(xué)的范式,從本體論上確立起心身二元論。這種哲學(xué)框架對(duì)后世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奠定了近代西方形而上學(xué)、知識(shí)論的基礎(chǔ)。它對(duì)心靈哲學(xué)的影響尤其重大,心身關(guān)系的探討成為最基礎(chǔ)和最重要的主題。可以說,任何當(dāng)代心靈哲學(xué)家的研究都必須在這一問題上表明自己的立場。今天,隨著科學(xué)的進(jìn)步,大多數(shù)的人可能會(huì)說笛卡爾的實(shí)體二元論主張是錯(cuò)的。腦科學(xué)家就主張,我們的主觀心理經(jīng)驗(yàn)中發(fā)生的每件事情都可以用大腦過程來解釋。盡管如此,當(dāng)代心靈哲學(xué)家大衛(wèi)·查默斯(DavidChalmers)說,意識(shí)現(xiàn)象仍然是一個(gè)“困難的問題”,當(dāng)今的哲學(xué)和科學(xué)理論還不能給它提供完滿的解釋。
就他心問題而言,笛卡爾的影響首先表現(xiàn)在,心身二元論為他心問題的提出奠定了本體論基礎(chǔ)。當(dāng)心靈與身體從邏輯上被分開以后,如何在兩者之間建立起橋梁就成了巨大的難題。由于心靈與身體是邏輯分開的,擁有身體并不意味著擁有心靈。我們只看到了外在形式的身體,他心是無法進(jìn)入的,也是難以了解的,所以笛卡爾可以懷疑他人是沒有心靈的自動(dòng)機(jī)。他心問題的產(chǎn)生還跟人們對(duì)心靈的理解有關(guān)。傳統(tǒng)的觀點(diǎn)不僅把心與身從本體上分開,而且把心靈刻畫為“機(jī)器中的幽靈”,認(rèn)為它屬于私人領(lǐng)域,只對(duì)主體開放。也就是說,只有主體通過反思、內(nèi)省的方式才能獲得對(duì)自己心靈的權(quán)威認(rèn)知,人們對(duì)自心的心理內(nèi)容是透明的、即刻的并且不可錯(cuò),人們對(duì)自己的心理有某種特權(quán)和權(quán)威,但這種特權(quán)或權(quán)威并沒有拓展到他心上。他心問題就由此而產(chǎn)生。
其次,在心身二分的基礎(chǔ)上,笛卡爾開創(chuàng)了通過知識(shí)、邏輯的方式來認(rèn)識(shí)、證明他心的模式,其影響也很深遠(yuǎn)。在笛卡爾那里,追求知識(shí)成為他的首要目標(biāo),通過知識(shí)來認(rèn)識(shí)他心也是他開創(chuàng)的,可以說,笛卡爾開創(chuàng)了通過邏輯的方式來證明他心存在的先例,比如最常見的就是通過類比論證他心。但與此同時(shí),在哲學(xué)史上,有另外一批人反對(duì)這種做法,認(rèn)為它直接有違于我們的生活直覺。他們強(qiáng)調(diào)他人存在、他心存在是一種對(duì)待生活的態(tài)度,是前反思的。里德(T.Reid)就堅(jiān)持認(rèn)為,我們的同伴有心靈是第一原則。在我們開始談?wù)撊绾瘟私馑闹埃司陀行撵`了這一點(diǎn)不能被質(zhì)疑。通過類比、假設(shè)或推理的方式來證明這種智慧同伴的存在是一種根本性的誤導(dǎo),他心的存在不是類比、推理或假設(shè)的結(jié)果,而是前提。阿尼塔(A.Anita)將這樣一個(gè)包含世界與他者及主體體驗(yàn)的起點(diǎn)叫“生活立場”。根據(jù)維特根斯坦的觀點(diǎn),我們關(guān)于他心的哲學(xué)任務(wù)必須是去理解生活立場是如何可能的。戴 維森(D.Davidson)就 證明,在我們的 語言世界里,關(guān)于世界的知識(shí)、關(guān)于他心的知識(shí)以及關(guān)于自我的知識(shí)構(gòu)成了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三角,其中的任何一角都依賴于另外兩角。我們對(duì)世界的認(rèn)知不是原子式的自心運(yùn)作的結(jié)果,它還依賴心靈之間的交流互動(dòng)。現(xiàn)象主義者更是通過拋棄心與身、心與世界、主體與客體的二分而徹底地重構(gòu)了主體性。唯有堅(jiān)持主體間性,我們才能堅(jiān)持生活立場。
再次,笛卡爾從反向上啟發(fā)后人如何去尋求解決他心問題的根本路徑。當(dāng)我們說笛卡爾的框架造成了他心問題,沿著笛卡爾的路徑,人們無法走出他心的迷宮時(shí),這同時(shí)意味著解決的路徑也就出來了,那就是從源頭上消除心身二元論,強(qiáng)調(diào)心身一體,為心靈“祛魅”。這一路徑在后來的歷史中呈現(xiàn)為兩種方案,即以胡 塞 爾、梅洛·龐 蒂、加拉 格 爾(S.Gallagher)等人為 代表的現(xiàn)象學(xué)方案和以維特根斯坦為代表的語言分析方案。當(dāng)然,這是對(duì)笛卡爾問題的現(xiàn)代回應(yīng),也是后話。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