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需要一定的知識作為基礎,這種知識基礎將成為文學研究的成果的奠基因素和把握方向的因素。當文學研究去關注它的研究對象時,影響到研究的最終結果的知識基礎問題并不在自身的思考范圍之內,這樣就有必要對于文學知識本身進行一種知識論意義上的追詢。在這種追詢中,我們需要追問文學知識的類別、文學知識在回答解釋文學問題上的可靠性、文學知識在歷史的積累中知識增長的模式等重要的方面,本文最后則對文學知識的反思進行了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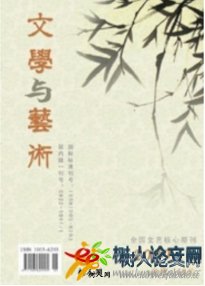
《文學與藝術》雜志是經國家新聞出版署批準,由:吉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管,延邊州文學 藝術界聯合會主辦。本刊系CNKI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數據庫等網絡數據庫全文收錄、中國核心期刊(遴選)數據庫收錄期刊。
文學研究需要知識作為基礎和支撐,而且這種知識需要具備遠比個人感受更為值得信賴的可靠性。當文學研究津津樂道于對于文學的各種發見時,往往并沒有追問這一發見的認識依據。當然,對于各個具體的研究來說,這樣的情況也是正常的,沒有必要讓所有的研究都回到對于知識的合理性的證明這一步驟,可是在研究的理論層次上就應該回答這樣的問題。在柏拉圖的對話集里面,柏拉圖假托蘇格拉底之口,表達了自己對事情的無知,可是在對話的最后,智慧的或者狡黠的蘇格拉底總是把自以為知道的對手難住,然后蘇格拉底才說出自己的看法。這樣一種說服人的方式,是一種把對手立論的支點抽空,從而達成論辯中勝利的方法。
在古希臘論辯術的背景下,蘇格拉底更多地被作為論辯的典范來看待,其實從思想的角度看,蘇格拉底其實更是一位對于認識進行積極反思,從而對知識的有效性與合理性進行改良的大師。關于文學的研究,不涉及到民生,它和每個具體的人的溫飽都沒有什么直接關系,除非文學的作者依靠此事謀生。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學知識就成為一種專家自言自語的場合,所謂的專家們主要就是考慮如何通過構建一套文學的話語來顯示其存在的價值。在權力社會中,專家們主要考慮統治者會如何處置他們的文學見解,而在市場化條件下,專家們更多地是受制于公共媒體所傳達的形象問題。只是在建構時的前提本來是針對對象的,而現在的實際狀況則是早先沒有擺到臺面的利益問題可能才是知識問題的主要癥結!
在這樣的現實情形下,就有必要對于文學的知識問題提出質詢。往近的方面說,它是我們理解文學知識言說的一個途徑,而往遠一些說,則是我們剖析文學知識合法性的一個步驟。
一、文學知識的類型追問
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科林武德曾經說,人類掌握了三種知識,分別是經驗的、先驗的和歷史的,這樣三種知識分別解決不同的問題。經驗知識的典型形式是自然科學,如物理學、化學等,它的知識采取公式化的模式,針對的是可以重復驗證的事實,如自由落體的公式,在比薩斜塔可以做,在其他的什么地方也同樣可以驗證;如果實驗的結果不同于公式的數據,就要求作出修改。先驗的知識或許也可以稱為超驗的知識,它不是在經驗驗證的基礎上獲得知識的可信度,而是在邏輯的自洽上體現出作為知識的公
信力。譬如數學領域的點、線的規定,在實際的作圖上點、線都需要占據一定的空間,也就是說,點線的顯現是必然占據了面積的,也因此才能達到可以觀看的目的,可是在數學的學科規定上,點、線是不占據物理空間的,也就沒有面積可言。這里的問題不能通過經驗來驗證,關鍵在于只要驗證具體顯示出來了的點、線都必然占據空間,都可以測量或計算出面積,問題是這樣一來每次具體的面積都不同,就影響了數學表達追求的普遍涵蓋效果。最后還有一種知識的類別就是歷史知識。歷史知識在柯林伍德看來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它是經驗性質的,對于歷史的史實的記載需要進行嚴格的甄別,另一方面歷史又不像經驗學科所研究的對象那樣具有普遍性,歷史絕不重復,就如同古希臘名言所說的人不可能兩次踏人同一條河流!
一般知識的三種類別,如果結合到文學知識這一特殊領域來看的話,也是可以成立的。文學知識總的來說應該屬于經驗性質的,可是恰好就是在文學領域不能把普遍化作為一種基本訴求,這里,不同族群、不同時代的文學,可能有著完全不同的屬性。西方美學家沃蘭德感慨:“隨著現代藝木愈來愈激進(其目的就是要推翻藝術家所完成的那些美的作品并且最后要推翻藝術作品本身),它也就變得更加難以理解了 在目前的混亂之中,美學必須確定藝術到底能夠是些什么和應該是些什么東西。”①曾經擔任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會長的厄爾-邁納在他的重要著作《比較詩學》中寫道:“這里提到我和中國文學原則的沖突,是因為中國文學的觀點對我來說特別難以接受。”②他們兩人所說的不是針對同一問題,不過他們都分別在時代意義、民族意義上表達出各種不同文學之間可能具有的重大差異。
文學的知識不同于實用學科的知識,它不需要通過效用的檢驗來證明其合理性。譬如某種自然科學的和應用科學的體系,一經實踐就可以看到該種體系的效能如何,文學的思想則很難有這樣的一種檢驗指標。這里涉及到一系列的人的主觀規定性,以及文學問題的儀式性方面,在這種情形下言說的對象和言說本身是一體化的,兩者本來就是一個問題的不同表述,所以他就可以保持在言述的邏輯上有效性。文學知識在不能等同于經驗知識的前提下,它還不能等同于哲學類別的知識。即哲學類別的知識要有對于事物的終極原因的追問,這種追問在經驗的角度無法求解,那么這種追問在一定程度上就不是為了獲得某種解答,而是為了獲得一種看待問題的角度的合法性。當古希臘哲學家要解釋宇宙的終極性質,并且提出了諸如宇宙的本質就是“理念”(柏拉圖)、就是“數”(畢達哥拉斯)、就是某些基本元素(赫拉克利特)等等時,他們無法驗證自己的設想的正誤。他們這樣的假說只不過是為自己提出的一個總體宇宙知識的框架搭建出最基本的平臺,而這樣一種努力在當時是顯得有必要的。人類宗教的作用,不是用以構造一個神話的基礎,也不是用以作為現實中無能為力的憑借,根本的作用在于,宗教是作為一種世界觀的體系,把人的各種知識和信仰串接起來,使得各種支離破碎的經驗能夠粘和成為一個整體,而這樣人們才有一種精神的依靠。哲學秉承了宗教的這個作用,只是宗教更多地關注彼岸世界,而哲學則是在彼岸世界與此岸世界搭建一座橋梁,它要把信仰中的東西加以理性化的分析和言說,這樣就使得超驗的信仰性質的內容和經驗的行為過程中積累的知識可以顯得是整體的。
知識在形式上是關于對象的言說,而在實質上則是對于主體的一種自我言說,至少在部分的意義上是這樣,而這樣一種性質在知識的講述中是未加以說明的。福科曾經說,“如果把科學僅僅看作一系列程序,通過這些程序可以對命題進行證偽,指明謬誤,揭穿神話的真相,這樣是遠遠不夠的。科學同樣也施行權力,這種權力迫使你說某些話。科學之被制度化為權力,是通過大學制度,通過實驗室、科學試驗這類抑制性的設施。”⑧在這里,福科把知識的自我言說性質還擴大到了自然科學的領域。我們一般可能會產生疑問,就是科學所追求的的確是一種客觀的東西,它似乎本身沒有其他的權力、利益方面的考慮,而把知識看成是一種知識的建構者關于自身利益的合法性的表述是一種對于知識的褻瀆。但是捫心自問,當科學作為一種變革世界的系統走向歷史舞臺時,它是以前就有過的各種知識之外的一個新的體系,而這一體系在學理層次上是標榜可檢驗性,如果有經驗對于知識系統的挑戰,那就對系統進行修改,這就極大地方便了知識系統的更新,而在此前往往可能會采取比較激烈的方式才能達成的知識的變革,現在可以成為一種常規的工作。另外就是科學一旦應用于實踐領域,就可以產生某種重要的效果,諸如技術革新再生產中的表現。這里的關鍵癥結在于,科學知識關于知識的更新的承諾有些相當于政客的競選承諾,它其實就是通過知識更新的常規化和合法化,來樹立自身的影響力,而所承諾的更新的常規化,則是在具體觀點可能隨時變化的情況下,整體的科學知識系統則維持不變。事實上,一位愛因斯坦時代的物理學家完全可以明白牛頓時代科學家的知識的表述,而一位筆者所在的武漢地區的未接受過小學教育的當地農民,北部的黃陂人和南部的江夏人就可能無法對話,他們的口音不同,而且在話語中有些常用單詞的用法也不同。這里應該考慮到愛因斯坦和牛頓其實是在一個共同的知識架構之內的不同觀點,它們之間的差異并不是一般表述的那么大。換句話說,兩種爭論性的言談可能是有共同的言述基礎的,而根本不是談論同一個題域的意見之間,才具有更為重大的差異。
二、文學知識的可靠性追問
文學知識的可靠性是一個問題,這一問題不只是已經得出的認識的可信程度如何這樣一個簡單層次的問題,而且還包含了已經得出的各種認識之間的取舍選擇問題。所謂的“詩無達詁”,就是在多種對于詩歌意義的解釋中,并沒有哪一種可以證明自己理所當然地處在可以淘汰其他解釋的地位,或許它們都各自有一定的依據,或許各自的依據都不能成為一種毫無疑義的定論i文學知識的可靠性的懷疑還在于,所謂文學并不是一個文本的事實,而是一個文化的事實。也就是說,一部作品是否屬于文學,如果作為文學,它是在何種價值層次上,這些問題都涉及到所在文化對于文學的規定性,也涉及到批評家的個人化的口味。
有學者在比較詩學的意義上提出“在當今世界主要的幾個文學體系中,并不存在共同的文學價值觀。在某些體系中被奉若神明的詩學觀念在其它體系中根本未被提及。 自亞’理士多德至德里達以降的西方文學和文化觀念并不具有普遍性。”④實際上,在文學史上,所謂的文學從來就是一個游走性的概念,它的外延和內涵都在不斷的變化中。而對于這樣一個變化著的概念所提出的知識就不能冀望它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有效性。如果把一個系統中的文學的知識移換到另外一個文學的系統,要么就是理論自身的言不及義,要么就是對于文學現象的削足適履。
其實關于知識的問題,涉及到知識的對象和方式等一系列錯綜的問題。在對象方面,關于日月星體的運行就可以有現代的天文學的知識和源自古代的占星術這些不同的體系,固然我們不能以占星術的表述作為今天進行太空航行的依據,可是在閱讀古籍和考察民間文化時,卻必須是以這種占星術一類的傳統的見解作為理解的基礎。這樣就是在某一層面不屬于知識的,在另外一個層面則是屬于知識。在知識的方式方面,按照科學哲學的證偽主義觀點,知識是應該可以被證偽的,即一個給定的陳述,它可以通過相關條件來證明,同時也可以在相反的數據下被修正。諸如月亮繞地球運行和地球繞太陽運行,本來都是對的;可是在人們的視覺經驗中,太陽東升西落的感受就顯得地球繞日運行難以被接受,在這樣的情形下地球繞日運行更顯得知識的重要,它修改了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再進一步,地球和月亮以橢圓軌道繞行,就比一般地說明繞行更精確,實際上就是越具體就越可能出錯,而它才有更大的價值,因此知識要有可證偽的特性作為其存在的依據。以此來看,風水術、相面術一類就是模棱兩可的表達意見,往往是事情出現了不同的結果都可以得到解釋,這就不是知識的表述。在這個層面看來,其實文學知識恰好就有怎么說都可能圓通的情況,而別人采用了這樣一種方式來比較好地說明了文學之后,其他人并不能保證也可以取得大致相應的效果。
美國學者希爾斯曾經說,“在科學傳統中,偉大人物是受人敬仰的紀念碑,但是,一旦他們著作中的精華被攝取和吸收,它們就不再被人們所閱讀。而偉大哲學家的著作始終保持其知識的有效性,他們一再成為新一代哲學家哲學反思的出發點。”⑨希爾斯的這一段表白,我們一般是理解為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不同,也就是說,自然科學的新成果一旦出現并且獲得了學界的認可的話,早先的學說就被置于“過時的”行列,而文學等人文學科不同,雖然不斷有新的思想問世,但是早先的思想仍然可以作為對當下有效的言述。不過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其實自然科學的對象是一種可以通過儀器來實測的存在,所以它的言說如何就可以不斷地被糾錯,而人文學科的對象經常屬于一種假定性的存在,譬如文
學中的“意境”、社會學中的“友誼”、歷史學中關于各種歷史發展模式的敘說,等等,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的感受,即采用某一種學說就可以把人們經驗中的事實加以合理化的闡釋,經驗的世界通過這樣一種闡釋才便于思維的把握。而實際上這樣一些模式并不能任意還原。譬如某次戰爭的勝利可能是屬于杰出的軍事指揮,另外一次則是因為氣象因素,還有一次又可能是由于軍事裝備和技術,等等。企圖只是以一種模式就解釋所有的人文現象的做法,那是黑格爾時代之后就已經被思想家們所放棄了的。
英國歷史學家巴特菲耳德(H.Butterfield)在其《歷史的輝格解釋》中提出,“ 不是要讓過去從屬今日,而是 試圖用與我們這個時代不同的另一個時代的眼光去看待生活。假定路德、加爾文和他們那代人只不過是相對的,而我們這個時代才是絕對的,這樣做是不能獲得真正的歷史理解的;要獲得這種理解只能是通過充分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那代人與我們這代人同樣正確,他們爭論的問題像我們爭論的問題一樣重要,他們的時代對于他們就像我們的時代對于我們一樣完美和充滿活力。”⑥這樣,那種絕對可以信任的知識的承諾就顯得可疑了。孔德給出了一個知識的界限:“人類的精神承認不可能得到絕對的概念,于是不再探索宇宙的起源和目的,不著求知各種現象的內在原因,而只是把推理和觀察密切結合起來,從而發現現象的實際規律,也就是發現它們的不變的先后關系和相似關系。”“我們的企圖只是精確地分析產生現象的環境,用一些合乎常規的先后關系和相似關系把它們互相聯系起來。”(z)在這樣一種認識看來,知識所達成的不一定是“真理”,而是達成使得現象在知識的框架中“合理”!真理只有一個,而達成合理的途徑則不一定只有一個!
赫勒曾經說:“我們十分清楚,地球圍繞太陽旋轉,太陽并未‘躲到’云彩后面,但是我們的日常生活是從太陽的‘升’和‘落’,從太陽在云彩之后的‘消失’,而不是從天文學的事實得到的宿示。為了正確地行動,我們甚至不必知道我們業已了解的這么多。”⑧針對文學知識來看,它的有些知識可能在客觀性和對象的實際的符合程度有出入,但是它可以在解釋上給予讀者一種安撫,那么這樣的信息算不算是知識?也許我們得要退一步看待問題,那就是面對外部世界的描述,知識的回答需要有驗證的程序和方式,當知識和現象的表現一致時,我們就認為這個知識是可信的,反之就不可信,而不可信的甚至不能稱為知識。
文學知識的可靠性其實就是該知識的可信度。這種可信度不是依靠儀器來檢測的;而且儀器也確實無法檢測。那么文學知識的可信度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種心理信念的強度問題。譬如文學的意境,你根本不能說哪一個表達就是意境而非此就不是意境,意境實際上是把讀者聯想、把閱讀的再創造的空間加以合理化并且追認到創作的層面,比附為作品的功能的結果。最初提出文學意境的人,他是以此來評價他所推崇的作品,并且也就對他人作出了一個閱讀的示范,而在這種示范的引導下,可以感受到新穎的經驗,這就相當于文學文本的厚度得到了增加。通過這種感受也影響到新的文學的創作,新的創作就自覺地營造作者認為可以表達出意境的文本,于是它形成了從閱讀到創作的一個鏈環。當已經有了文學的意境的理論之后,它對于意境有一套評價的標準,也就可以說它所認可的有意境的文本所包含的意境是真實的;但是這種真實存在是和意境理論共生的,如果沒有意境理論也就沒有這樣的意境。它的真實性在于感受和言說的自洽!這樣一種看待意境的思路是承認意境的真實性,但是這一真實性不同于“月球圍繞地球運行”的真實性。后者是不依賴于人的存在和人的思想而發生的,而意境則必須和人的認定相關。在已經把意境作為一種自覺的美學目標來營造、并且讀者也已經適應了這樣一種看待文學的方式之后,關于意境的評價、意境的操作上的要求等方面就是文學知識的不可或缺的內容,反之,則在物質層面根本不能夠實證的意境的說法,就不是文學知識。這里的知識其實就和知識所存在、所生發的語境相關。福科認為:“我們不應再從消極方面來描述權力的影響, 實際上,權力能夠生產。它生產現實;它生產客觀的領域和真理的儀式。”⑨文學的知識其實可以追溯到文學體制背后的權力關系。文學知識的可靠性,依賴于文學的權力體制的穩固狀態。當文學的體制發生變化,則文學的知識也不能不發生重要的改變。
三、文學知識的積累模式追問
文學知識在發生變化,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文學本身就不一樣,而且在社會發展中知識系統本身也在變化,不同的認知框架對于同一文本也可以有不同的甚至迥異的看待。在這種變化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是不同的關于文學的認知和判斷展開交鋒和碰撞,另外一個方面則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有一些觀點成為了后學者共同認可的,進入到了文學知識的殿堂中。
在這一過程中,隨著歷史的推演,文學知識也發生的改變就是文學知識的累積模式問題。一些知識顯得陳舊了而不被采用,也有一些知識因為體現的價值觀不被認可而受到冷落;而新增長出來的知識因為可以解釋當下所面對的文學問題,或者說它所提供的解釋比較吻合當下人們的精神需求,于是就進入到了知識系統中。前者的狀況有詩歌的音韻學知識,在中國古代系統中采用的“廣韻”,它是宋代以中原音韻為基礎設立的,本來中國隨著社會的變化(文化中心的遷移、主導民族的變化等因素)音韻也發生了變化,要說在清朝的官方語音就夾雜了滿語發音,已經不同于“廣韻”的音韻了,姑且還是把詩歌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領域,可是在白話新詩興起之后,原先殘存的一點韻律的合理性也都消失了,當今的詩歌的韻腳采用的是普通話的發音作為依據。另外就是涉及到了價值觀念方面的內容,在封建王朝時代,應制詩、宮廷詩一類經常運用,包括一些最有地位的詩人也寫了不少此類詩歌,如果在當時就會把詩人的這種詩歌作為“政治正確”的表現加以肯定,可是在封建王朝的“政治正確”在總體上被否定之后,它的被肯定的基礎就被動搖了。在文學知識發生這樣一些陳舊的內容被淘汰的情況下,也會有~些知識可以在后來的階段繼續適用,這樣就會有著舊知識在并不被簡單的棄置的狀況下又有新的知識產生的問題。于是就有了知識的疊加。這里新舊知識之間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取代關系、補充關系,而是并置關系、平行關系。但是在這種并置中彼此并不一定有通約性。在這一累積的過程中可能出現一些復雜的局面。它包括知識類型的回歸,也包括知識的相對適用性問題。
知識的回歸是一種知識更替中比較常見的現象。譬如在對空間的認識上,最初人們假設了空間可以是純粹空無的,而后來覺得絕對的空無無法想象,就假定了宇宙空間中存在著一種“以太”,以太是不顯示的,它是傳遞光線、引力等的介質。可是在現代物理學尤其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出現之后,根本不需要假定這種介質的存在,因此絕對的真空又成為知識的認定。可是再到今天的天體物理學往往假定宇宙中有一種暗物質,因為從目前的宇宙的尺度看,它的星體的質量遠遠不及目前數據顯示出來的質量。暗物質成為虛空中一種隱秘的存在。它成為“黑洞”那種不可被觀測的對象,但是通過可觀測的對象可以測算它的質量。因此知識在變化的過程中,可能恢復到以前被棄置了的某種狀態,當然這種恢復可以被看成一種螺旋式的進程曲線。
在知識的回歸中還不只是具體的思想和觀點,而且更重要的是知識的方法。在原始時代,知識主要依靠經驗來獲得,知識的實踐性是其特征,知識具有經驗痕跡。然后隨著知識量的擴大和質的深化,知識本身需要系統化,于是知識的經驗性特征之外又加上了它的系統性特征,這種系統性特征主要表現為知識本身的自洽和知識的可推演性質,也就是說,通過已經得到的知識,在面對一個給定的現象時,可以有相應的應對或解釋。這些在給定對象條件之后再經過推演分析得出的新的認識,就是知識應該具有的再生功能,否則知識的體系化追求就沒有必要了。在這樣一個新的知識產生的過程中,原先知識的經驗性就逐漸淡出0新的知識是由既有的知識衍生的,這種狀況就相當于亞里斯多德邏輯三段式的演繹推理。如果新的知識和新觀察到的現象之間缺乏可驗證性,或者說它不能解釋新的現象,就會有對知識系統本身作出調整的要求。如果這種調整得到了有效貫徹,那么這樣的知識就可能走向科學;如果知識系統拒絕調整而是頑固的堅持己見,并把新的現象作出一種納入到既有知識框架中去理解的途徑,那么它就成為了一種類似于宗教的信仰體系。信仰體系是自我封閉的系統,它不把經驗問題的新的挑戰作為自身改進的動力,而是把所有經驗的現象都納人到既有的系統中作出解釋,盡管在嚴格的學科意義上這種所謂的解釋并不能成立但也會堅持。
在知識的演進中,方法的回歸是其中的~個方面。在最初的原始認識中,人的認識和人的實踐密不可分,也就是說親身經歷和口傳身授是知識傳播的基本渠道,而在社會分工之后,知識的產生與傳播有一些專人負責,授課和書本的知識傳播成為系統知識、專門知識的主渠道,在這樣的變動下,知識作為認識的結果就和實踐脫節了。這種脫節可以達到一個非常嚴重的程度,就相當于葉公好龍之龍和作為知識對象的龍并無直接關系。當這種脫節成為了知識的常態之后,甚至還把這種脫節加以合理化,認為關注對象本身會影響到知識的純粹性。在此背景下的一個基本假定就是,人的認識都只是對事物做一種不改變事物原貌的關注,如黑格爾就說視覺是純粹認識性的,“對象沒有遭破壞,保持著它的完整面貌”⑩,在這里沒有影響到對象本身是認識的可靠性的一個佐證!可是在近代科學背景的解剖學建立之后,解剖學的認識就是通過打開原先隱秘的軀體器官,進入到軀體內部去發現真理,于是原來的認識作為靜觀方式的唯一性至少就受到了顛覆。真理的獲得可以是通過改變事物的本來面貌來完成的,也就是說,原先與認識相對的實踐現在也就具有了認識論的意義。這樣的一個改變也體現在物理學實驗的領域,即觀察物體的行為本身可能就干擾了物質的運動過程,當觀察者得出對物體的運動的數據時,實際上不是物體本身運動的狀況而是被干擾之后的狀況。而這樣一種事實是無法回避的!
那么知識的累積如何發生呢?當不同的知識相遇時,這里可能出現四種情形:1、新知取代舊知,這樣的過程就達成了知識領域的新陳代謝,它是一種理想的狀況,在知識史、學科史韻角度看便于梳理線索。2、新舊并立,這種并行的狀況基于兩種條件,一是新船并不足以推翻既有的見解,但是新知可能會對某些學科內的現象給予新的有啟迪性的認識;二是新知出現之后可以達成某種互補的效果,新舊知識的兩者并不是水火不容。3、學科的分化,當新知既無法取代舊知,而新知又有比較大的生存能力并不被舊有的知識所屏蔽,那么新知就只有另覓空間,在新的空間中新知可以開辟出新的知識的視野,得出新的學科的見解。4、新知對于舊知造成了挑戰,而舊知在積極面對挑戰的過程中也對于自身體系作出了有效調整,從而在挑戰面前并不至于崩潰,反之也因為新知對既有知識作出積極調整之后的確可以應對詰難所提出的問題,于是舊有知識就通過一種體制之內的改進來化解了知識問題的危機。其實在學科史中,這樣的情形也許才是最為普遍的。
四、文學知識的反思如何可能
我們研究文學是在文學知識的基礎上進行的,那么我們來反思這種知識時也還是得依靠相關的知識,這里就有一個疑難出現了,那就是這種反思如何可能?譬如,關于文學閱讀活動就需要由相關的文學知識,否則面對文學的表達就可能不知所云。喬納森·卡勒舉例說:
如果有人不具備這種知識,從未接觸過文學,不熟悉虛構文字該如何閱讀的各種程式,叫他讀一首詩,他一定會不知所云。他的語言知識或許能使他理解其中的詞句,但是,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他一定不知道這一奇怪的詞串究竟應該如何理解。 他還沒有將文學的“語法”內化,使他能把語言系列轉變為文學結構和文學意義。⑩
卡勒這里說到的問題其實是文學知識領域中的自洽問題。當我們說文學知識的時候,這種文學知識有兩種完全不同的關系。一種是關于對象的知識,譬如李白是中國唐代詩人,假如批評家對李白作品的解讀是采用基督教美學的要求,尤其還去發掘其中上帝的表征的話,那么我們就可以說至少在我們今天的文學批評模式看來是錯誤的,這種對象知識有著對象方面的客觀性要求。另一種是系統的知識,它是系統在運行中需要的,這種知識不能主觀任意的規定,但是它畢竟和人的行為有關,人的行為與之有相關性。在這樣的系統中,相應的規定是知識的必要條件。譬如中國傳統詩學講究“意在言外”,這種美學規定就是在文本的語言表達層面直接顯示的東西可能看不出的一些方面,要求在語用的、語境分析的層面來加以觀照,它所派生的結果就是詩歌美學中意境的追求,由此意境就成為中國詩學的核心范疇。關于意境的知識、以及在具體的閱讀中對于意境的捕捉,其實不能在純粹認識的角度來論證,而必須考慮到中國傳統詩學的理論前提。在此基礎上,我們又可以說,只有能夠把握意境之后,才能夠對中國傳統詩歌尤其是唐代以后的詩歌有深入骨髓的理解。在這里知識是知識系統內部所催生的。由于有某種認定,才產生了相關的認識,并構成了該學科的知識。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的問題就在于,我們針對知識的反思是要考查知識提供了我們認知可能的情況下,它是否會把我們引向錯誤的方向,在這里反思知識需要站在知識之外的一個立場,可是文學知識本身就不是一個統一的立場,我們如何來尋求這樣一個“之外”?當我們面對作為對象的文學知識的時候,我們還是需要比較近距離的考察,分析其中的細節問題;可是當我們來剖析作為系統的文學知識時,這種近距離就可能不再是一個合適的焦距!也就是說,文學知識本身的兩種類別本身使得我們要考查整體的文學知識遭遇到困難!當我們把文學知識作為整體來思考時,它其實并不是一個整體;當我們用分析的眼光來對其進行具體的看待時,則我們又缺乏一種整體的厚度。
這里涉及到了文學研究的思維層次問題。文學研究需要能夠對文學現象產生“同情”,它是有感情投入的;而作為一項研究工作又不能有太多的主觀傾向,于是就在“有”的多少上徘徊,這種量的把握和對對象思考的深度沒有關系,因此也可以說是它耗費了精力,但是不這樣的話,文學研究就要么沉浸到作品所營造的情感的場域中,要么則是于巴巴的在沒有真正把握作品的外在分析里。這樣的結果就是文學研究經常可能是一種錯位的思考。而這種錯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文學科的普遍狀況。美國《紐約時報》國際問題專欄作家弗里曼曾經發表《凌志車與橄欖樹——理解全球化》一文⑥,其中凌志車代表全球化經濟體系,橄欖樹則代表傳統的有著地域特色的文化,兩者之間的緊張關系就是全球化進程的主題。這里的全球化通過一個人工產品的全球市場體系得到了彰顯。其實凌志車作為人工制品更應該是地方性的,因為人總是生活在他的生活圈里面,這種生活圈可以體現為譬如以前封閉條件下的某個山村,另外也可以是遍布全球的肯德基食品店,一位縱然成天東奔西走的忙人,他所到之處其實也還是他的相對固定的場所。在全球化的大勢下,人生活的地方由地圖意義上的某處轉變為商品消費層次上的某處。橄欖樹作為天然物倒是應該作為全球化的代表,也許在氣候土壤等方面,橄欖樹并不能隨處生長,可是作為一個生物物種,它是全球生態圈的產物,全球氣候的某一處的失衡,很難預料會對另外一處產生什么影響,但是從長遠的角度看,全球氣候的相關性是可以肯定的。在此意義講,橄欖樹作為大ca然的一件作品,它更有理由代表了全球化!這里實際上涉及到看待問題的角度問題,在一個角度看來理應如此的,在另外一個角度看來絕非如此!
這里還可以參照一個事實,都市里的婦女們往往會說買雜貨是“買東西”(doing the shopping)(與干家務類似),而買衣服是“去購物”(going shopping)(與愉快地“去外面”相似)。@這里的差別在于,買衣服屬于與自己的身體外觀相關的,而身體外觀在這里成為女性的身份認同的一個具體落實之處。她想象自己是什么樣子,她就把自己穿成那種樣子,她把自己穿成那個樣子,她就認為自己是那樣一種身份或者地位。因此男性需要在生活中苦苦拼搏得來的那張職業意義上或者經濟條件上的地位,女性只需要在購物中就可以達成。“事實”是通過“想象”來達成的。女性產生這樣的認知和女性生活的實際狀況相關。在當今雖然女性的工作是普遍化的,可是女性在文化中依然有一種意識認為家庭狀況比之于自己的工作狀況更為重要。男性需要在自己的職場地位上來證明自己的社會價值,而女性可以通過找到一位如意郎君來實現目的,而她個人的職場地位只是相對于一份“兼職”。在這種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文化規定面前,所謂的嫁得好就要有一個物質臺階作為衡量,這也如同工作的優劣往往和薪酬聯系類似。“買東西”(doing the shopping)是作為家庭主婦的義務,只有“去購物”(going shopping)才是落實到自己的消費。這樣一個社會學意義的措詞,是婦女們根據自身處境得來的分類,它和一般的社會學家的關于消費的分類毫不相干。在這里我們能夠說是社會學家還是婦女中的哪一方有認知的錯誤呢?
文學知識的反思其實就是當我們考察文學的知識時,我們不是去分析一個統一的被命名為“文學知識”的板塊,而是面對一個龐雜的、內部充滿了矛盾、但又在形式上作為一個統一體的認識系統。在這里矛盾的問題無法在一個平面的思考中得到協調。這讓人想起奧威爾(G.Orwell)和赫胥黎(A.Huxley)兩人對于信息時代的一種擔憂,不過他們完全是從兩個不同的方向來人思的,“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愿意讀書;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剝奪我們信息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奧威爾害怕的是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的是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游戲的庸俗文化 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于我們熱愛的東西。”@這樣兩種不同的角度幾乎呈現為邏輯上的對立狀態,按理說它們不應該同時成立,可是事實上在我們面對當今的文化狀況時,卻都是我們需要處理的關系。
恩格斯當年說,“意識形態是由所謂的思想家有意識地、但是以虛假的意識完成的過程。推動他的真正動力始終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則這就不是意識形態的過程了。”⑩這樣一段論述,我們大多只是在看待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的時候帶有一絲譏諷的態度來理解的,其實這也許是人類思想問題的宿命。思想是針對對象的,思想往往不把自身作為一個思考的對象,正如眼睛是觀看的器官,而人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眼睛!對于文學知識,我們并不能奢望能夠有一個總體的、一勞永逸地解決反思的方案,不過我們需要做一些局部的、修補式的工作,而這種局部和修補在長期地堅持中也可能產生出在整體上的洗心革面。我們知道一項艱苦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可是我們可能需要知道,對文學知識的反思因為對象的特殊性,在邏輯上也只能是知難而行。
注釋:
①朱狄:《當代西方美學》,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頁。
②厄爾·邁納:《比較詩學》,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頁。
③福科:《權力的眼睛——福科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2頁。
④見樂黛云、張輝編《文化傳遞與文學形象》,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頁。、
⑤[美]希爾斯:《論傳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頁。
⑥H.Butterfield,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History,G.Bell and Sons,1931,pp.16—17.⑦洪謙主編《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30一31頁。⑧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頁。
⑨福柯:《規訓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218頁。’ · ⑩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上),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3頁。⑩喬納森·卡勒:《結構主義詩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頁。⑥參見倪世雄、蔡翠紅《西方全球化新論探索》,載《國際觀察)2001年第3期。@柯林·坎貝爾:《購物、快感和性戰爭》,見羅鋼、王中忱編《消費文化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第218—219頁。
⑩Neil Postman,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New York:Elisabeth Sifton Books,1986,P.70(此處譯文參照徐賁的文字。)
⑩恩格斯:《恩格斯致費·梅林》,《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01頁。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