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畫傳統語境下,以筆墨為之的意象造型,諸多 蓋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眾法也……蓋自太樸散而一畫之文章都有談及。若從“體—相—用”的角度加以闡釋,則 法立,一畫之法立,而萬物著矣”。那么“一畫”便作為無中國傳統哲學體系為“體”,意象造型為“相”,而筆墨為“用”, 法之法,作為母法,其強調的是“乃自我立”,尊重自我感受,三者之間是互相聯系、不可或缺的關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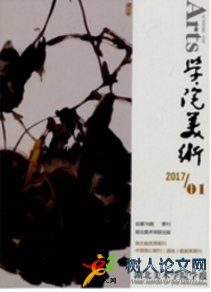
《湖北美術學院學報》至1998年我院正式創刊至今,我們的辦刊思想始終以推進學院美術教學、美術創作和美術理論建設為主旨。不僅立足本院,同時也放眼于國內外美術學科的建構和當代進程。主要欄目:楚美術研究、美術史論、當代美術家、藝術視野、教學研究、譯介、學術動向、關注。
因此,我們不可 貼近自然本真。由此可看出石濤的“一畫論”不是一個關于能單一地來探討筆墨的問題。若缺少了“相”及“體”,中 畫法的理論,而是一種側重于自性本體的理論,這一自性本國畫的筆墨就會被簡省為諸如西方繪畫中畫筆、刮刀之類 體或可以稱為創造本體。在《畫語錄》中,尊受“”“蒙養”“生的工具,筆墨的生發也就成為單一的繪畫技法,何談美與 活”“資任”等石濤整合的概念,都是圍繞著“一畫”而展妙?孔子在《論語》中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 開的,都是為了凸顯“一畫”作為創作本體的特點。石濤所可見“游于藝”先須“志于道”。本文試圖借用“一筆墨”[1] 謂“一畫”乃是畫之“一”,是繪畫創作的最高法則。因而,的概念,由“用”至“相”,進而探究其“體”之毫厘。 “一筆墨”的“一”,有其本源,方得始終。
一、“一筆墨”的“用”
“一筆墨”這個概念的提出,源于筆墨的“用”,有其自身的規律和形而上的意義,是中國畫創作與審美的具體實踐性規律,且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及哲學的深刻內涵。
(一)“一筆墨”的“一”
《老子》提及:“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而在繪畫理論上鮮明地提出“一”的,應屬石濤的“一畫論”。石濤的“一畫論”言簡意深,源于他的哲學思維,而他的哲學又多得益于老莊思想,他的繪畫實踐和他的理論是相得益彰的。下面我們具體看一下他在“一畫論”中的一些觀點。“太古無法,太樸不散,太樸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畫。”(清石濤《苦瓜和尚畫語錄》)在這里,石濤所說的“一畫”,是繪畫創作的法則,而非具體的方法或是技法。他強調的是貼近自然,以悟為真,以創造為本。“這里的自然,不是山川樹木,而近乎于道,可以說是道的另一種說法。”[2]接著他又說,“所以一畫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畫之法者,
(二)“一筆墨”的書寫性
接下來,我們再來探討一下“一筆墨”中對于“筆”的理解,中國畫強調書寫性,是有其特殊意義的。在書法中,后漢蔡邕曾言:“唯筆軟則奇怪生焉。”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敘論》中也提到“筆才一二,象已應焉”,可見在“一筆墨”中用筆何其重要。“中國書法在宋代以后,其技巧大量借用到繪畫中去。書、畫技巧的互滲推進了二者的發展。”[3]“一筆墨”講究用筆的書寫性,講究筆與筆之間的搭接、相讓、虛實等關系,因而與書法中的用筆如出一轍。我們可以考察中國古代遺存的巖畫、彩陶、飾紋,均以線為主要表現手段。以線造型是中國藝術的特點,區別于西方的面與體的概念。通過對傳統中國畫的用筆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繪畫由于造型的需要,其筆鋒的空間運動與時間運動形式大都是從隸書、草書、行書中借鑒而來。如徐渭所言:“迨草書盛行,乃有寫意畫。”由此可見,形成中國文人畫,骨法用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章祖安先生曾說過“書法為虛無之象”,[4] 中國書畫運筆的行止、疾徐,體現的是人的情感。書家認為“書當造乎自然”,書法與繪畫理論上講“氣運筆隨”,都是對書寫性的崇高向往和畢生追求。
一、“一筆墨”的“用”
“一筆墨”這個概念的提出,源于筆墨的“用”,有其自身的規律和形而上的意義,是中國畫創作與審美的具體實踐性規律,且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及哲學的深刻內涵。
(一)“一筆墨”的“一”
《老子》提及:“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而在繪畫理論上鮮明地提出“一”的,應屬石濤的“一畫論”。石濤的“一畫論”言簡意深,源于他的哲學思維,而他的哲學又多得益于老莊思想,他的繪畫實踐和他的理論是相得益彰的。下面我們具體看一下他在“一畫論”中的一些觀點。“太古無法,太樸不散,太樸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畫。”(清石濤《苦瓜和尚畫語錄》)在這里,石濤所說的“一畫”,是繪畫創作的法則,而非具體的方法或是技法。他強調的是貼近自然,以悟為真,以創造為本。“這里的自然,不是山川樹木,而近乎于道,可以說是道的另一種說法。”[2]接著他又說,“所以一畫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畫之法者,
(二)“一筆墨”的書寫性
接下來,我們再來探討一下“一筆墨”中對于“筆”的理解,中國畫強調書寫性,是有其特殊意義的。在書法中,后漢蔡邕曾言:“唯筆軟則奇怪生焉。”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敘論》中也提到“筆才一二,象已應焉”,可見在“一筆墨”中用筆何其重要。“中國書法在宋代以后,其技巧大量借用到繪畫中去。書、畫技巧的互滲推進了二者的發展。”[3]“一筆墨”講究用筆的書寫性,講究筆與筆之間的搭接、相讓、虛實等關系,因而與書法中的用筆如出一轍。我們可以考察中國古代遺存的巖畫、彩陶、飾紋,均以線為主要表現手段。以線造型是中國藝術的特點,區別于西方的面與體的概念。通過對傳統中國畫的用筆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繪畫由于造型的需要,其筆鋒的空間運動與時間運動形式大都是從隸書、草書、行書中借鑒而來。如徐渭所言:“迨草書盛行,乃有寫意畫。”由此可見,形成中國文人畫,骨法用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章祖安先生曾說過“書法為虛無之象”,[4] 中國書畫運筆的行止、疾徐,體現的是人的情感。書家認為“書當造乎自然”,書法與繪畫理論上講“氣運筆隨”,都是對書寫性的崇高向往和畢生追求。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