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dāng)代小說中關(guān)于市民文化的書寫,真實(shí)地反映了普通市民的衣食住行、文化價(jià)值觀和審美情趣。其中,飲食文化尤其成為作家表現(xiàn)的重點(diǎn),從而體現(xiàn)中華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池莉、王安憶、陸文夫的小說充分展現(xiàn)了武漢、上海、蘇州市民的飲食特色與飲食文化,于日常生活細(xì)節(jié)中彰顯普通市民的飲食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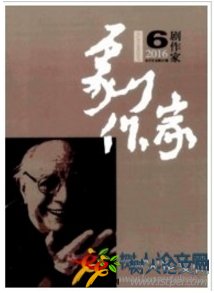
《劇作家》她以每期二分之一版面刊登大、中、小型劇本,大力扶植探索性劇本和新人新作,重視刊發(fā)戲劇研究新成果、南北戲劇信息和戲劇爭鳴,對廣播、影視提供理論探索平臺,每期推介一至二名戲劇家,并開辟“戲劇講座”,深受專家和讀者喜愛。獲獎(jiǎng)情況:中文核心期刊(1992)、中國期刊方陣期刊、黑龍江省社科類一級期刊。
中國當(dāng)代小說中關(guān)于市民文化的書寫,真實(shí)地反映了普通市民的衣食住行、文化價(jià)值觀和審美情趣。在的眾多小說中,衣食住行成為體現(xiàn)人們文化價(jià)值觀和審美情趣的重要載體,從而折射出普通市民的生存狀態(tài)和文化形態(tài)。在百年中國現(xiàn)代化的歷史進(jìn)程中,普通市民的衣食起居和幸福指數(shù)越來越得到作家和讀者的關(guān)注,民以食為天,因此,熱衷于市民小說創(chuàng)作的作家,諸如陸文夫、池莉、方方、王安憶、劉震云等,更是樂此不疲地在他們的小說中展現(xiàn)不同地域豐富的飲食特色和飲食文化,成為中國當(dāng)代市民小說中一道獨(dú)特的風(fēng)景,引人入勝。
一、池莉與武漢市民的飲食文化
池莉是武漢人,生于斯,長于斯,深為武漢人而自豪。從小到大看慣了武漢市民的日常起居,民風(fēng)民俗。平凡的生活離不開柴米油鹽,穿衣吃飯是池莉漢味小說的一個(gè)重要的表現(xiàn)視角,無論是特色小吃還是普通的家常飯菜,無不透漏著武漢飲食的地方特色和文化。池莉?qū)︼嬍澄幕苡醒芯浚⑶以谒男≌f中描寫生動,表現(xiàn)到位,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在《武漢話題·二十七則》里,池莉不惜用大量筆墨來描寫武漢的小吃,對武漢的傳統(tǒng)小吃熱干面、三鮮豆皮、面窩、油糍、小罐雞湯等進(jìn)行了詳細(xì)的介紹,并對這些小吃今不如昔的退化現(xiàn)狀表現(xiàn)出了深深的憂慮。
在池莉的小說中,關(guān)于武漢傳統(tǒng)小吃的介紹隨處可見,在《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中,作者借小說中的王老太之口對武漢的小吃做了精辟的總結(jié):“老通城的豆皮,一品香的一品大包,蔡林記的熱干面,談炎記的水餃,田啟恒的糊湯米粉,厚生里的什錦豆腐腦,老謙記的牛肉枯炒豆絲,民生食堂的小小湯圓,五芳齋的麻蓉湯圓,同興里的油香,順香居的重油燒梅,民眾甜食的洑汁酒,福慶和的牛肉米粉。”[1]這些小吃代表著武漢人的飲食喜好,是武漢城市的直接代表。很多小吃經(jīng)濟(jì)實(shí)惠,符合普通市民的消費(fèi)要求,成為武漢人的驕傲。
除了武漢的傳統(tǒng)小吃,普通的家常飯菜也是池莉津津樂道的對象,在《煩惱人生》中,下班回家的印家厚,對妻子準(zhǔn)備的家常小菜深感欣慰:紅燒豆腐和汆元湯,一疊綠油油的白菜和一碟橙紅透明的五香蘿卜條。普通的家常小菜處處透著生活的溫情。在《來來往往》中,池莉?qū)獞c街的家常小菜的描寫令人垂涎欲滴:“菜是康偉業(yè)時(shí)雨蓬兩個(gè)人一塊兒點(diǎn)的,他們點(diǎn)的涼菜是涼拌籬篙,涼拌田螺,糖醋藕片,紅油蝦球;熱菜是爆炒鴨雜,紅燒魚籽豆腐,白椒豬血,臭干子堡,干煸刁子魚,紫菜苔炒臘肉;蒸菜是兩陽三蒸:粉蒸帶皮腿肉,粉蒸青魚肚膛和粉蒸茼蒿;湯是砂鍋燉的騰湯,騰湯里面是一定要燉進(jìn)枸杞、紅棗、黨參和米粉的。康偉業(yè)和時(shí)雨蓬點(diǎn)菜點(diǎn)得興高采烈,恨不能將吉慶街的家常美味一網(wǎng)打盡。”[2]由此看來,家常人生離不開人們對特色美食的追求,追求中盡顯著武漢市民的文化性格以及他們精明務(wù)實(shí)的品質(zhì)。池莉?qū)⑦@種人生追求世俗化了,更加體現(xiàn)出一位作家對于普通市民衣食住行的終極關(guān)懷。
二、王安憶與上海市民的飲食文化
上海市民的飲食特色處處體現(xiàn)著講究和精致,久居上海的王安憶將這種講究與精致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在小說中,開啟了這個(gè)國際化大都市別具一格的美食傳說。王安憶有著執(zhí)著的上海情結(jié),傾心于描寫上海市民的一日三餐,以日常生活的細(xì)節(jié)揭示人生的真實(shí)。在《“文革”軼事》中,王安憶眼中的上海生活是這樣的:“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樣富于情調(diào),富于人生的涵義:一盤切成細(xì)絲的蘿卜絲,再放上一撮蔥的細(xì)末,澆上一勺熱油,便有輕而熱烈的聲響啦啦地升起。即便是一塊最粗俗的紅腐乳,都要撒上白糖,滴上麻油。油條是剪碎在細(xì)瓷碗里,有調(diào)稀的花生醬作佐料。它把人生的日常需求雕琢到精妙的極處,使它變成一個(gè)藝術(shù)。上海的生活就是這樣將人生、藝術(shù)、修養(yǎng)全都日常化,具體化,它籠罩了你,使你走不出去。”[3]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市民對于飲食的審美追求。
在《長恨歌》中,為消磨時(shí)光,王琦瑤和嚴(yán)師母等鄰居聚在一起,聊天、打麻將、吃下午茶。嚴(yán)師母對于飲食的追求充分體現(xiàn)著講究。打牌閑聊過后,待蓮心湯煮好,嚴(yán)師母便差保姆去買蟹粉小籠,并囑咐保姆一定坐三輪車回來,一則免得乘公共汽車擠漏了湯水,二則到時(shí)小籠包子還燙著嘴。天晚了,嚴(yán)家?guī)熌妇蜁斜D窡齻€(gè)八珍鴨,這可是過年才吃的哦。王琦瑤對于日常飲食的追求則以精致見長。買一只雞,片下雞脯肉留著熱炒,然后半只燉湯,半只白斬,再做一個(gè)鹽水蝦,剝幾個(gè)皮蛋,紅燒烤鼓,就有了四個(gè)冷菜。這種對于飲食的講究與精致堪稱一種境界,就像周作人的《喝茶》一樣:喝茶當(dāng)于瓦屋紙窗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塵夢。這種生活的情趣與王安憶小說中所表現(xiàn)的一樣,處處體現(xiàn)著普通市民的飲食觀念與人生形式。
三、陸文夫與蘇州市民的飲食文化
陸文夫被稱為美食家,很大程度得益于他的描寫蘇州飲食文化特色的小說,他的這些小說被稱為“糖醋現(xiàn)實(shí)主義”,尤其是他的小說《美食家》發(fā)表之后。陸文夫?qū)τ诔灶H為講究,是一個(gè)文化食客。這就使得《美食家》中的朱自冶無時(shí)無刻不追求著吃喝的最高境界:喝茶要選門石路的茶樓,那里的茶樓有考究,茶樓上有幾個(gè)和一般茶客隔開的房間,擺著紅木桌、大藤椅,自成天地。沏茶的水是天落水,茶葉來自于洞庭東山,煮水用瓦罐,燃料用松枝,宜興出產(chǎn)的紫砂壺泡茶,別有一番滋味。
《美食家》中,陸文夫非常細(xì)致地介紹了蘇州的傳統(tǒng)菜肴,如松鼠鱖魚、笑蓉雞片、蜜汁火腿、雪花雞球、蟹粉菜心、菊花魚、冰糖蹄膀、剔心蓮子羹、桂花小圓子、藕粉雞頭米等。除此之外,還有家常炒菜,如白菜炒肉絲、紅燒魚塊、大蒜炒肝、豆腐干,辣白菜,蘭花豆等。這些菜肴來自于民間,經(jīng)過時(shí)間的洗禮和歲月的浸泡,深得蘇州人的喜愛,體現(xiàn)了蘇州市民的飲食觀念。
此外,陸文夫還興致勃勃地介紹了頗具特色的“頭湯面”“醬方肉”“糟鵝”“天下第一菜”(鍋巴湯)“鲃肺湯”“活炒雞丁”“石湖船菜”等菜肴的特色和做法,其中有的詳細(xì)介紹了名稱來歷和有關(guān)的傳說,令讀者大開眼界。因此,陸文夫與蘇州市民的飲食文化緊密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美食家》是一幅真正的蘇州美食畫卷。
中華美食文化源遠(yuǎn)流長,集中了各民族烹飪技藝的精華,綜合了多種文化現(xiàn)象。由古至今,在文學(xué)作品中傳揚(yáng)中華優(yōu)秀的美食文化已經(jīng)成為作家的自覺地責(zé)任。池莉、王安憶、陸文夫?qū)τ谄胀ㄊ忻竦娘嬍澄幕M(jìn)行了精心的梳理和描繪,豐富了中國當(dāng)代市民小說的文化內(nèi)涵,格調(diào)高雅,令人耳目一新。
參考文獻(xiàn):
[1]池莉.池莉文集2[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
[2]池莉.池莉文集3[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
[3]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錄[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