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南進士整體發展過程以雍正二年和咸豐二年兩個時間點為界限,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經歷了落后到興起再到鼎盛的轉變。終清一代,湖南由于進士團體的不懈努力,從科舉落后之地一躍而成為國家仰仗的重要省份。清代湖南進士時空分布受經濟、考試地點、書院教育和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展現出了較為穩定的分布特征。總體上湘中、湘北多進士,湘西、湘南為科舉落后之地,長沙府在湖南科舉中一枝獨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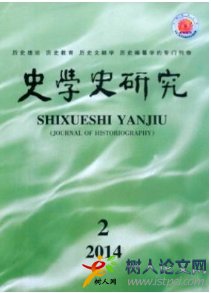
《史學史研究》被北大1992版核心期刊、北大1996版核心期刊、北大2000版核心期刊、北大2004版核心期刊、北大2008版核心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2008年版)收錄。
20世紀80年代以來區域史研究已經成為熱潮,區域文化史也得到重視,各區域關于進士的研究著作也層出不窮,如厐思純編著《明清貴州七百進士》一書詳細地闡述了貴州地區科舉文進士的情況。然在學界專門論述湖南進士的文章著作尚少,本文結合《明清進題名碑錄》、光緒十一年的《湖南通志》等資料,[1]在仔細整理進士名單、籍貫、中試年代的基礎上,擬就清代湖南進士的時空分布展開論述。
雍正二年前的地理分布
清朝初期由于湖南未能單獨開設貢院,至雍正二年(1724年)甲辰科考試前,湖南整體科舉情況均極為庸常,“可憐湖南數千里賦稅之地,漸棄為科第淪落之鄉。”[2]順治二年(1645年)清廷下旨:“開科以取士,薄斂以勸農,誠安民急務,順歸各省準照恩詔事例,一體遵行。”[3]次年會試共取士373名,但湖南省無人上榜,直到順治九年才有善化人黃鈊,武陵人陳維國、茶陵人尹惟日、澧州人俞崇修和田郡玉五人中進士。此后除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九年和康熙十五年三科外,湖南皆有舉人中進士,然而每科進士人數很少,少則只一人,多則不過六七人。至雍正二年,在清初30次科考中全國共錄取了7298名進士,湖南進士人數只有68名。
1.長沙、常德、岳州三府是這一時期進士主要產出地。造成這種分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上述地區本身在湖南屬于發達地區,伴隨經濟發達而形成書院教育事業繁盛。在科舉時代,湖南書院的教育水平遠勝于縣府州官學,湖南較有影響的書院如岳麓書院、城南書院、天寧書院等都分布于長沙、常德、岳州等地,這些書院培育了大批試子,在科舉中取得了優異成績;另一方面是這三府所轄縣較多,其中長沙府的19名進士來自于湘潭(8人)、攸縣(4人)、善化(3人)、茶陵州(2人)、寧鄉(1人)和益陽(1人)六地;常德府的17名進士來自于武陵(14人)、桃源(2人)、龍陽(今漢壽1人)三地;岳陽府的15名進士來源于巴陵(4人)、華容(4人)、澧州(4人)、安鄉(2人)、臨湘(1人)五地。有如此多的縣都產出進士,這三府進士人數多也就不足為奇了。
2.常德、岳州兩府人數基本與長沙持平,出人意料。自康熙三年詔令“湖廣右布政使移駐長沙,轄長、寶、衡、永、辰、常、岳等七府,郴、靖二州。”[1]。長沙府作為湖南巡撫(此時稱偏沅巡撫)駐地,自然是全省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科舉理應領先全省,但長沙府此時科舉卻未能領先,究其原因是受兵災侵擾。岳州府、常德府多進士是由于此地靠近洞庭湖區,湖廣在清前期未分闈考試,湖南試子只能渡湖去往武昌參加鄉試。因此靠近洞庭湖區的岳州、常德試子在湖南的優勢就凸顯出來,他們不必像湖南其他地區的試子那樣長途趕考,也就不會耽誤應考時間。岳州、常德的試子更容易考取舉人,奪取進士,故岳州府、常德府進士較多。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偏沅巡撫潘宗洛上疏:“因中隔洞庭……以致士多畏懼,裹足不前,其能至武昌而入場者十無二三。”[2]靠近洞庭湖區的岳州、常德試子在湖南的優勢就凸顯出來了,他們不必像湖南其他地區的試子那樣長途趕考,耽誤應考時間。岳州、常德的試子更容易考取舉人,奪取進士,故岳州府、常德府進士較多。
3.辰州、郴州、永州和靖州這兩府兩州少產或不產進士。這些地區地處湘西、湘南,自古以來便是湖南落后之地,被稱為“邊楚蠻荒”。經濟上的貧困造成士人無法享受到與富庶地區相同的學習資源。加之,這些地區自古為苗族、瑤族等不以科舉為意的民族聚居之所,漢族文化雖然流入該地區,但卻不占絕對優勢。樸素踏實的民風使得主要以漢人四書五經為考試內容的科舉在湘西、湘南地區沒有引起廣泛重視。清前期由于湖廣未分闈考試,湖南試子不說進士,就連舉人都難高中。偏遠巡撫趙申橋曾上疏說:“第近科以來,自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科至四十一年壬午科,湖廣鄉試中額不等,湖南總不及四分之一,或僅逾十分之三。”[3]這使得偏居湘西、湘南的試子感覺科舉無望,對科舉的期待日漸消薄。
雍正二年到咸豐二年的地理分布康熙以降,湖南文化漸興,士人對科考高中的愿望與日俱增。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終于頒布上諭:“于明春即分湖南、湖北兩闈考試。倘為期已迫,預備不及,則于下科舉行。”[1]湖廣分闈之后的第一年,湖南試子即在雍正二年甲辰科考試中高中8名進士,此后進士人數基本達到全國平均水平,湖南科舉迎來一個嶄新的階段。
隨著單獨貢院的設置,湖南進士的地理分布也出現了較之前有所不同的情況。具體而言,這一時期的進士分布有以下三個特點:
1.分布范圍變廣。貢院單獨設置之前,湖南只有六府一州有試子考中進士,而在這一時期8府、4州有進士分布。永州府前一時期并沒有進士而這一時期總計出現了16名進士,并在全省17府(州、廳)中排名第六,表明這一時期永州科舉事業發展較快。新成立的桂州直隸州也出現了2名進士,靖州,出現了1名進士,新成立的沅州府也考中2名進士,與前一時期相比,湘西終于有進士產出。總之在這一階段,湖南進士的分布范圍較前一階段已經擴大很多。
2.岳州、常德兩府發展乏力,衡州府后來居上。湖廣分闈后,岳州、常德失去之前的優勢,進士增長速度出現停滯狀態,且由于石鼓書院的優質教育以及船山之學的影響,使得衡州府一越成為全省第二進士分布地。
3.長沙府一家獨大。這一時期長沙府共有220名進士,占全省的一半多,遙遙領先于全省其他州府廳,這與長沙府作為全省中心的地位相符合。長沙府所轄的12縣(散州)均有進士,長沙53人、湘潭44人、善化35人、寧鄉22人、湘陰18人、湘鄉15人、益陽10人、攸縣6人、瀏陽5人、茶陵州5人、安化5人、醴陵2人,這些數據表明長沙府整體上教育發展比較均衡,轄區內的各縣和散州各方面綜合情況就全省而言屬優良。
咸豐二年后的湖南進士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起清廢止科舉考試。自咸豐二年(1852年)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1]的52年中清舉行24次科舉,共錄取6271名進士,湖南有279名進士。之所以將咸豐二年作為湖南科舉史上的又一個分界點,并不是出于人數和地域變化考慮,而是基于咸豐二年后湖南在全國地位變化的考慮,湖南進士群體開始在全國掌握政治話語權。
上表所反映的地理分布與雍正二年至咸豐二年的地理分布特征基本一致,說明湖南進士分布具有穩定性。此時湘西的鳳凰廳、永順府終于有進士分布;沅州府卻無進士;乾州廳和晃州廳終清一朝都未有進士出現,湘西確屬湖南科舉文化不興之地。南洲廳雖然沒有進士,但它是光緒二十一年“以華容縣屬烏咀地置南洲直隸廳,以洞庭湖漲沙地并析華容、安鄉等縣隸之。”[1]所以南洲廳沒有進士分布也就情有可原。
湖南進士在這一時期成為清朝依靠的力量,湖湘文化再次成為全國主流思想。嘉慶年間陶澍、賀長齡、賀熙齡等人高中后竭力宣揚已經被時代遺忘的經世致用的理學思想,而后在曾國藩、胡林翼等人努力下,理學群體不斷壯大,湖南士人群體開始初具規模。經世致用的思想也使得鴉片戰爭后原本放蕩不羈的湖南試子希望通過科舉取得在朝為官資格,從而改變腐朽的國家現狀。至咸豐元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后,湖南士大夫群體正式凝結起來。正如楊毓麟在其所編寫的《新湖南》一書中所說“咸同以前,載湖南人碌碌無所輕重于天下,一不幾知存所謂天下之責任,知有所謂天下之責任者,自洪楊始。”也是由于太平天國運動,“清學之發祥地及根據地,本在江浙;咸同之亂,江浙受禍最烈,文獻蕩然,后起者轉徙流離,更無余裕以自振其業,而一時英拔之士,奮志事功,更不復以學問為重。”[2]隨著江浙考據學的衰落以及曾國藩統帥湘軍的節節勝利,湖湘經世致用的理學思想再次熠熠生輝。受這些中興將相的影響,湖南試子無不希望在科場取勝而建功立業,以救國于危亡,湖南進士成為清朝不容忽視的一股力量。太平天國運動后,清朝的歷次重大事件無不受湖南人影響,如洋務運動時期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的活動;戊戌變法時期湖南成為全國最受關注的省份;清末新政時期翟鴻機協理新政,故楊度曾說:“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諸君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華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3]
當前中國處于社會轉型時期,湖南作為一個中部省份,其基礎實力和機遇雖不如沿海省份,但在這一關鍵時期,如何轉化劣勢,加速湖南發展是湖南七千萬人民的共同心愿。本文雖是論述清代湖南進士分布的演變情況,但也展現了清一代湖南在全國地位的變化。清代湖南進士的變化,恰巧反映出清代湖南省地位的變化。清代的湖南由一個飽受戰亂的殘破省份一躍成為清朝政府不得不依靠的大省,且湖南人才輩出,堪稱奇跡。當今湖南在彎道超車理念的帶動下,科技、文化和經濟都有了明顯的發展,百年大計,教育為先,借鑒清代湖南發展的經驗,文化的復興當是湖南振興的關鍵。
[1] 周宏偉:《湖南城區沿革》,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51頁.
[2]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1頁.
[3] 楊度:《少年湖南歌》,《新民叢報》,1903年.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