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國食品安全事故頻發,“問題食品”層出不窮,嚴重損害了消費者甚至社會大眾的財產權益和人身安全。為此,國家在2015年修訂了《食品安全法》,其中第148條第2款再次明確了懲罰性賠償的適用。雖然該條款加大了對違法食品生產經營者的懲治力度,但也存在著主張權利的主體范圍不清、賠償金數額計算標準不合理等諸多問題,因此,本文認為有必要對新《食品安全法》中懲罰性賠償的具體內容加以研究,以指出我國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制度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完善的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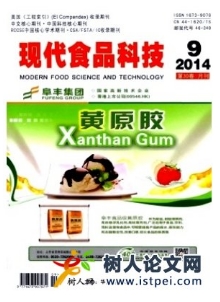
《現代食品科技》雜志是由國家重點大學、國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點建設大學的華南理工大學主辦的全國知名的食品科技類期刊,具體事務依托建有國家和廣東省重點學科的輕工與食品學院運行,1985創刊,月刊。主編為華南理工大學副校長李琳教授,副主編為輕工與食品學院院長于淑娟教授和副院長吳暉教授(兼任常務副主編)。
一、問題的提出
民以食為天,食品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食品安全關系到每個人的人身、財產安全,也是關系到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課題。自進入21世紀,隨著我國食品工業及食品貿易的飛速發展,食品安全惡性事件頻繁發生,“問題食品”越來越多,例如,蘇丹紅鴨蛋、染色饅頭、敵敵畏火腿等,其中最為震驚的當屬2008年乳制品行業的“三鹿奶粉”事件,同時,生產制造、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的“黑作坊”、“黑加工廠”也屢禁不止。一樁樁觸目驚心的食品安全事件,暴露了食品生產經營者唯利是圖,置消費者等社會大眾的生命健康于不顧,同時也說明我國食品安全立法和監管方面存在著不足。
2015年《食品安全法》第148條以立法的形式規定了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的構成要件,何謂懲罰性賠償?現代法律制度中的懲罰性賠償,起源于英美法系國家,它是相對于補償性賠償而言的。具體來說,懲罰性賠償是違法者在主觀惡意、故意甚至詐欺的支配下,對受害人實施了具有超出一般放任、過失等極具惡劣性質的違法行為,并使其遭受人身或財產損害時,法院判決違法者向受害人另行支付的補償性賠償之外的、超過實際損失的一筆額外的金錢賠償。將懲罰性賠償寫入立法文件并應用到司法實踐,這種做法已被兩大法系的一些國家所承認和接受。
作為一種特殊的制度安排,懲罰性賠償制度被我國傳統的民事責任體系排除在外,只能被安排在個別的單行法部門中。就食品安全領域而言,2009年《食品安全法》中的亮點之一就是引入了懲罰性賠償,然而該制度的適用并沒有改變我國食品安全事故愈演愈烈的趨勢。為此,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4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其中第148條第2款規定:“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經營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經營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或者損失三倍的賠償金;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一千元的,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標簽、說明書存在不影響食品安全且不會對消費者造成誤導的瑕疵的除外。”由此可見,國家通過立法強化了食品生產經營者的賠償責任,更加具有震懾力。
二、新《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條款之評析
與2009年的規定相比,新法在賠償金額的計算方式、最低額方面有所改進和提高,此外,增加的但書規定也對標簽、說明書是否適用懲罰性賠償做出了界定。但該規定似乎帶來的只是形式上的變化,并沒有太大的、實質上的突破,至少還有以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和思考。
(一) 懲罰性賠償適用的主體范圍具有局限性
新《食品安全法》第148條沿襲了舊法第96條的規定,將主張懲罰性賠償的權利主體限定為消費者。何謂“消費者”?新舊《食品安全法》并沒有對其作出規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也無明確闡述,只是將“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這一行為納入該法的調整范圍,語義上的模糊,就會對“消費者”這一概念的理解產生分歧,諸如“知假買假”、“單位”等是否可以被涵蓋在消費者的范圍之內,在理論界也備受爭議。同時,在司法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法院駁回原告懲罰性賠償訴訟請求的案例,其裁判理由就是原告不屬于《食品安全法》上的“消費者”。另外,在現實中,并不是所有受到損害的消費者都會提出賠償請求,即便個別消費者啟動了訴訟程序也不是所有權益遭受侵害的人都可以獲得賠償,這就不足以全面保障財產權益或人身健康受到侵害的消費者甚至社會大眾。
(二)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行為難以劃定
懲罰性賠償適用的客觀要件是食品從業人員有生產或經營“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食品的行為,懲罰性賠償適用的前提之一是國家建立了完善的、健全的食品安全標準。我國在這方面的立法以《食品安全法》出臺前后為分水嶺,在之前,我國并沒有統一的食品安全標準,該法頒布實施后,原衛生部根據規劃將食品衛生標準、食用農產品質量標準等加以整合,迄今為止,雖然國家有關部門已公布了300多項食品安全標準,涵蓋了幾千種食品,但我國目前的食品安全標準仍比較繁雜,并且,一些從事食品生產、經營的“小作坊”、“小加工廠”并沒有相應的食品安全標準可供參考。雖然我國法律也規定沒有國家標準時,可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地方標準或企業標準,但這種自行制定的標準很可能規避懲罰性賠償適用,無法使消費者的權益得到保障。
(三)對違法生產經營者的主觀過錯界定不清
新《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第2款對食品生產者、經營者適用不同的歸責原則,就生產者而言,適用無過錯原則,即只要實施了違反食品安全法的行為,而不問其主觀狀態如何,就必須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對經營者而言,適用過錯原則,即只有在故意這種心理狀態支配下仍實施銷售行為,懲罰性賠償才有適用的可能性。通過對比可以發現,法律只對經營者的“故意”行為進行規制,而將經營者的重大過失或其他有損于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排除在外,這一方面減輕了經營者的查驗、注意等附隨義務,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承擔舉證責任。這就可能出現這一狀況,盡管法律賦予了消費者請求懲罰性賠償金的權利,卻使得原告無所適從,也讓法院沒有辦法實施,最后只能息事寧人、不了了之。
(四)懲罰性賠償金的數額計算標準不合理
新《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第2款將消費者的選擇權從舊法中單一的“價款十倍”擴大至“損失三倍”,賠償金的最低額也限定為1000元,這似乎與之前的規定相比更加合理,也積極對備受爭議的“十倍賠償金”做出了回應,但其是否真正提高了食品生產經營者的違法成本?新法中懲罰性賠償金的數額雖然有所調整,以固定金額作為賠償基數,這看似具備了統一標準,也避免了法官的自由裁量,但實際上會使實現規模化生產的企業對其食品承擔低廉的懲罰性賠償,法律的懲戒力度與其獲得的巨額收益之間難以構成比例,這就無法對其起到懲戒和震懾作用,也就使該制度的設置喪失其應有之義。
三、新《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完善
新《食品安全法》對2009年舊法第96條第2款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懲罰性賠償在我國食品安全領域的發展進程,新法的出臺為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我國的適用奠定了法律上的基礎,但很有必要在立法上進一步加以完善,以彌補我國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制度現有的缺陷。
(一) 明確懲罰性賠償適用的前提條件
首先,應界定“消費者”的范圍,對其進行擴充解釋,以更好地使法律的天平傾向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第一,在認定其是否構成《食品安全法》上的消費者時,應首先采取客觀標準,同時考慮其主觀心理狀態。具體說來,當購買者出于合法理性的目的而從事了名義上的購買、實際上的食用行為或兩種行為兼有時,并且使自身權益遭受侵害的,該受害人即可認定為該法上的“消費者”。第二,對于“知假買假”的職業打假者或者“打假公司”,也不應一概而論:如果主觀上企圖通過購買假貨來主張懲罰性賠償以牟取暴利,客觀上實施了超出購買、食用行為并造成惡劣影響時,則不能認定為“消費者”;但如果購買者明知其將要購買的食品有瑕疵或缺陷,但仍出于正常的消費目的而購買,并因此對其造成物質、人身損害時,則應認定其為“消費者”,可以主張懲罰性賠償。第三,就“單位”而言,原則上應將其排除在“消費者”之外,但在特殊情況下可突破該原則,例如,單位發放給職工食品作為福利時,如果發現該食品存在嚴重質量問題,為了避免經營者免于承擔法律責任,應賦予單位消費主體資格,其主張的懲罰性賠償金可以職工福利基金的形式予以發放和安排。
其次,應加快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標準等配套制度,同時參考國際上先進的立法經驗。第一,著重擬定缺失的食品安全標準,主要是針對未被列入我國食品行業安全標準類目的食品,同時,也應提高“家庭作坊”、“小食品加工廠”等市場主體的準入門檻,并為其設置最低限度的食品安全標準。第二,對于地方食品安全標準、特定行業、企業標準,應采取嚴格的備案制度。沒有國家標準的,可允許其根據地方、企業發展的實際情況設置相應的標準;有國家標準的,則應參照適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允許地方、企業制定嚴于國家標準的食品安全標準。第三,食品安全標準要與國際接軌,我們可以積極借鑒國外的食品安全立法技術,這樣才能提高我國食品行業的整體質量和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二) 考量違法行為人的主觀過錯程度
就食品生產者而言,“一刀切”的嚴格責任歸責原則有失公平。為此,我們可以參照其他國家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條件,在主觀方面則將行為人的心理狀態區分為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這就使違法的生產者承擔的法律責任與其過錯程度相適應,不僅合乎比例性原則,也更加具有合理性。
對食品經營者來說,應延伸其主觀過錯的范圍,將重大過失也納入到責任體系中來。之所以這樣設置,是因為在實際生活中存在著經營者因未盡到相應義務且在主觀上無所顧忌,在客觀上卻造成了嚴重食品安全事故的現象,因此,只有將重大過失也作為經營者承擔懲罰性賠償的主觀要件,才能防止其利用法律漏洞來規避相應的法律責任,也能夠更好地救濟權益遭受侵害的消費者。
(三) 采取固定與彈性相結合的賠償金計算方法
懲罰性賠償金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種,即:固定金額模式、彈性金額模式、無數額限制模式,從域外立法來看,設置彈性的、具有可裁量空間的懲罰性賠償金額已為越來越多的地區和國家所接受。我國新《食品安全法》在確定賠償數額時,采取的是固定金額立法模式,這種計算方法雖然操作較為簡便,但缺乏靈活性,不能使法官根據案件實際情況作出具體的、有針對性的懲罰性賠償。因此,可以在原有固定金額的基礎上,采取“階梯式”的彈性賠償金計算方法,劃分的層級可依據違法生產經營者的主觀惡性程度,并在原有最低額的基礎上提高懲罰性賠償的額度。另外,法院在判定懲罰性賠償時,應依據多方面的因素加以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幾個方面,例如,被告的現有財產狀況、原告遭受的物質損失與精神傷害大小、原告額外支出的訴訟費用、被告行為對社會大眾造成的危害程度、被告意識到自己行為不妥時的主觀心理狀態、被告是否采取相應補救措施等等,并且,還應當允許法官對整個案件進行價值評判,并在一定的額度范圍內行使自由裁量權。
參考文獻:
[1]李響.食品安全訴訟當中的懲罰性賠償研究.北京社會科學.2013(4).
[2]周姹、付慧姝.我國食品安全領域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兼議新《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第2款.企業經濟.2015(9).
[3]陳業宏、洪穎.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法經濟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5(5).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