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xué)現(xiàn)代性理論作為我國文學(xué)研究的一個(gè)獨(dú)特視角,由于傳統(tǒng)不同,現(xiàn)代性呈現(xiàn)不同的內(nèi)涵。長期以來,我國學(xué)者一直借用西方理論來闡釋中國文學(xué)的問題,普遍缺乏較為寬廣的世界文學(xué)視野和反思能力。本文從“時(shí)”、“質(zhì)”兩個(gè)方面把握我國文學(xué)現(xiàn)代性特質(zhì),表明中國的文學(xué)現(xiàn)代性總是按自身的特點(diǎn)去演進(jìn),體現(xiàn)出自身的獨(dú)特節(jié)奏、問題呈現(xiàn)方式及重心。當(dāng)今,文學(xué)現(xiàn)代性更強(qiáng)調(diào)為文學(xué)跨越新的精神世界提供一種‘反促力’,這“反促力”就是文學(xué)的現(xiàn)代性的時(shí)代征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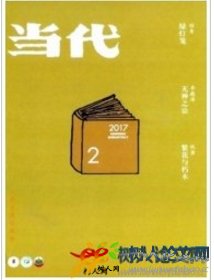
《當(dāng)代》(雙月刊)創(chuàng)刊于1979年,由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主辦。奉行文學(xué)克隆真實(shí)的宗旨,堅(jiān)持以文學(xué)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關(guān)注百姓人生的立場,被公認(rèn)為現(xiàn)實(shí)感最強(qiáng)的中國大陸文學(xué)刊物。長期關(guān)注讀者趣味,尊重讀者權(quán)利,相信讀者格調(diào),成為發(fā)行量最大的文學(xué)原創(chuàng)期刊之一和最受歡迎提文學(xué)品牌之一。
現(xiàn)代性理論作為跨越民族、國家界限的一種世界性景觀,它提供了一個(gè)與政治觀念不同的更為廣闊的研究空間,至80年代后引人我國迅速成為我國的一個(gè)重要理論資源。我國學(xué)者以其為研究和建構(gòu)對象,來闡釋、反思我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理論和創(chuàng)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寫了過去文學(xué)理論研究的狹隘視野,取得了較為豐碩、新穎的成就。
一
西方“現(xiàn)代性”一詞使用始于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有兩個(gè)層面的含義:一是時(shí)間方面的,即指啟蒙時(shí)代以來新的世界體系生成的時(shí)代,是一種持續(xù)進(jìn)步的洽目的性的、不可逆轉(zhuǎn)的發(fā)展的時(shí)間概念;二是觀念(思想文化)方面的,即以建立對社會(huì)歷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認(rèn)知體系次知識(shí)創(chuàng)造和傳播以及各種學(xué)科和思想流派,推進(jìn)民族國家的歷史實(shí)踐,形成民族國家的政治觀念與法的觀念,建立高效率的社會(huì)組織機(jī)制,創(chuàng)建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正義為核心的價(jià)值理念,并推動(dòng)社會(huì)向著既定的理想目標(biāo)發(fā)展。概言之,現(xiàn)代性包含進(jìn)步的時(shí)間觀念、民族國家的形成及其組織機(jī)制與效率、以人的價(jià)值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義等觀念這樣幾方面內(nèi)容。中國“現(xiàn)代性’,一詞的出現(xiàn),則源自周作人發(fā)表于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號(hào)的翻譯文章《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
一般意義上,我國學(xué)者將西方現(xiàn)代性理解為兩個(gè)不同緯度上的現(xiàn)代性。一是社會(huì)現(xiàn)代性,它表現(xiàn)為社會(huì)的現(xiàn)代化以及與工業(yè)化進(jìn)程相關(guān)的社會(hu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二是審美現(xiàn)代性,它以主體性和個(gè)體性為內(nèi)核,對工業(yè)主義和資產(chǎn)階級的市儈哲學(xué)及其觀念的批判。這兩個(gè)維度之間的關(guān)系呈現(xiàn)出相容且相斥的特色,在工業(yè)化初期,審美現(xiàn)代性表現(xiàn)為對社會(huì)現(xiàn)代性的謳歌,而在工業(yè)化后期,審美現(xiàn)代性常表現(xiàn)為對社會(huì)現(xiàn)代性的對抗和批判,審美現(xiàn)代性成為調(diào)節(jié)社會(huì)現(xiàn)代性中負(fù)面的東西。而對審美現(xiàn)代性的內(nèi)涵把握,則一般認(rèn)為其現(xiàn)代性是個(gè)歷史的動(dòng)態(tài)的過程,隨社會(huì)的發(fā)展不斷擴(kuò)展、變化,不同時(shí)期都呈現(xiàn)不同特色。文學(xué)現(xiàn)代性的主要特征就是其批判性的反思,它是現(xiàn)代性社會(huì)得以不斷更新變異發(fā)展的精神動(dòng)力。從這點(diǎn)出發(fā),一些學(xué)者指出,“現(xiàn)代性就是一種質(zhì)的否定性”,“上承文藝復(fù)興和啟蒙運(yùn)動(dòng)的變革精神,與生俱來地表現(xiàn)出對于以往傳統(tǒng)的否定性、叛逆性和批判性”,等等。同時(shí),我國學(xué)者從微觀層面探討現(xiàn)代性的內(nèi)在諸多要素,使得現(xiàn)代性的研究呈現(xiàn)多元的景觀,諸如現(xiàn)代性原則、內(nèi)核、層次問題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在對現(xiàn)代性的研究過程中,我國也有部分學(xué)者忽視中國的現(xiàn)代性與西方的現(xiàn)代性在發(fā)生環(huán)境、社會(huì)制度、文化根基等方面的不同,缺少對中國現(xiàn)代性的民族性的考察。如果以西方現(xiàn)代文學(xué)的特點(diǎn)來確認(rèn)中國二十世紀(jì)文學(xué)的整體特征,以西方文學(xué)思潮的演進(jìn)軌跡來確認(rèn)二十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演進(jìn)的軌跡,這種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會(huì)造成與中國近百年文學(xué)實(shí)踐的距離[4]。現(xiàn)代性作為全球性的話語系統(tǒng)具有普適性,但不同民族、區(qū)域所呈現(xiàn)的現(xiàn)代性具有差異性。中國的社會(huì)現(xiàn)代性與西方的社會(huì)現(xiàn)代性就具有不同的內(nèi)涵特質(zhì)與時(shí)代背景。中國的現(xiàn)代性源于救亡圖存的嚴(yán)酷現(xiàn)實(shí),屬于“晚發(fā)外生型”。經(jīng)濟(jì)上,中國在20世紀(jì)上半葉可謂工業(yè)凋敝,整個(gè)社會(huì)以傳統(tǒng)的農(nóng)牧生活為主;政治上,人民享受的教育、自由等權(quán)利可謂毫無保證。而在西方,其現(xiàn)代性則屬于“早發(fā)內(nèi)在型”,由于推行商品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生產(chǎn)力得到較大規(guī)模的釋放,與其相適應(yīng),各種保障市場運(yùn)行的政策法規(guī)也隨之完善,以物質(zhì)文明為標(biāo)志的現(xiàn)代化水平較高。就審美現(xiàn)代性而言,中國文學(xué)的現(xiàn)代性是在具有民族危亡的背景下產(chǎn)生出來的,從一開始就具有濃郁的憂患意識(shí)和現(xiàn)實(shí)關(guān)懷,從而導(dǎo)致中國文學(xué)現(xiàn)代性的審美先天不足批判有余,偏于以階級斗爭為內(nèi)容的文學(xué)而有意忽略關(guān)注個(gè)人生存價(jià)值的文學(xué)。而西方文學(xué)的現(xiàn)代性是在西方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基礎(chǔ)上產(chǎn)生出來的,前期主要表現(xiàn)對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歌頌與向往,通過啟蒙運(yùn)動(dòng)以理性化來彌補(bǔ)個(gè)性解放帶來的人性缺失,后期則主要表現(xiàn)對工業(yè)化進(jìn)程中出現(xiàn)的人的異化、物化現(xiàn)象的關(guān)注與反思,努力消弧物質(zhì)至上導(dǎo)致的精神荒蕪和變異。目前我們對現(xiàn)代性理論研究呈現(xiàn)“四多四少”的現(xiàn)象,即引進(jìn)的多,闡釋的多,套用的多,解決具體問題的多;批評的少,反思的少,發(fā)展的少,理論重構(gòu)的少。正如有學(xué)者所指,對現(xiàn)代性的簡單化的理解在某種程度上漠視了這一概念的內(nèi)在張力,對中國文學(xué)現(xiàn)代性的獨(dú)特性研究不夠,對現(xiàn)代性視角的理論價(jià)值認(rèn)識(shí)不足“真正的審美現(xiàn)代性,它一方面是批判現(xiàn)代性的(主要是針對現(xiàn)代文明和科技理性對人的壓抑與操縱),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價(jià)值原點(diǎn)仍落在現(xiàn)代二字上,它不是從根本上拋棄現(xiàn)代立場,即它在現(xiàn)代性之內(nèi)反現(xiàn)代性,而不是要回歸前現(xiàn)代性與傳統(tǒng)。這也正是現(xiàn)代性的建設(shè)性的本質(zhì)的體現(xiàn)。”出現(xiàn)上述現(xiàn)象的主要原因,我們認(rèn)為,一方面我國本土現(xiàn)代性理論幾乎沒有,長期以來一直借用西方理論來闡釋中國文學(xué)問題,出現(xiàn)了所謂的“失語癥”,另一方面,我國學(xué)者普遍缺乏較為寬廣的世界文學(xué)視野和反思能力,未能站在區(qū)域化甚至全球化的視野上考察文學(xué)現(xiàn)象和文學(xué)問題。
二
在中國文學(xué)現(xiàn)代性的研究中,“作為一個(gè)歷史分期的概念,現(xiàn)代性標(biāo)志了一種斷裂或一個(gè)時(shí)期的當(dāng)前性或現(xiàn)在性。它既是一個(gè)量的時(shí)間范疇,一個(gè)可以界劃的時(shí)段,又是一個(gè)質(zhì)的概念,亦即根據(jù)某種變化的特質(zhì)來標(biāo)識(shí)這一時(shí)段。正是由于現(xiàn)代性既是量的一個(gè)呈現(xiàn),又是質(zhì)的一個(gè)表微,在時(shí)間性中蘊(yùn)涵一種價(jià)值判斷,其準(zhǔn)確界定較為困難,同時(shí),由于對現(xiàn)代性歷史淵源的梳理與整合的視點(diǎn)各不相同,因此,中國文學(xué)現(xiàn)代性在量的呈現(xiàn)上,即現(xiàn)代性的開端究竟在什么歷史時(shí)段展開,眾說紛紜。有少數(shù)學(xué)者對中國現(xiàn)代性的開端持不同的看法,一是否定20世紀(jì)文學(xué)的現(xiàn)代性特質(zhì),或退一步講只是現(xiàn)代性與近代性的雜揉,"20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的本質(zhì)特征,是完成古典形態(tài)向現(xiàn)代形態(tài)的過渡、轉(zhuǎn)型,它屬于世界近代文學(xué)的范疇,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不具有現(xiàn)代性。”他們認(rèn)為20世紀(jì)的中國文學(xué),既手屬于新民主主義性質(zhì)的文學(xué),也不能用近代文學(xué)概而括之,它是一個(gè)以現(xiàn)代為基調(diào)的帶有近代因素的文學(xué)。其本質(zhì)更接近于現(xiàn)代,但更多的時(shí)候與近代性結(jié)緣,因此,它更多的呈現(xiàn)出交叉復(fù)合的文學(xué)色彩。二是認(rèn)為中國文學(xué)現(xiàn)代性的起源語境應(yīng)該是晚清、晚明甚至更早的宋明時(shí)期,其話語邏輯就是中國很早就有現(xiàn)代性的萌芽。他們認(rèn)為文學(xué)現(xiàn)代性不是單純生成于五四新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的一夜之間,雖主要來自于五四的推助,但文學(xué)內(nèi)部的不斷漸變不應(yīng)忽視。近代至清末,以洋務(wù)運(yùn)動(dòng)和維新運(yùn)動(dòng)為代表,現(xiàn)代性的表達(dá)通過中西、新舊之爭確立其在工具理性與科技主義等現(xiàn)代性的品格,洋務(wù)派注重技術(shù)物質(zhì)層面的現(xiàn)代性,維新派注重“中體西用”制度層面的現(xiàn)代性,而五四則是對西方現(xiàn)代性的思想資源的引進(jìn)。上述關(guān)于中國文學(xué)現(xiàn)代性開端研究的觀點(diǎn)都結(jié)合中國具體的社會(huì)環(huán)境而推演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們認(rèn)為,中國文學(xué)現(xiàn)代性開端的研究,應(yīng)放在整個(gè)社會(huì)環(huán)境背景和學(xué)術(shù)背景上通盤考慮,既要特別注意中國社會(huì)自身的特殊性和特定歷史時(shí)期的作用,諸如洋務(wù)運(yùn)動(dòng)、辛亥革命、五四運(yùn)動(dòng)等等,又要特別注意外來思潮的引進(jìn)、自身政治經(jīng)濟(jì)的改革與文學(xué)自身的獨(dú)立性、從屬性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以此來甄別萌芽與形成之間的關(guān)系,“萌芽永遠(yuǎn)是現(xiàn)代性的可能而決不會(huì)成為現(xiàn)代性的本身。”
我們認(rèn)為,中國整個(gè)20世紀(jì)的過程是個(gè)文學(xué)追求現(xiàn)代化的過程,也是文學(xué)現(xiàn)代性不斷獲得的過程。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作為中國新舊文化的分水嶺,是對舊文化的一種徹底的決裂運(yùn)動(dòng),也是西方現(xiàn)代性思潮大規(guī)模涌進(jìn)的特殊時(shí)期。從文學(xué)自身的角度看,由于文學(xué)與社會(huì)發(fā)展的不平衡性,文學(xué)現(xiàn)代性的研究應(yīng)從文學(xué)文本這一現(xiàn)代性的載體人手,而不是從所謂的思想和文化現(xiàn)象人手來“失本逐末”的研究。從文學(xué)文本人手,我們就會(huì)發(fā)現(xiàn),五四文學(xué)的現(xiàn)代性品質(zhì)鮮明地呈現(xiàn)出與以往所有文學(xué)迥異的時(shí)代特色:一是文學(xué)形式的現(xiàn)代性。漢字結(jié)構(gòu)由繁體到簡體,書寫格式由豎排到橫排,表達(dá)由文言到白話,標(biāo)點(diǎn)從無到有,詞匯從舊到新,處處顯示著與世界的時(shí)代潮流相合拍的現(xiàn)代性眼光,改寫了傳統(tǒng)文學(xué)僵化守舊的形式教條,順應(yīng)了文學(xué)發(fā)展的世界讀寫潮流和變遷了的社會(huì)心態(tài)。二是文學(xué)內(nèi)容的現(xiàn)代性。作為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革命文學(xué),從根本上突破傳統(tǒng)的子民思想,肯定個(gè)性的自由、尊嚴(yán)和價(jià)值,由傳統(tǒng)的載“道”(封建倫常之道)文學(xué)轉(zhuǎn)向“人的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陳獨(dú)秀的“文學(xué)革命”論,胡適的《建設(shè)的文學(xué)革命論》、《文學(xué)進(jìn)化觀念與戲劇改良》,劉半農(nóng)的《我之文學(xué)改良觀》,周作人的《人的文學(xué)》、《思想革命》,魯迅的“隨感錄”等給中國人帶來了真正的思想自覺和文學(xué)的自覺,催生了新的價(jià)值觀的誕生,改變了人們對文學(xué)本原的看法,文學(xué)的目的不再是道德教化和經(jīng)世致用,而是以人為核心的生命體驗(yàn)、人生感悟,比傳統(tǒng)文學(xué)更自覺、更深人地體現(xiàn)了文學(xué)的審美本質(zhì),促使中國社會(huì)的思想和精神發(fā)生整體轉(zhuǎn)型。三是思想反思的現(xiàn)代性。傳統(tǒng)古典文學(xué)對社會(huì)的反思是以封建倫理觀念為背景,對社會(huì)的反思是“中和”。而五四文學(xué)則徹底撕破了封建道德的偽善面孔,向人們血淋淋地揭示封建社會(huì)的全部歷史就是一部人吃人的歷史。具有現(xiàn)代性的新文學(xué)思潮在與反動(dòng)的、復(fù)古的思潮斗爭中,由人道主義、民主主義、愛國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社會(huì)主義文學(xué)觀的轉(zhuǎn)變,個(gè)體價(jià)值從而得以重視、完善并健康發(fā)展。
三
現(xiàn)代性理論給中國的文學(xué)研究提供了一個(gè)理論預(yù)設(shè)和嶄新視角,在全球現(xiàn)代性語境中,來自西方現(xiàn)代性思潮的中國化問題更應(yīng)引起我們的注意,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可與全球現(xiàn)代性相分離或絕緣的中國現(xiàn)代性顏面,中國的現(xiàn)代性總是按自身的特點(diǎn)去演進(jìn)的,體現(xiàn)出自身的獨(dú)特節(jié)奏、問題呈現(xiàn)方式及重心等。“探討中國現(xiàn)代性的顏面,有必要澄清一個(gè)常見的混淆:要么標(biāo)舉中國現(xiàn)代性的特殊國情,要么把它僅僅等同于西方現(xiàn)代性”,同時(shí)面對西方的現(xiàn)代性理論,“是否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是否存在一種非西方的現(xiàn)代性的出路,我們能否對西方的現(xiàn)代性本身作出合理的批判”,只有在不斷的批判與反思之中,我們才能不斷彰顯中國現(xiàn)代性的獨(dú)特內(nèi)涵。文學(xué)的審美現(xiàn)代性本身就是作為一種否定思維的方式存在的,它并不是包治文學(xué)百病的良方。但是,當(dāng)下的文學(xué)研究卻常常把它神圣化、妖魔化了,一研究文學(xué)問題就喜歡貼上“現(xiàn)代性”的招牌,以示學(xué)術(shù)研究的前沿化,使富有活力的現(xiàn)代性理論走向庸俗;同時(shí),一些學(xué)者以現(xiàn)代性的反思性為依憑,對一些陳舊過時(shí)的文學(xué)理論、文學(xué)現(xiàn)象進(jìn)行從新包裝,使正常的學(xué)術(shù)活動(dòng)走向了偽學(xué)術(shù)的邊緣,從而會(huì)導(dǎo)致文學(xué)理論的虛無主義。這些都是我們要時(shí)刻注意的。
考察中國文學(xué)的反現(xiàn)代性思潮之源頭,筆者認(rèn)為,應(yīng)為洋務(wù)運(yùn)動(dòng)的“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承認(rèn)西方工具器物的現(xiàn)代性和普遍性,否定其作為本體文化上的現(xiàn)代性與普遍性。二十世紀(jì)初的梁啟超在《歐游心影錄》中指出西方人過分追求物質(zhì)而喪失精神道德的判斷與指引。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等一系列著述中,倡導(dǎo)鄉(xiāng)村重建理論,來避免西方現(xiàn)代性造成的官僚化、集權(quán)化等社會(huì)弊端。此外,二十年代出現(xiàn)的“國粹派”、“學(xué)衡派”等也都提出了不贊同否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張。這些論點(diǎn)對五四文學(xué)主導(dǎo)性話語進(jìn)行回避、置疑與消解,對西方現(xiàn)代性持有警惕應(yīng)值得重視。但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在現(xiàn)代世界中,仍有某種絕對堅(jiān)固的東西是現(xiàn)代動(dòng)力所不能破壞的,就像大海不可能被它的波浪破壞一樣。這就是現(xiàn)代社會(huì)格局本身。現(xiàn)代性動(dòng)力的運(yùn)動(dòng)就是現(xiàn)代社會(huì)格局的波浪”,這種絕對堅(jiān)固的“現(xiàn)代社會(huì)格局”是我們反思現(xiàn)代性的一個(gè)不可或缺的基點(diǎn)。同時(shí)我們要注意的是,“作為現(xiàn)代性動(dòng)力的載體,文化話語可以持續(xù)否定任何事物;否定可以像一個(gè)主要的體育項(xiàng)目一樣得以進(jìn)行。游戲可能變得具有破壞性,變成憤世嫉俗的或虛無主義的”。
理論的設(shè)立,不能限于理論自身的建構(gòu),更重要的指向?qū)嵺`。對現(xiàn)代性的關(guān)注,某種程度上中國文學(xué)的研究又重新找回自己的言說姿態(tài)和定位,重新肩負(fù)起自己應(yīng)有的歷史使命和社會(huì)責(zé)任感。當(dāng)前,隨著商品市場的建立和完善,社會(huì)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加快,文學(xué)脫離了唯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的藩籬,文學(xué)出現(xiàn)許多新質(zhì)和新變,其自身的現(xiàn)代性也呈現(xiàn)出鮮明的時(shí)代特色,文學(xué)現(xiàn)代性的世俗化特色越來越濃厚。今天的中國社會(huì)雖然還處在現(xiàn)代化的初始階段,但是現(xiàn)代化的步伐正順應(yīng)著世界潮流向前邁進(jìn),特別是當(dāng)前高增長的工業(yè)經(jīng)濟(jì)、現(xiàn)代化的城市擴(kuò)容、大規(guī)模的城鄉(xiāng)一體化建設(shè),必將為我國文學(xué)的現(xiàn)代性鋪設(shè)深厚的時(shí)代背景和時(shí)代資源,使文學(xué)的現(xiàn)代性具有一個(gè)無限廣闊的視角空間。但是,在社會(huì)現(xiàn)代化推進(jìn)過程中,現(xiàn)代性給我們帶來了工業(yè)文明和都市的繁華,也帶來了工具理性、功利主義的盛行,“一個(gè)人不再會(huì)僅僅為了快樂而在一些無用的東西上接受教育,諸如音樂、詩歌和哲學(xué)。人們提供社會(huì)所需要的才干和能力。社會(huì)不需要的東西沒有用途,也沒有價(jià)值”。
部分傳統(tǒng)美德的消失,物質(zhì)的生產(chǎn)和消費(fèi)造就的繁榮,也造成了價(jià)值觀念的混亂,財(cái)富成為鼓動(dòng)一部分人衡量人成功與否的標(biāo)志了。在市場經(jīng)濟(jì)的沖擊下,特別是文學(xué)的商品化,在商業(yè)利潤的刺激下,通過效益的經(jīng)濟(jì)杠桿,篩選掉不符合商業(yè)運(yùn)行機(jī)制的文化形式,出現(xiàn)了寫作的欲望化、身體化、私人化、平面化等等有背社會(huì)道德底線的傾向,文學(xué)消解了崇高和神圣的緯度,文學(xué)對社會(huì)的反思功能減弱甚至消失了。現(xiàn)代性追求中的個(gè)人的存在價(jià)值特別是積極的社會(huì)價(jià)值取向滑落到道德邊緣,公平、自由、平等、正義等體現(xiàn)現(xiàn)代性的價(jià)值理念被商潮湮沒,“商潮的涌起使人們樂于把文學(xué)定格于滿足快感的欲望功能,人們因厭惡以往的仆役于意識(shí)形態(tài)的位置而恥談使命和責(zé)任。對于世俗的迎合使文學(xué)(包括藝術(shù))迅速地小市民化,庸俗和淺薄成為時(shí)尚。這種時(shí)尚使一些人怡然自得而不曾感到羞赦,以“鄉(xiāng)下人進(jìn)城’,文學(xué)題材為例,文學(xué)敘述上庸俗的反思、批判有時(shí)仍不能凸顯現(xiàn)代人生的生活真諦,部分作品的敘述仍停留在前現(xiàn)代或傳統(tǒng)的水平上,漠視城市與鄉(xiāng)村的對立緊張的關(guān)系已趨向和諧發(fā)展之路,漠視鄉(xiāng)下人的身份地位的顯著變化,漠視城市對農(nóng)村的接納度提升的現(xiàn)實(shí),而熱衷于將目光投向歌廳、舞廳、酒吧等消費(fèi)性場合,用有色眼睛看在這里的鄉(xiāng)下人的生存只有賣弄風(fēng)情才是唯一的生路,而忽視了這些場所文明的體現(xiàn);熱衷于將農(nóng)民工進(jìn)城視為一種盲目的流動(dòng),忽視對農(nóng)民工進(jìn)城的現(xiàn)實(shí)考察,總認(rèn)為農(nóng)民工是一種無理智的盲動(dòng)行為,懷疑農(nóng)民對當(dāng)前的人才市場的信息把握能力(諸如通過各種招聘廣告、老鄉(xiāng)關(guān)系等等),始終將農(nóng)民工進(jìn)城當(dāng)成無由頭的外出冒險(xiǎn)活動(dòng),從而使一些作品只滿足于平面描述,缺少審視和深度開掘,無節(jié)制地渲染時(shí)尚,人物面目和情節(jié)故事被時(shí)尚之手緊緊拖住和捉弄,陷人了消閑解悶的時(shí)尚品,失落了真實(shí)。
同時(shí),一些作家流露出精英意識(shí),身處事外的“超然”造成的旁觀姿態(tài)使這些作家在描述農(nóng)民工的時(shí)候不自覺的流露出一種優(yōu)越感,知識(shí)者的精英話語控制著一切,字里行間流露出對農(nóng)民工的輕蔑和對底層苦難的玩味欣賞之意,而全然不顧及嚴(yán)重的社會(huì)不平等的存在與這種不平等的結(jié)構(gòu)正不斷被強(qiáng)化的現(xiàn)實(shí)。文學(xué)和文學(xué)理論應(yīng)該如何體現(xiàn)自身的現(xiàn)代性特色,如何表現(xiàn)、反思工業(yè)社會(huì)壓力下人們那種躁動(dòng)不安、心理焦慮、神經(jīng)緊張、變態(tài)行為等等的異化現(xiàn)象,如何關(guān)注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tài),“對那些只沉迷于物質(zhì)享受而失卻對精神提升的文學(xué)現(xiàn)象,對非理性的、反本質(zhì)主義的、忽視人間真情的寫作,我們必須加以重構(gòu)與解釋,它可以避免創(chuàng)作主體由于思維的偏袒而造成精神的定型化、凝固化,為文學(xué)跨越新的精神世界提供一種‘反促力’。這“反促力”就是文學(xué)的現(xiàn)代性的時(shí)代征候。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