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西地區的社會發展進程早于中原地區,是中華文明起源、文化發生的主要源頭。紅山文化具有“原創性”,為后世中華文化“主根系中的直根系”,是中華文化的重要源頭。燕北西遼河流域是中國“崇龍”文化最早起源地之一,后世中華文化中的崇龍習俗很可能就源自燕北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玉器不僅在技術、藝術等方面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程度,且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內涵,中華尚玉之風源于西遼河流域。修筑祭壇以祭天、建造宗廟以祭祖的文化傳統亦源于燕北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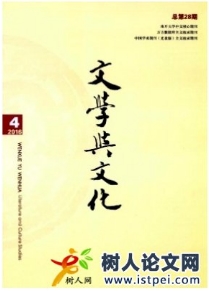
《文學與文化》(季刊)創刊于2010年,是由南開大學出版社主辦的以文學研究、文化研究為宗旨的中文學術刊物,由南開大學陳洪教授擔任主編。現為南開大學中文核心期刊,中國知網(CNKI)、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全文收錄期刊。
已有相關研究成果表明,紅山文化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力水平、社會的復雜化程度以及意識形態等諸多方面,與同期的其他考古學文化相比,并不遜色和落后,反而在某些方面居于領先地位,并對后世中華文明的起源、中華文化的形成有著廣泛而深遠的歷史影響,成為后世中華文明、中華文化的主要源流之一。
一、紅山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地位
關于紅山文化在中華文明中的地位,蘇秉琦先生曾給予高度評估,認為遼西發現的5000年前的祭壇、女神廟、積石冢群,不僅把中華古史研究從黃河流域擴展到燕山以北的西遼河流域,而且將中華民族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蘇先生認為,紅山文化已在相當程度上具備了“文明誕生”的基本要素:高級技術能力;大型公共儀式建筑;等級化、復雜化的社會結構。紅山文化已具有了文明的涵義但不具備文明的全部內涵,應看到它已形成了文明的“干細胞”。紅山文化為后續中華文明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如果說整個中國文明發展史是一部交響曲,遼西古文明則是其序曲,比中原早1000年;如果說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那么西遼河則是中華民族的祖母河。蘇先生還提出:“紅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前就率先跨入古國階段。以祭壇、女神廟、積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器為標志,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的發展已經達到基于公社又凌駕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組織形式。而與此同時代的中原地區迄今還未能發現與紅山文化壇、廟、冢和成套的玉禮器相匹敵的文明遺跡。古文化,古城、古國這一歷史過程在燕山南北比中原地區看得清楚得多,而且先行一步。”①郭大順先生認為:“在中華文明起源的過程中,遼西地區曾先走一步,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總根系中直根系的一部分,并可能與五帝前期的代表人物有關。”②
紅山文化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不僅突破了關于中國文明起源時空上的傳統認識,而且引發了學界對文明要素和標志、文明起源之路和模式等相關問題的熱議,并提出了很多新觀點。紅山文化研究進一步突破了文明三要素的局限,認為金屬器、文字和城難以作為文明的普世標準。有學者提出應把“禮”作為中國文明起源的一項主要標準。考慮到紅山文化玉器的發達及尚玉之風之濃,也有學者認為應把玉器及玉文化作為文明起源的一個重要因素。牛河梁地區發現的規模宏大的祭壇、女神廟、積石冢祭祀遺址也為那種將大型祭祀中心視為文明起源的一大要素的觀點提供了實證。以往認為農業的發展為文明起源提供了直接物質基礎,但新的觀點認為漁獵經濟同樣能夠孕育文明。
通過對紅山文化所包含的文明要素的考察,可以判定紅山文化晚期處于國家產生的前夜,出現了文明曙光。從西遼河流域的歷史發展及社會進化來看,紅山文化晚期的社會發展水平達到了本區新石器時代最高峰,放大到整個中國甚至更大空間范圍內,紅山文化的社會進化程度也更為復雜。尤其是,紅山文化的文明發生之路,在中國乃至東亞具有代表性。所謂“由巫而王”、“由祀而禮”可能正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從氏族邁向文明和國家的獨特之路。對紅山文化的研究表明,紅山文化所處的社會階段正對應于塞維斯的國家起源和形成路徑中的酋邦階段,這不僅為酋邦理論提供了實證,而且也對恩格斯的文明和國家起源理論做了修正、發展和完善,即由平等的氏族社會過渡到國家之間曾經歷一個不平等的氏族社會階段——酋邦階段,這也許更符合歷史的真實。對紅山文化文明起源問題的研究,驗證了中國確實存在著與西方不同的道路和模式。
蘇秉琦先生還認定,以紅山文化為代表的文明起源模式為“原生型”,③因為考古發現確知從距今8000年的興隆洼文化開始,本地區有著幾千年文脈一致、相承的文化序列。蘇先生在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基礎上,認定北方文化區與中原文化區各自文化序列清晰,他們是平行發展的兩個文化區系,并非前者由后者“衍生”而來。他認為各大考古文化區的諸考古文化之發展大都是同步或大致同步的,影響是互相的。但同步不等于對等,它們的發展是有先有后的,影響也不是對等的,而是有主有次的。某些先進文化因素最初在中原以外地區出現并對中原地區產生影響的現象屢見不鮮。中原地區與周圍地區文化交流關系,不是像光和熱那樣由中原地區向四周放射,而是如車輻聚于車轂那樣由四周向中原匯聚。北方地區與中原地區的關系尤其如此。④
二、紅山文化在中華文化源流中的地位
紅山文化具有“原創性”,為后世中華文化“主根系中的直根系”,是中華文化的重要源頭。蘇秉琦先生曾經從文化區系及其相互關系的角度,提出過“三岔口”和“Y形文化帶”的概念,認為這一Y形文化帶在中華文化起源史中具有極為重要地位,是“中華文化史上最活躍的熔爐和文明曙光升起最早最光亮的地區,是中華文化總根系中的直根系”。⑤其中,這個“Y”形文化帶,就包括紅山文化所在的燕北西遼河流域。蘇先生以牛河梁為例,說明距今5000年前晚期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南北交匯,促使中華文化的傳統初現。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壇的平面圖前部像(明清時期)北京天壇的圜丘(皇帝祭天場所),后部像北京天壇的祈年殿方基;廟的彩塑神像的眼球使用玉石質鑲嵌與我國傳統彩塑技法一致;冢的結構與后世帝王陵墓相似;龍與花的結合會使人聯想到我們今天的自稱‘華人和‘龍的傳人。發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間的歷史轉折,它的光芒所披之廣,延續時間之長是個奇跡”。⑥
紅山文化在諸多方面與后世中華文化之傳統相契合,說明了紅山文化與中華文化的淵源關系。就物質與意識而言,紅山文化更重視后者,存在所謂“精神重于物質的思維觀念”。郭大順認為,牛河梁遺址的積石冢“把完全脫離實用性的玉器作為唯一隨葬品而排斥其他與生產、生活有關的器類,更說明紅山人在表達人與人的關系時,是視思維觀念的精神因素在物質因素之上的”,⑦是信仰與意識形態而非經濟聯系,在紅山文化先民的思維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在以后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中,我們同樣發現,是“精神因素”、是信仰和意識形態,而非物質文明和生產力狀況,一直居于突出重要的地位。
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觀念,包括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君權神授的政治觀以及兼容并包的文化觀等均與紅山文化有著淵源關系。紅山文化時期已經有了天、地、人的觀念,這可以從牛河梁冢壇遺址的結構和祭祀功能中找到答案。牛河梁遺址可見對“三”和“方圓”的運用,其中,牛河梁和東山嘴祭壇南圓北方的建筑布局是那個時代天圓地方觀念的反映。尤其有趣的是,馮時運用天文學原理分析牛河梁第二地點祭壇的設計,提出牛河梁三環石壇是“迄今所見史前時期最完整的蓋天宇宙論圖解”。⑧
根據對紅山文化的原始信仰——對天神和祖神的崇拜及文明起源路徑的考察可以斷定,三代以后君權神授的政治觀源遠流長,可追溯到新石器晚期,他是由天神崇拜及對祖神與天神關系的認識,結合現實需要推演而來的。從文化內涵和特征來分析,紅山文化是在吸納周緣文化的優勢因素發展起來的,由此具有了兼容并蓄的特征,并且作為一種文化傳統傳承下來。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從牛河梁與東山嘴遺址可見一般。郭大順先生認為,牛河梁遺址壇、廟、冢三位一體,與周圍自然環境和諧一致。指出:“牛河梁遺址群以三組建筑為主的規劃布局,既主次分明,又相互聯系,彼此照應,形成以女神廟為中心,以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為前沿,以諸多積石冢為環圍,有主軸、有兩翼、有呼應的大規模禮儀性建筑群體。”這一布局乃是“以與當地自然環境完全和諧一致而實現的”。牛河梁遺址“這種大范圍的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的巧妙結合和將人文景觀融入大自然之中的奇特效果,已經超越了建筑群反映的以一人獨尊為主的人與人的等級關系,而具有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的深刻含義,即包括人與天、地之間的關系在內,以至令今人身臨其境也會產生一種‘神地感”。
三、紅山文化“崇龍”習俗及其對后世中華文化的影響
“崇龍”是中華文化傳統的重要內容之一,滲透于中華文化的各個方面。中國是龍的國度,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先秦時代,龍之寓意頗豐;秦漢以來,龍又成了王權的象征,歷代帝王多以龍種自居,龍與封建王朝結下了不解之緣,民間百姓則將龍視為吉祥之物和能夠翻云降雨的神靈。中國的崇龍文化源遠流長,傳承至今,文脈不絕。考古發現的史前崇龍遺跡和遺物,在燕北西遼河流域的紅山諸文化遺存中分布最集中、數量最多、年代最早、題材與造型也最為豐富。⑨可以斷定,西遼河流域是中國“崇龍”文化最早的起源地之一,后世中華文化中的崇龍習俗很可能源自西遼河流域,因此有“龍出遼河源”的提法。⑩
燕北西遼河流域有著中國歷史上的最早崇龍實證,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的興隆洼文化時期,這就是在遼寧阜新查海發現的擺塑“石堆龍”。據調查,該石堆龍采用紅褐色大小均勻的石塊堆塑而成,龍頭、龍身處石塊堆積尤為厚密,而尾部石塊堆積則較松散。此龍昂首張口,蜷身弓背,給人一種巨龍騰飛之感。龍頭向西南,龍尾朝東北,龍身全長19.7米,寬1.8-2米,11郭大順先生將其稱為“擺塑石龍”。它的發現說明,早在興隆洼-查海文化時期,龍的觀念就已出現。不過,該石堆龍之形狀與紅山文化玉豬龍并不契合,有很大程度的不確定性。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內蒙古工作隊在興隆溝遺址成功發掘到了頭部為實物豬首、軀體用陶片、石塊擺放成“S”形的龍形物。有人認為,“擺放的真實豬首及用陶片、自然石塊和殘石器組成的“S”形軀體代表了當時人們心目中的豬龍形象,具有明顯宗教祭祀意義,這也是中國目前所能確認的最早的豬首龍的形態,對研究龍的起源以及龍禮俗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12
距今6000年的敖漢趙寶溝文化遺址中發現有一件尊形陶器,上面刻有豬頭龍、鹿頭龍和鳥頭龍圖形紋飾。據田廣林先生研究,這樣的圖形紋飾迄今在小山、趙寶溝和南臺地三處均有發現,三處發現的圖案紋飾在制作技藝和造型等方面高度一致。共同的特點是作為龍頭采用寫真手法,軀體則采用抽象的變體的表現方法,蜷體麟身,呈飛升之狀。田先生認為:“這種麟身能飛的神秘鳥獸,可以分別視為原始形態的鹿龍、豬龍和鳥龍。從稍晚大量出現于西遼河地區的紅山文化鹿首、豬首、鳥首蜷體玉龍和石龍的造像特點來看,趙寶溝文化遺存中的鳥獸圖,就是紅山文化蜷體龍的直接前身。”
紅山文化時期,尤其在晚期,燕北西遼河流域的崇龍習俗更為濃厚,實證是考古發掘和發現了大量龍形遺存和遺物,主要是玉龍、石龍以及陶器上的彩繪鱗紋。其中,“豬首龍形器”——玉豬龍是紅山文化的典型器類,也是迄今所見年代最早的“龍”的實物之一。紅山文化玉龍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數量最多、形象最完備、構成最清晰、功能較明確的玉龍,在中國龍文化的發展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3目前已確認屬紅山文化的玉豬龍之數量尚未有確切統計,估計包括采集和傳世總計約數十件。其中發現最早、最具代表性的是1971年在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發現的“C”形玉龍。14三星他拉玉龍為豬首蛇身(有學者不贊同蛇身說),該玉龍琢制精細,造型奇特,為已知的距今年代最早的玉龍。紅山文化各種形制的玉龍在造型、制作等方面已經高度規范,無論是在總的形象特征還是細部的藝術處理等方面,都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反映了“龍”的形狀、龍的觀念在人們心中初步定型,崇龍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文化現象。
紅山文化的崇龍習俗、崇龍文化對后世有著深遠影響,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崇龍文化可能就源于北方的西遼河流域。有學者研究,中原地區代表龍山時代最高水平的陶寺遺址出土的彩陶龍紋,從整體造型到局部鱗紋表現,都與紅山文化之龍紋有聯系。據稱古史傳說中黃帝的龍圖騰形象,與紅山文化的玉豬龍極其一致,兩者都呈蜷曲狀。商代甲骨文龍字源于紅山文化的蜷龍,商代的龍形玉雕也承襲了紅山文化玉龍的傳統。商代婦好墓出土的玉龍也應是由紅山文化玉龍發展而來。不過相關實證還不充分。張永江先生指出,(即使)現有材料不能證明中原的龍源于紅山文化,但反過來卻(能)證實紅山文化之龍絕不是中原影響的結果。而且,與龍同樣重要的鳳之形象在小河沿文化的彩陶尊形器上業已出現,15這也遠遠早于中原地區。16
關于燕北西遼河流域的崇龍習俗之起源、發展及其對后世中華文化的影響,田廣林先生概括的非常精當。他說,我國淵遠流長的崇龍習俗最早源于燕北西遼河流域的趙寶溝——紅山文化時期。就影響而言,至龍山時代,源于紅山文化的崇龍禮俗開始流行到黃河流域和江淮之間。至夏家店下層文化、三代及以后,中國的崇龍習尚凝結滲入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中,并在后來中國歷史中長期起到重要的規定性影響。最具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崇龍習尚,其最初原型是豬、鹿、鳥和蛇,至紅山文化時期,發展定型為獸首蛇身、周身蜷曲的標準形態,這便是后世三代龍紋的來源。
四、紅山文化與中華“尚玉”傳統的淵源關系
中國不僅有著濃郁的崇龍習俗,還有著悠久的尚玉傳統。崇龍和尚玉并行為華夏文化傳統的重要內容。根據現有資料,中國的尚玉習俗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有兩個中心,一個是北方的西遼河流域,一個是南方的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其中,尤以前者更為重要。石器時代開始的這種崇玉尚玉習尚,經由幾千年的發展,孕育而成一種內涵蘊意豐富的文化,滲透于華夏民族文化的深處,蔓延和擴展至中華大地,并延續至今。
在燕北西遼河流域,早在距今8000年的興隆洼文化時期,這里的先民們就已具備了辨識真玉的知識和能力,學會了玉器的雕琢和使用。從那時起直至距今約5000年的紅山文化時期,在幾千年歲月里,燕北西遼河地區的尚玉風尚延綿不絕、一脈相承,且愈演愈盛。興隆洼文化玉器是我國已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史前用玉遺存,我國因此也成為用玉最早、歷史最悠久的國家。17迄今所見的興隆洼文化玉器己有數十件,分別發現于四個地點。興隆洼文化的玉器制作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已出土的玉器種類有玉玦、匕形器、管、斧、鎊鑿等。其中,玉玦是中國北方最早發現的,數量最多,其選料加工也比較講究。興隆洼文化玉玦造型規范,工藝精良,可能已使用線切割技術。鄧聰教授認為興隆洼文化所在地為中國玉雕工藝線切割技術的原生地,由此輻射至中原——南方環太湖流域,并輻射至俄羅斯濱海地區、日本列島、朝鮮半島和東南亞地區。18
紅山文化之玉器在承繼興隆洼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得到創新和發展,是史前玉文化的高峰。與興隆洼文化相比,紅山文化玉器數量、種類題材明顯增多。除中原地區常見的壁環類玉器外,紅山文化還有豐富的動物形玉器,如龍、虎、龜和鳥、鸮、魚、蟬以及其它具有專門或特殊用途的玉器,如馬蹄箍形器、勾云玉佩等。紅山文化玉器制作技術先進,雕琢工藝精湛、高超,非專業人員難以做到。紅山文化玉器制作和造型已相當規范,顯然是受到了某種思想和觀念的約束。紅山文化玉器社會寓意深刻、豐富,功能多樣,使用也很普遍。研究表明,紅山文化玉器不僅在技術、藝術等方面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程度。紅山文化“玉文化”發達有多方面的成因:本地區幾千年的制玉尚玉傳統、東北地區玉雕文化的影響,尤其是紅山文化社會意識形態及信仰層面的因素,后者對于紅山文化尚玉之風的興盛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紅山文化玉器在東北乃至整個中國史前玉器發展進程中居于核心地位。19傳統上認為中國古代文明發祥地是黃河中游地區,張永江指出,正如彩陶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成就一樣,玉器也是紅山文化的代表性成就。雖目前尚不能肯定紅山玉器與中原玉器的關系,但紅山玉器在中國玉雕藝術發展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視。20研究表明,紅山文化玉器對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陶寺文化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不過這些影響可能是間接的。殷志強認為,從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徽、裝飾構成以及商代玉器、玉龍看,紅山文化玉器對外影響頗大。21郭大順認為,紅山文化玉器對后世的影響最直接的是對商代玉器的影響。多年主持殷墟發掘和研究的鄭振香認為紅山文化玉器對商代是有影響的。他指出,紅山文化中的“獸形玉”、勾形器柄在其他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未有發現,因此殷墟這兩類玉器大概來自紅山文化。22郭大順提到商代玉器中的代表性玉器即玉雕龍,其玦形和首部形象都是與紅山文化玉龍有著直接的承繼關系的。玉勾形器則是由紅山文化流傳下來的。商代安陽殷墟出土雙連玉龜殼、婦好墓出土簡化型勾云玉器和勾形器、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國墓也出土玉龜殼、勾云形玉器都與紅山文化相同,這是紅山玉影響商周玉的重要例證。
紅山文化對商代玉器的影響可以找到直接證據,紅山文化玉器至少在四個方面對商代玉器有或多或少的影響:一是玉材使用方式。商代立體動物形玉器,多用子料雕刻琢磨,依玉材的形狀與大小施以合適的藝術題材,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玉材。這種巧用玉材的琢玉方法始見于紅山文化。紅山文化動物形玉器,多用此工藝琢磨。二是構圖方式,尤其是一些玉龍、獸形玉器的構圖技巧,很明顯是來源于紅山文化玉器。三是裝飾技巧。商代玉器有一些裝飾技法源自紅山文化。四是紅山文化玉器對商代玉器工藝直接起到了示范與標準化作用。商代玉器在很多方面受到紅山文化玉器造型的影響。殷墟婦好墓出土一件鉤形玉與內蒙古巴林右旗出土的玉鉤形器一模一樣。23
五、紅山文化與中華祭天崇祖、尊奉禮制等傳統的淵源關系
根據目前的考古資料,筑祭壇以祭天、造宗廟以祭祖的文化傳統源于燕北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王巍先生指出,紅山文化的圓形祭壇的形制和結構是我國同類遺址中年代最早的,對于研究中國古代祭祀系統的起源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群中發現的圓形祭壇平面呈圓形,分內中外三層。由外向內逐步升高,整個祭壇成為三重圓壇形。紅山文化的三重圓形祭壇與后代用于祭天的天壇的結構不乏相似之處,即同為三重圓壇,由外向內逐漸升高。而良渚文化的方形祭壇則與中國古代用于祭地的地壇形狀結構相近似。24對于牛河梁遺址,蘇秉琦先生一再強調:壇、廟、冢是配套的,應該近似于北京明清時期的天壇、太廟與十三陵。是“海內孤本”。
中國有悠久的崇祖、祭祖習俗。商代的崇祖、祭祖文化尤其濃重,這很可能是受到了紅山文化的影響。紅山文化女神廟開啟了中國宗廟制度的源頭。郭大順先生對此有過論述:“女神廟的結構、布局已具宗廟雛形。”“女神廟的這種主次分明、左右對稱、前后呼應的復雜結構和布局,其規模和等級都遠非史前時期一般居住址單間、雙間、甚至多間房屋所能相比,而是已開后世殿堂和宗廟布局的先河。”“這正如《禮記·曲禮下》所記:‘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后。史前時期有一種呈‘呂字形的雙間房址曾被建筑史界作為后世‘前堂后室的前身。牛河梁女神廟不僅各室間有了主次之分,而且已具備左右側室,這又正符合‘室有東西廂曰廟(《爾雅·釋宮》)的說法。所以,從建筑結構布局分析,牛河梁確已具宗廟雛形。”
作為中華文明重要因素和標志的“禮”源于新石器晚期的巫術和祭祀,紅山文化的祭祀活動尤盛,很可能是后世中華之“禮”和禮制文明的直系源頭。王立新先生認為,牛河梁遺址一帶埋葬的是當時社會上的一些特殊人物,而同時又禁絕世俗性居住和一般性的族屬墓地進入這一地區,這與周代社會“禮不下庶人”的做法是頗為接近的。25周代的禮制,發端于原始社會末期的祭祀禮儀,經由商代,完成由祀到禮的轉變——即由調節天人關系發展為調節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有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是禮制,敬天地、祭祖宗、尚君權是其基本內容,紅山文化是這種博大精深的中華禮制文化的肇始。26“禮”、“禮制”或“禮治”的核心是君權神授和宗法思想,夏商西周三代統治階級所使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繼承了上古社會形成的神權思想和宗法思想。君權神授和宗法傳統構成了中國上古社會的根本政治制度,其源頭可追溯到紅山文化。
東山嘴和牛河梁建筑遺址契合中國古代建筑布局之風格,可以斷定,紅山文化開啟了中國特色建筑傳統之先河。徐光冀先生曾指出,東山嘴遺址“石砌建筑基址呈組群布局,而且采用均衡對應的方式,以南北縱軸線安置主要建筑,注重中心建筑與兩側建筑對稱,方形建筑與圓形建筑對應,開了具有我國特色的建筑布局的先河”。27尤為有趣的是,東山嘴和牛河梁遺址均體現了古人講求建筑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的用意。東山嘴遺址石砌建筑基址的主要特征:遠離居住區,基址幾乎占據整個山梁正中向南突出的前端部分,周圍地勢開闊,東臨大凌河,與對岸馬架子山遙望。而牛河梁“女神廟”則表現為主體建筑既有中心主室,又向外分出多室,以中軸線左右對稱,另配置附屬建筑,形成一個有中心、多單元對稱而又富于變化的殿堂雛形。遺址內供奉有主神、群神及附屬的動物偶像,墻壁彩繪等,這些特點對中國古代宗教建筑的影響顯而易見。
注 釋:
①蘇秉琦.蘇秉琦文集(三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319.
②郭大順.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牛河梁紅山文化壇廟冢[A].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與玉器精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③蘇秉琦.國家起源與民族文化傳統(提綱)[A].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M].沈陽:遼寧大學處版社,1994.
④郭大順.從‘三岔口到‘Y形文化帶——重溫蘇秉琦先生關于中華文化與文明起源的一段論述[J].內蒙古文物考古,2006,(2):99.
⑤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124-127.
⑥蘇秉琦.象征中華的遼寧重大文化史跡[J].遼寧畫報,1987,(1).郭大順.從“三岔口”到“Y”形文化帶——重溫蘇秉琦先生關于中華文化與文明起源的一段論述[J].內蒙古文物考古,2006,(2):99.
⑦郭大順.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牛河梁紅山文化壇廟冢[A].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與玉器精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⑧馮時.紅山文化三環石壇的天文學研究——兼論中國最早的圜丘與方丘[J].北方文物,1993,(1):9.
⑨田廣林.中國北方西遼河地區的文明起源[D].東北師范大學,2003.
⑩郭大順.龍出遼河源[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
11席永杰.從考古新材料看西遼河流域古代科技發展水平[M].赤峰學院學報——紅山文化研究專輯(第一輯),2008.17.
12殷志強.紅山文化玉龍要素構成辨析[A].紅山文化研究——2004年紅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304.
13翁牛特旗文化館.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發現玉龍[J].文物,1984,(6).
14遼寧省博物館.遼寧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J].文物,1977,(12).
15張永江.論紅山文化的幾個問題(下)[J].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2):41.
16張緒球.中國史前玉器的起源與發展[A].玉魂國魂——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C].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17席永杰.從考古新材料看西遼河流域古代科技發展水平[M].赤峰學院學報——紅山文化研究專輯(第一輯),2008.13-14.
18員雪梅.紅山文化玉器研究述評[M].紅山文化研究——2004年紅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259.
19張永江.論紅山文裕的幾個問題(下)[J].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2):42.
20殷志強.紅山文化玉龍要素構成辨析[A].紅山文化研究——2004年紅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306.
21鄭振香.殷墟玉器探源[A].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22殷志強.紅山文化玉龍要素構成辨析[A].紅山文化研究——2004年紅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306.
23王巍.紅山文化與中華文明起源研究[A].紅山文化研究——2004年紅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58.
24王立新.論紅山文化的社會性質[A].紅山文化研究——2004年紅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123-128.
25王惠德.紅山文化無底筒形陶器初步研究[A].紅山文化研究——2004年紅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46.
26徐光冀.座談東山嘴遺址,徐光冀發言記錄[J].文物,1984,(11).朱乃誠.遼西地區文明起源研究的歷程[A].紅山文化研究——2004年紅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21.
27張永江.論紅山文化的幾個問題(下)[J].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1990,(2):42.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