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圍繞“自然辯證法”的問題爭辯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馬克思是否贊同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研究;馬克思與恩格斯在自然觀上有無原則分歧;辯證法是否適用于自然界;“自然辯證法”應當具有怎樣的學科定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自然辯證法”是一個具有鮮明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科。新時代中國自然辯證法的學科建設與事業發展,必須承繼自然辯證法的馬克思主義傳統,適應新時代發展的社會需求,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尋求自身定位與未來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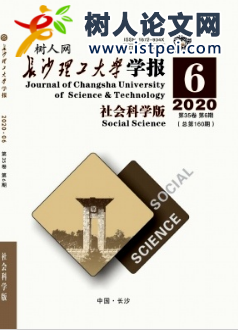
本文源自《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反映校內外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本刊系綜合性社科類高校文科學報,自辦刊以來,一直秉持辦精品學術刊物的宗旨,追求高學術品位,力求辦成學術水平高,編輯精美的社會科學類學術刊物。獲獎情況:全國百優社科學報、湖南省社科期刊一等獎、2002年全國文科學報“百優期刊”、1998年湖南省優秀理論期刊。
提到“自然辯證法”,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恩格斯的名著《自然辯證法》。也正是在這一名著影響下,我國確立了一門哲學學科———“自然辯證法”。后來考慮到其他的學科都叫“某某學”,如倫理學、邏輯學,“自然辯證法”作為學科名稱好像不太規范,出于學科建設考慮和國際學術交流需要,“自然辯證法”才改為現在所用的“科學技術哲學”,作為哲學一級學科下的一個二級學科。但是,恩格斯給我們留下的只是未完成稿,后人在編纂恩格斯的手稿時才冠以書名《自然辯證法》。早在1873年恩格斯開始撰寫這部著作之前的1865年,柏林大學講師杜林就已經出版了以“自然辯證法”命名的著作。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就是針對“創造體系的”“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有感而發,是在友人的“請求”之下,“跟著杜林先生進入一個廣闊領域”展開批判的[1](P8)。這一事實說明,“自然辯證法”這一概念并非恩格斯原創,而且恩格斯嚴正批判了杜林的“自然辯證法”。1925年,恩格斯的手稿由當時的編輯梁贊諾夫(1870-1938)冠名《自然辯證法》在蘇聯出版。1927年,當第二次出版該手稿時,梁贊諾夫又換了個書名《辯證法與自然》。而對于我們所說的“自然辯證法”學科的教學與研究,蘇聯學者則是在“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下進行的。從中國20世紀80年代曾出版《自然科學哲學問題》雜志,可以看到蘇聯的這種影響。可以說,中國的“自然辯證法”深受蘇聯影響,之后蘇聯也不再強調這一稱謂,但“自然辯證法”還是在國內學者研究中引起了諸多爭辯,這種爭辯可細分為以下四個問題。
一、馬克思是否贊同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研究
歪曲、批評、詆毀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思想,在自然觀上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立起來,源于以盧卡奇為代表的某些西方學者的思想主張。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認為,恩格斯未能把握住辯證法中的主體因素,缺少主體的“自然”辯證法不是作為“認識”辯證法的“革命的方法”[2]。西方學者“以黑釋馬”,渲染馬克思青年時代《巴黎手稿》中的人本主義思想,夸大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思想關聯,認為恩格斯誤讀黑格爾而把辯證法歸于自然界。阿爾都塞在《保衛馬克思》一書中批評某些“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們把馬克思裝扮成胡塞爾、黑格爾或提倡倫理和人道主義的青年馬克思,而不惜冒弄假成真的危險”[3]。針對西方“馬克思學”對于恩格斯的種種批評責難,制造馬克思與恩格斯之間的思想對立,黃楠森先生明確指出:“其目的就是要否定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唯一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4]。
馬克思是否贊同恩格斯的自然、自然科學的哲學研究這一問題,答案是明確的、肯定的。針對杜林錯誤思想的蔓延,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肆意攻擊,1876年5月24日,恩格斯寫信詢問馬克思的意見。馬克思次日回復恩格斯說,我們對待這些先生的態度,“只能通過對杜林的徹底批判表現出來”[5](P15)。馬克思知道恩格斯撰寫《自然辯證法》的計劃,并表示高度期許。1876年10月7日,馬克思寫信給威廉·李卜克內西,否定了自己“將參加同杜林先生的辯論”的錯誤報道,明確指出恩格斯正忙于批判杜林著作的寫作。馬克思認為,這對于恩格斯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犧牲”,因為恩格斯為此耽擱了“更加重要得多的著作”,即《自然辯證法》的寫作[5](P194)。在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明確指出全書的絕大部分世界觀是由馬克思確立、闡發的,其中第二編“政治經濟學”部分的第十章《〈批判史〉論述》就是馬克思寫的,在付印之前全部原稿都念給馬克思聽過。1878年10月10日,馬克思在致摩·考夫曼的信中高度評價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論》,認為這本書“對于正確理解德國社會主義是很重要的”[5](P322)。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不但有長期學術合作也有理論分工,恩格斯講自己的主要任務就是在報刊上批駁各種敵對見解,以論戰的形式闡發、捍衛馬克思主義觀點[6]。正是恩格斯承擔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宣傳普及以及針對各種錯誤思潮的批判工作,馬克思才有更多時間和精力從事哲學基本理論的闡發、發展與完善。
確立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需要堅實的數學與自然科學知識基礎。恩格斯為此進入了長達八年的艱難“脫毛”階段,褪去不適于追趕自然科學進步的陳舊知識羽毛,代之以更為輕快有力飛翔的新生知識羽毛[1](P13)。馬克思本人每每為最新的科學成果欣喜,并堅持自然科學知識的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在1863年7月6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寫道:“有空時我研究微積分。順便說說,我有許多關于這方面的書籍,如果你愿意研究,我準備寄給你一本。我認為這對你的軍事研究幾乎是必不可缺的。”[7](P206)在1865年8月1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寫道:“‘利用這個機會’,我又順便‘鉆了一下’天文學。”[8]在1877年10月25日的致信中,馬克思表達了其與恩格斯兩人給予科學成果高度一致的評價。馬克思寫道:“我和恩格斯非常感謝寄來兩本《物質動力學說》。我們兩人都認為,我們的亡友[按:指莫·赫斯]的這部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價值并且為我們黨增添了光榮。”[5](P284)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講話》中高度評價馬克思為科學巨匠,盡管他專心致志地研究科學,但是他并沒有完全陷進科學。馬克思欣喜于任何一門理論自然科學的發現,但對于那些能夠帶給工業生產、社會歷史革命性影響的科學發現,馬克思的喜悅就“非同尋常”了[9]。馬克思不是為科學而科學,對馬克思而言,“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這必須從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對于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社會制度變革的視角理解。
二、馬克思與恩格斯在自然觀上有無原則分歧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自然觀上是否存在原則分歧,對于這一問題的認定有賴于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觀的精準解讀和完整把握。西方學者無視恩格斯研究的自然對象是“被人的活動改造過的自然”,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是與實踐、主觀貫通聯系的辯證法,不能理解恩格斯永恒的自然規律變成“歷史的自然規律”的深刻辯證含義[10]。把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理解為僅僅關注外在于人的天然客觀規律而漠視人在社會歷史和改造自然中的能動作用,不僅僅是西方學者的“發現”,也有國內學者的附會和跟進。
這可能是融入西方學術話語的策略之選,也可能是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思想浮光掠影之后的匆忙結論。恩格斯強調人與其他狹義動物的不同,首先是“手”,然后是手和“腦”一起,“反作用”自然界“有意識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1](P421-422)。人們在不斷地認識自然規律的過程中,逐漸從對自然事物干預的較近后果認識擴展到較遠的后果認識,當然還總是有一些不為我們所認識的負面實踐后果出現。恩格斯指出,隨著我們自然認識的不斷積累和深化,我們就會認識到自身與自然界的一體性,“那種關于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之間的對立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1](P560)。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有一篇《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研究》的論文,對于我們正確理解和把握恩格斯自然觀大有益處,有必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針對一些自然科學家迷戀“招魂術”“降神術”,恩格斯指出,從自然科學走向神秘主義的最可靠道路,不是“理論思維”“辯證法”,而是蔑視理論思維的膚淺經驗主義。即使是憑借“經驗性的實驗”,也難以擺脫“降神者的糾纏”。在這篇論文中,恩格斯通過對經驗主義的批判,強調了理論思維、主觀能動性在自然科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缺少了理論思維的徹底經驗主義者,就像休謨那樣沒法把兩件自然現象聯系起來,只能走向否棄“因果關系”的懷疑論。恩格斯明確指出,“輕視理論顯然是自然主義地進行思維、因而是錯誤地進行思維的最可靠的道路”[1](P452),從而與“自然主義”劃清了界限。
一些學者指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等于“客觀辯證法”,區別于馬克思強調的“主客體辯證法”,偏離了馬克思的實踐唯物主義。其根據是恩格斯曾經講過:“唯物主義自然觀只是按照自然界的本來面目質樸地理解自然界,不添加任何外來的東西。”[1](P458)但是,我們要注意恩格斯在這里所講的具體語境,是在什么樣情況下強調客觀自然的。恩格斯是在講到哲學史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世界觀的歷史轉變,講古希臘的樸素唯物主義之后是兩千多年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占世界主導地位,要回歸到唯物主義世界觀必須對唯心主義世界觀予以批判。恩格斯強調,“返回到不言而喻的東西”所面臨的困難,這就是我們必須面對兩千多年唯心主義世界觀的“添加”,我們要對“添加”的唯心主義世界觀“這一外來的東西”進行批判。這里的批判不是全盤否定和拋棄,而是“要把那些在錯誤的、但對于那個時代和發展過程本身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唯心主義的形式內獲得的成果,從這種暫時的形式中剝取出來”[1](P458)。在此,恩格斯要與唯心主義世界觀劃清界限,對唯心主義展開批判背景下強調客觀自然的首要地位,這是非常正當、沒有問題的。即使如此,恩格斯還是提出了吸收唯心主義形式下取得的積極人類成果,體現出恩格斯一以貫之的辯證法思想。
三、辯證法是否適用于自然界
辯證法是否適用于自然界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都給出了確定無疑的肯定回答,馬克思從來沒有否認過自然界的辯證發展歷程。如果說,自然界的辯證發展在希臘人那里還是天才的直覺,恩格斯的辯證自然觀則是具有更為明確形式的嚴格科學研究結果。自康德在“自然界絕對不變”自然觀上打開第一個缺口,賴爾以地球地質的“漸變論”取代居維葉的“災變論”,特別是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細胞學說、生物進化論三大科學發現,“整個自然界被證明是在永恒的流動和循環中運動著”[1](P418)。1853年,馬克思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開篇指出,黑格爾贊譽“兩極相聯”規律揭示了“自然界的基本奧秘”,“是一個偉大而不可移易的適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馬克思沒有就此展開直接理論論證,而是確認太平天國運動對于文明世界的影響是“兩極相聯”原則的“明顯例證”[11]。在此,馬克思不但肯定了黑格爾對立統一規律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同時也肯定了對立統一規律能夠在社會歷史領域中得到證明,科學認識的辯證法體現著自然界的辯證法。馬克思在1867年6月2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明確表示,自己在著述中引用了黑格爾發現的從量變到質變的辯證法規律,并把這一規律“看作在歷史上和自然科學上都是同樣有效的規律”[7](P264)。
恩格斯不滿于當時自然科學和哲學現狀,它們看到的要么是“自然界”,要么是“精神”,就是看不到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恩格斯對于一味強調自然界對于人的基礎性決定作用,漠視或者否定人對于自然界的積極改造作用的“自然主義”歷史觀給予批判,這同樣是對當今某些誤解、肢解恩格斯自然觀學者“非此即彼”思維方式的絕好批判。恩格斯對于人的實踐活動在因果認識中的確證作用闡發得非常明確,恩格斯指出單憑觀察所得的經驗,自然現象的前后相繼不能“證明”現象間的因果聯系;但是人的實踐活動帶來的自然界變化可以對因果性作出驗證,可以從成功的或者是失敗的正反兩方面行動后果作出“雙重驗證”。人的思維基礎不僅僅是“自然界本身”,人是在學會“改變自然界”的基礎上發展自己智力的[1](P483)。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長達四十年的共同戰斗中,不是為了理論而理論,而是要承擔各種各樣的理論批判和教育大眾的任務。這種復雜局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論本質的“家族相似”之下,為應對各種理論挑戰,他們的著作闡述就會有不同的側重和互補。理論批判不得不進入對手的問題和范式,雖然這可能降低論辯的境界和水平。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高喊“向德國制度開火”,雖然這種制度本身已經昭然若揭,雖然這種制度低于任何批判目標的水平,但是在此批判、駁倒敵人已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表達憤怒、消滅敵人的武器手段。按照馬克思所說,這種“搏斗式的批判”不在于敵人是否旗鼓相當的高尚有趣,而在于“給敵人以打擊”[12]。恩格斯講自己面對杜林的自吹自擂和陰謀攻擊,過了一年才下決心寫作《反杜林論》,“啃這一個酸果”[1](P7)。
“因為在批判和論戰中,決定著述‘有效性’的不是其本身的學術價值,而是其論戰效果。這兩者并不一定呈正比例關系。有時學術性高,論戰效果未必好;論戰效果好的,學術性也不一定就高。”[13]1860年,馬克思寫了與庸俗唯物主義者論戰的著作《福格特先生》,雖然具有很高的文學和學術價值,但是從論戰效果來講“得不償失”。此后馬克思很少參與論戰,這一重擔更多地落在了恩格斯的肩上。對于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當今一些學者的評價并不是很高,認為其主旨是“舊唯物主義范式”的“物質本體論”。但是,《反杜林論》在當時的批判效果很好,起到了宣傳、教育、發動群眾的作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三版序言中說:“本書所批判的對象現在幾乎已被遺忘了;這部著作不僅在1877年至1878年間分篇登載于萊比錫的《前進報》上,以饗成千上萬的讀者,而且還匯編成單行本大量發行。”[1](P10)所以,我們不能脫離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的革命形勢和當時語境來學習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而是要在理論與實踐的互動中體會、領悟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精神實質,在理論與實踐的互動中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家族相似”下的不同闡述。
四、“自然辯證法”的學科定位與未來發展
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寫于1873年至1883年間,是指導工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爭取自由解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重要部分。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后,歐洲工人運動進入低潮。巴黎公社起義失敗的經驗表明,無產階級要在與資產階級的斗爭中取得最終勝利,必須有自己的政黨,需要更完備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自然辯證法》就是在這樣的無產階級革命情勢下產生的。《自然辯證法》進入中國,不論是在延安戰爭環境下用理論武裝群眾,還是在改革開放時代引領思想解放,自然辯證法對促進中國革命與建設事業蓬勃發展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吳國盛教授指出,中國自然辯證法有兩個傳統:一是從20世紀50年代延續下來的自然辯證法傳統;二是新興的科學哲學傳統[14]。從后來吸納并結合科學技術哲學的廣義自然辯證法來看,可以說自然辯證法有兩個傳統。但是從恩格斯創立《自然辯證法》的本意、內容來看,從自然辯證法的最初翻譯、進入中國來看,它只有一個傳統———馬克思主義傳統。
不僅僅是自然辯證法的理論傳統,自然辯證法的現實發展對于自然辯證法的學科歸屬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當前形勢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蓬勃發展,馬克思主義學院特別是重點馬克思主義學院建設如火如荼。馬克思主義學院統一開設全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課程,統一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課教師,統一負責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自然辯證法”是高等院校為研究生開設的一門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課程,自然辯證法的學科建設與教學改革要以馬克思主義學院建設標準作為前提依據。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前理事長吳啟迪在2017年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工作報告中指出,一些長期困擾我們事業發展的困難和問題,仍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主要是:以往的學科建制和學科發展定位面臨著新的挑戰,由此可能引發的學科危機、隊伍危機、生源危機、就業危機等,值得我們花大力氣給予關注......新時代新形勢下,自然辯證法的學科歸屬與未來發展需要我們重新反思、調整應對。
(一)學術規范與社會需求雙重作用下的“自然辯證法”
在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蓬勃發展的大好形勢下,在全國重點馬克思主義學院建設規范管理情勢下,作為理工農醫類研究生必修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課程之一的“自然辯證法”,其“哲學”學科建設難以契合馬克思主義學院建設的目標要求,馬克思主義學院體制下的“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師隊伍面臨學科與角色調整要求。
討論“自然辯證法”的學科歸屬,一般都從學科的歷史淵源與演進講起,需要尊重學科的歷史傳統與內在發展規律,把握學科的“范式”性質。但是學科歸屬顯然不是由學科自身決定的,定位要在社會中尋求承認,沒有社會承認就沒有存在價值或定位模糊。在中國現行體制之下,每一門學科之所以成為學科,就是要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審定的學科目錄之下尋到自身位置,并且經過國家審定通過,這就是學科獲得的國家法定“戶口”“身份”,這才是合法存在和身份定位。我們對于自然辯證法的理解,不再僅僅是哲學意義上的自然觀和方法論,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學科歸屬要更好地適應“新時代”社會需求
把自然辯證法定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或者說把科學技術哲學確立為哲學一級學科下屬的二級學科,把自然辯證法(科學技術哲學)當作哲學學科來建設,這從學科內在屬性、學科建設規范以及當時學科發展建設態勢來看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學科歸屬不是一成不變的,它要適應學科發展與社會需求變化。正像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2005年12月《關于調整增設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及所屬二級學科的通知》所說: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和《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精神,為了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研究、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推進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和鞏固馬克思主義在高等學校教育教學中的指導地位,加強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培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隊伍,經專家論證,決定在《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中增設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及所屬二級學科。可見,學科調整不但要符合學科發展內在稟賦、屬性要求,更要適應國家社會發展需求,這可以作為我國學科歸屬調整的基本原則。
于光遠教授講,中國自然辯證法就是一個“大口袋”,什么都能往里裝。但是“自然辯證法”與“科學技術哲學”是兩種不同價值取向和研究方法傳統,在現實發展中隱含著矛盾和沖突,到一定發展階段這種矛盾沖突就會產生。清華大學劉立教授主張把自然辯證法分為兩部分,“科學技術哲學”部分保留在哲學學科,“自然辯證法”爭取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這從中國自然辯證法的現實存在來看,還是有一定依據的。
(三)“自然辯證法”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性質要求
郭貴春教授主編的教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配套用書《自然辯證法概論》的緒論開篇就講:“自然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關于自然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學技術與人類社會相互作用的理論體系,是對以科學技術為中介的人與自然、社會的相互關系的概括、總結。自然辯證法就是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15]自然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不僅是專家學者的觀點,更代表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教材權威部門的審定、認可。
自然辯證法在中國的引進和創立進程,不同于一般學科發展走過的道路,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發揮了一般哲學學科所不具備的社會政治功能。將“自然辯證法”更名為“科學技術哲學”,強化了其科學性和學科規范。過去我們總講與國際接軌,但是對外交流、接軌應該是一個雙向過程,必須堅持我們自己的學科特色。自然辯證法是一個中國特色非常鮮明的學科,這是它的優勢所在而非弱點。正像曾國屏教授等人所說:“中國的自然辯證法,作為馬克思主22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6卷義自然辯證法中國化的重要成果,是頗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一個學科。”
五、結語
馬克思贊成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研究,與其具有相同的自然觀。辯證法不僅是歷史辯證法適用于人類社會,自然界同樣遵循矛盾的對立統一辯證發展規律。自然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辯證法的學科歸屬基于學科歷史發展的自身認識,更要適應新時代的社會發展需求。中國自然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成果,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科,我們要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中尋求學科歸屬與未來發展。“為國服務”是自然辯證法的優良傳統,曾經獲得國家大力支持,也發揮了重要社會功能。以“自然辯證法”作為學科名稱具有中國特色的獨到優勢,在這面旗幟下可以匯聚更廣泛的各方力量。自然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中堅實扎根,堅持為國家服務的基本方向,未來發展前景十分廣闊。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注自然科學研究最新發展成果,馬克思主義理論建立在扎實的科學研究成果基礎之上,這為我們推進自然辯證法事業發展,特別是探討自然辯證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提供了重要啟示。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