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代9帝的5座陵寢中,除乾陵、顯陵2陵因考古工作不足、陵寢建制不齊備外,從祖陵、懷陵和慶陵的陵址卜選原則、陵寢朝向、陵園結構與建筑布局、地宮形制及崇尚厚葬的喪葬習俗來看,遼代自“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政策出臺后,陵寢制度建設也經歷了從借鑒學習、逐漸發展到有所創新的完善過程。遼代喪葬文化在對中原文化兼容并包的同時,也堅守著游牧民族的諸多特點,促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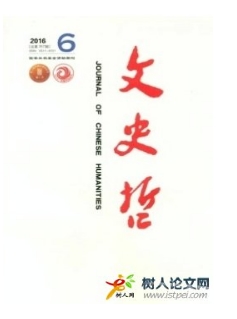
《文史哲》作為一家學術名刊,至今在同類刊物中仍然保持著三項殊榮,創刊最早,發行量最大,出口量最多,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這家以扶植小人物,延攬大學者而知名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一向以學術為本位,以創新為生命不斷發掘新的選題,展開新的爭鳴,受到國內外讀者,作者的高度關注及好評。
陵寢,或稱陵墓,是墓葬的一種,在中國古代專指帝王的墓葬。人類將死者的尸體或尸體的殘余按一定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場所,稱為“葬”。用以放置尸體或其殘余的固定設施,稱為“墓”。在中國考古學上,兩者合稱為“墓葬”。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的內容,物質層面的主要指陵園地面建筑、玄宮建筑以及神像生、碑刻等附屬設施,精神層面的探討,則應包括墓地選址規劃、葬式、陵園布局和玄宮結構所折射出的思想觀念等[1]。
契丹自北魏末年出現在史書記載之中,就與中原漢人有著廣泛的接觸。耶律阿保機完成統一北方諸部的使命后,“以兵經略方內,禮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晉圖書、禮器而北,然后制度漸以修舉”[2]。尤其是遼太宗耶律德光以中原王朝為取向的皇權與禮制建設就已廣泛開始,陵寢制度亦列其中。
遼代的9任皇帝中,除第四任穆宗耶律璟死后附葬懷陵、末帝天祚帝耶律延禧客死于金,后歸葬于廣寧府閭陽縣乾陵旁,陵寢建制不齊備外,其余幾位皇帝均有自己規整、獨立的陵寢。太祖耶律阿保機葬祖陵(巴林左旗哈達英格石房子林場的山谷中),太宗耶律德光和穆宗耶律璟葬懷陵(巴林右旗床金溝山谷中),圣宗耶律隆緒、興宗耶律宗真和道宗耶律弘基葬慶陵(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蘇木以北),此3陵皆位于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依據文獻記載,東丹人皇王耶律倍和其子世宗耶律兀欲葬顯陵,天祚帝耶律延禧葬乾陵,目前考古工作僅知2陵位于遼寧省北鎮醫巫閭山董家墳、龍崗村一帶的山谷中,具體坐標不詳。自太祖“省風俗”“定吉兇儀”以來,遼代陵寢制度經歷了借鑒學習、逐漸發展、有所創新的完善過程,我們可以通過皇陵建置一窺遼代陵寢制度及其特點之全面。
一、陵址卜選原則與主導因素
在君權至上的中國封建社會,皇帝的生死關系著整個朝代的盛衰更迭和國家社稷的安危成敗。作為帝王死后“萬年壽域”的陵寢建筑與制度,是與中國古代帝王及君主專制制度相伴而生的產物。對于帝陵的選址,務求審慎周密,順應自然,需考慮風水因素、地理因素、政治因素和禮制因素,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決定因素有所不同[3],遼陵的卜選亦同。
(一)依山為陵
唐宋時期,受風水堪輿術興盛的影響,葬地選擇除繼承漢代陰陽五行學說和天人感應諸法之外,也十分講究墓穴的方位、向背、排列位置等,在葬式、隨葬品、墓地選擇和地面建筑等方面也有特定要求。
遼代帝陵多在東、南或東南方向三面環山,前臨溪流,群峰環繞,林木繁茂,陵寢位于口袋形的山谷之中,僅在陵園入口處留一陵門。這一陵園選址標準,除去帝王個人喜好因素外,一方面沿襲了唐陵因山為陵的舊制,另一方面,也與中國傳統堪輿理論中“遠望柱天,近視入泉,草木長大,土色肥潤”上吉之地的墓地選址標準極為契合。“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4]的契丹人,在建國前仍奉行“死不墓”的喪葬習俗,對死后葬所的講求,明顯是受到了中原山陵文化的直接影響。
(二)“陵山之祭”的濫觴
唐代太宗親自定壽陵于九嵕山,鑿山穿穴,以營寢宮,其目的一是為了節儉,二是為了利用山岳雄偉形勢,體現帝王的宏大氣魄,三是為了防止盜墓,達到令奸盜息心的目的[5]。而遼代皇陵皆選大山的原因,除了因為從漢族知識分子之議改革契丹喪葬舊俗,陵寢制度仿漢制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則是緣于契丹族的祭山行為。契丹人信奉薩滿教,認為山岳為民族發源之地與死后靈魂的歸宿之地,是保佑本民族生存繁衍、死后魂歸天國的現實生活和超現實生活命運的主宰。在遼代,祭山儀被視為吉禮之一,神職人員、禮官以及群臣分工明確,組織有序,已形成一套完備的制度。
遼代所祭之山以木葉山和黑山為主。經考證,木葉山即為現在巴林左旗境內的漫歧嘎山。①黑山隔黑河與慶云山相對[6],被契丹族認為是死后魂歸之處,“即幽界黃泉之山,有黃泉神,死者居住其地”[7]。而遼代皇陵中,祖陵座落于木葉山上,慶州3陵的陵名與山名并出,巴林諸陵中,祖陵在黑山東南,懷陵在其南偏東,慶陵在其西偏北,木葉、黑山二山的地位,可與后代“陵山”相媲。
契丹人這種將帝陵選址與崇山之俗相結合的做法,在金代得到了延續,典型的例子就是金陵選址大房山并封大房山為“保陵公”:“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敕封山陵地大房山神為保陵公,冕八旒,服七章,圭、冊、香、幣,使副使持節行禮,并如冊長白山之儀。……是后,遣使山陵行禮畢,山陵官以一獻禮致奠。”[8]
金人因對山神的崇拜而在皇陵所在的大房山設神祭奠的做法,和契丹具有一定的師承關系,但最終將向皇陵所在山脈行祭享之禮確定為國家祭祀大典、實行“陵山之祭”制度的是在明代[9]。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明世宗諭內閣:“文皇帝既封黃土山為(天)壽山,今又擬顯陵為純德山,而獨鐘山如故,于理未妄(妥),朕惟祖陵宜曰基運山、皇陵宜曰翔圣山、孝陵宜曰神烈山,并方澤從祀。以基運、翔圣、天壽山之神設于五岳之前,神烈、純德山之神位次于五鎮之序。”[10]是為皇陵所依之山正式命名并行祭祀之始,此后清陵完全照搬了這一制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契丹人的祭山儀,或可稱為明代“陵山之祭”的濫觴,以契丹為代表的北方少數民族對中原王朝的陵寢制度與禮制建設進行了有益的補充與完善。
(三)預營壽陵和死后建陵
《周禮·天官·大府》曰:“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在商周時期動用國家財政收入去辦天子的喪事,已經形成制度,并為后世所沿用。自秦漢以來,帝王即位后不久便為自己擇地建陵,相沿成制。唐代皇陵有預營壽陵和死后建陵兩種形式。唐太宗李世民和文德皇后長孫氏合葬的昭陵是預營壽陵的代表,除昭陵外,玄宗的泰陵陵址亦為玄宗生前預選。死后建陵的代表是高祖的獻陵。高祖李淵遺詔:“既殯之后,……園陵制度,務從儉約。”[11]太宗李世民聽從朝臣的建議,以東漢光武帝原陵之制修筑獻陵,并于貞觀九年(635年)十月,葬高宗于獻陵。北宋皇陵制度比漢唐簡易,諸陵中除宋太祖的永昌陵是生前選定陵址外,其余皇帝生前不再預造壽陵。
遼代皇陵的選址,也有兩種形式。一為死后建陵,如祖陵。天顯元年(926年),阿保機病死于征渤海后西歸的途中,天子死后安身之所尚未完工,只得權殯于“子城西北”,由述律后主持陵墓營建工作。天顯二年(927年)八月,“治祖陵畢”,“葬太祖皇帝于祖陵,置祖州天城軍節度使以奉陵寢”[12]。慶陵的建造緣于圣宗在捺缽途中,因其愛慕慶云山的風景秀麗,于是立下“吾萬歲后,當葬此”欽命,由“興宗遵(圣宗)遺命,建永慶陵”[13],“興宗崩,道宗親擇地以葬”[14],與唐泰陵和宋代永昌陵的選址過程如出一轍,但陵寢的建造則是在圣宗、興宗崩后所為,與泰陵有所不同。二為預營壽陵,如乾陵。據《遼史》記載,乾亨二年(980年)“五月,雷火乾陵松”[15],是時景宗未崩,說明乾陵是在景宗在世時就開始修建的。
綜觀遼代帝陵的選址與修建過程,從太祖死后述律平匆忙主持祖陵的營建,到景宗生前預營壽陵,再到圣宗是生前選定陵址、崩后再行營建之事,一方面體現著遼代陵寢制度因襲唐制并有所完善,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中原腹地的漢人與契丹民族在陵寢文化方面的互動:遼代陵寢卜選承襲了唐代的兩種形制,而北宋諸陵中僅有永昌陵預營壽陵的做法,使得遼陵的修建過程愈顯其過渡性。
(四)血緣關系衍生出的派系之分
在中國古代,皇陵的選址除考慮風水因素外,地理、政治和禮制因素皆在考慮之列。其中政治因素對皇陵卜選的影響是偶然的,主要受眾為某些特殊人物。遼陵卜選的依據,除去帝王愛憎之外,政治因素占據主導地位。而與中原不同的是,這種政治因素主要表現在血緣關系衍生出的派系之分。
遼太祖葬祖陵,太宗葬懷陵,與太宗爭位的東丹王耶律倍死后被葬于醫巫閭山下,其長子兀欲繼位后,追“謚讓國皇帝,陵曰顯陵”[16]。世宗出于東丹王系,穆宗則為太宗系,他們死后,分別葬于顯陵和懷陵,都與其父合用一個陵園。從景宗開始,東丹王一系徹底打敗了太宗系,此后兵權完全由這一系獨攬。景宗死后,葬于顯陵附近的乾陵。雖不在同一陵,卻同處一個陵域。天祚帝盡管客死異鄉,但也是被安葬在了乾陵里。由于圣宗對慶陵所在的山水分外迷戀,因此,他死后,便在這里修建了宏大的慶陵陵園。其子、孫興宗和道宗,死后也長眠于此。由此可見,遼代諸帝因血緣上的差別而衍生出來的派系區分,也涇渭分明地反映在了陵墓布局上。
二、“以東為尊”與“東向拜日”的流變
遼俗東向而尚左,在禮儀交往、神靈祭祀、房屋建筑等方面,契丹族皆奉行以東為尊、東向為吉的觀念,史籍中多有記載。如《契丹國志·太祖紀》載遼上京“其城與宮殿之正門,皆東向辟之”,《續資治通鑒長編》天禧五年九月甲申條引宋綬《契丹風俗》云“祭天之地,東向設氈屋,署曰省方殿”,《新五代史·四夷附錄》載“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等等。
遼人這種尚左、以東為尊的觀念,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了遼代帝陵的朝向,在遼代契丹貴族家族墓地的排列方式上也有反映,如統和三年(985年)韓德昌葬于“渠劣山之陽先王塋之右”[17],重熙二年(1033年)蕭琳葬于“青山之左”[18],天慶二年(1112年)蕭義“葬于遼川之右,圣跡山陽”[19],諸如此類。
遼代東向為尊習俗的產生,一是緣于太陽崇拜。在遼代,契丹人通常是將拜日和祭天聯系在一起的。在軍隊出征或回師時,均祭天和拜日,如《遼史·兵衛志》載:“凡舉兵,帝率蕃漢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諸陵及木葉山神,乃詔諸道征兵。”此外,在一些特殊的重大場合,如皇帝登基時所行柴冊儀及再生儀、皇后生辰儀、冬至朝賀儀以及臘儀等歲時節日,均有東向拜日的習俗。二是緣于獲得中原王朝文化認同的心理需求。在政治上一統北疆之地的契丹政權,在文化上同樣主張在其勢力所及之地實現統一,“以東為尊”的習俗體現了遼代統治者希望將政權納入中華正統文化框架之中的文化歸屬與認同需要。
同歷史上其它南北政權對峙存在的朝代一樣,在遼代,受“內諸夏而外夷狄”“夷不亂華”等正統觀念的影響,某些漢人把漢族看做中原王朝的正統繼承者,少數民族即使建立了政權,也不被視為正統。而契丹政權一直視自己為與北宋地位對等,在與宋朝的書信往來中,甚至彼此以兄弟相稱:“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大宋皇帝闕下:粵自世修歡契,時遣使軺,封圻殊兩國之名,方冊紀一家之美”[20],“雖境分二國,克保于歡和;而義若一家,共思于悠永”[21]。宋真宗死后,遼圣宗甚至對臣下說:“吾與兄皇未結好前,征伐各有勝負,泊約兄弟二十余年,兄皇升遐,況與吾同月生,年大兩歲,吾又得幾多時也?”下詔“燕京憫忠寺特置真宗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22]。清寧三年(1057年),遼道宗曾以《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進皇太后,力排以中原漢族為正統來區分“華夷”的偏見,稱遼王朝立國是“承天意”,不再承認被視為“蠻夷”的地位。
自耶律阿保機建元之始,隨著生產方式發生轉變,對中原封建文化的仰慕與吸納,以及對游牧民族原始、落后道德觀念的逐步擯棄,契丹族的道德觀念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在元朝之后,契丹已逐漸融于中華民族的母體之中,體現了中華多元一體的發展趨勢及契丹族華夷同風的社會面貌[23]。而且,隨著契丹人漢化程度的不斷加深,遼代原始的“東向拜日”儀式已漸由宗教文化、民間文化向制度文化轉變[24],后來甚至演變為“凡祭皆向東”的“國俗”。
必須指出的是,從目前遼代考古資料來看,史載所謂的契丹人以東向為尊,并非是純粹的正東向,而是東南向。經實地勘測,遼代帝陵的朝向為座西朝向東南:祖陵入口黑龍門位于祖山之東南,其神道位置與陵門朝向一致,均為東南走向,祖州城的東門“望京門”也是東南向;懷陵座西朝東,其祭殿的方向為東偏南20度;慶州位于慶陵東南25華里之處,顯陵、乾陵雖形制不詳,但就帝陵的朝向而言,不會有太大的偏差。1962年,內蒙古文物工作者在對遼上京遺址進行勘察時,發現上京城墻、城門、主要宮殿的門址也為東南向。遼代契丹人的墓葬,墓門絕大多數在東、南之間(95°-175°),絕少例外[25],只有極個別負責管理漢人的南面官例外,因為他們可以“從漢儀”。
可見,“貴日”“拜日”“祭東方”的契丹舊俗,既影響遼的地上居室,也影響了墓葬的擇向。在實際操作中,產生于游牧民族原始日月崇拜思想的“東向拜日”習俗,已流變為“取向東南”。
三、陵寢建置與建筑布局特點
遼陵地表建筑所存無已,難述陵寢建置與建筑布局其詳。因而只能選舉具有代表性的陵寢分布、陵垣標識、神道及石像生制度進行初步的論述。
(一)單一兆域,多座帝陵
遼代帝陵的5個陵區中,除祖陵僅葬太祖耶律阿保機外,其余諸陵區內均埋葬有不止一個皇帝。與宋代帝后同塋異穴的埋葬方式不同,遼代帝后合葬于同一座陵墓之中,也沒有出現宋陵中諸后陵合葬于一陵、不按輩份祔葬于先陵的現象。這一陵寢建置特點與唐和宋代諸陵皆有不同,可謂開啟了中國古代單一兆域、多座帝陵的先河,并為明清陵寢制度所借鑒。
遼代陵寢的另一重要特點,是在陵四周及山脈的低凹處皆筑石墻以護衛陵區,將陵園密封成一個獨立的文化地理單元。而且在陵區內,一般筑石墻以區分將陵寢兆域區分為不同的功能區。比如祖陵正穴南嶺西側的山脊上,有長達近200米的石墻4段,有近30處封堵豁口。這些豁口與祖陵陵園西側山脊的石墻呈“T”字形交匯,將整個陵園分成南、北兩塊,成為了主陵區和陪葬墓區的區分帶[26]。懷陵陵園中部也筑有一道石墻,將其分割為內、外兩個陵區,內陵區主要為陵墓和祭殿,外陵區有祭祀性建筑分布。
遼陵在陵園入口處,夯筑高大的陵門,并建有規模宏大的陵墓祭殿。祖陵陵門“黑龍門”由門道、墩臺、陵墻、慢道、涵道和高大的城樓建筑組成,門道南端的五面坡慢道與《營造法式》所載“五瓣蟬翅”慢道的形制極為相仿。而黑龍門的門道基礎建筑在規整的石地栿上面置木地栿,木地栿上開卯口,上插排叉柱,與漢唐宋中原地區都城城門和帝王陵陵門的門址模式既有聯系又有不同,開啟了遼代特有的建筑模式[27]。
(二)神道與石像生制度
中國古代帝王、官員的陵墓前自東漢開始多有石雕像陳設,稱“石像生”,也稱“翁仲”。從唐高宗乾陵開始,石像生陳設于陵冢以南的主神道兩側形成定制。唐、宋兩朝對于石像生制度有著嚴格的規定。
由于遼陵地面建筑所剩無已,遼代神道及石像生使用制度不詳。從考古發掘情況來看,僅知遼陵神道位置均呈東南走向,與陵門朝向一致,神道兩側有石像生,目前僅出土有1個石犬及2個石翁仲(其中一個殘損)。神道碑樹立在陵區外山谷中的東側山坡頂,現存大龜趺,陵區內的兩座小山頂,地表散布有兩座經幢的殘片。慶陵陵區內未見有碑刻的遺跡,僅在中陵前殘存有石經幢一具,有蓋、身、座3部分,幢身銘刻陀羅尼經文。
從契丹貴族墓葬來看,目前發現有石像生的僅有耶律琮一例,其具體形制為:墓前端正中樹立石碑一通,碑后置石羊2對,石虎1對,武吏1對,文官1對。墓地右側殘存有神道碑一通“故太師令公神道之碑”[28]。此外,河北平泉縣柳溪鄉石虎村現地表存有13件石像生,包括石虎5只,石羊4只,石猴2只(其中一只缺頭),石翁仲2尊(均殘缺頭部)[29]。平泉縣石羊石虎古墓群因未經正式發掘,墓主人身份不明、墓葬地下情況不詳,缺乏進一步研究的依據。
從目前發現的遼代陵寢及契丹大貴族墓葬來看,遼代石像生制度存在石像生加石碑以及僅有經幢兩種。僅有經幢者,如慶陵的永興陵,又如敖漢旗白塔子墓,出土有紀年為大康七年(1081年)的石幢。祖陵和耶律琮墓兼有石像生和石碑。因其它諸陵均未做過系統發掘,契丹皇帝及大貴族究竟采用何種石像生制度,難具其詳。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遼代葬制中采用漢制,用意在于體現“華夷同風”,象征著契丹族皇帝是中國之主宰,契丹貴族對漢族人同樣具有管轄權。
(三)上宮與下宮
唐、宋皇陵的祭祀場所有上宮和下宮之分,上宮之祭殿建于陵冢前,即獻殿,供奉神主,是上陵時舉行禮儀性祭典的處所;下宮距陵宮稍遠,供奉墓主畫像、衣冠,飲食起居如常日,二處的祭祀性質存在明顯的差異。契丹皇帝沿襲漢唐舊制,在皇陵陵區內要進行諸多的祭祀活動,最為主要的是廟前祭祖和寢宮之祭兩種。遼陵考古工作雖有待進一步深入,對于遼陵上、下宮的形制與位置尚需考證,但筆者以為,這兩種祭祀活動也應分別在遼代陵寢的上、下宮之內進行。
遼代諸陵的宗廟,史料中一般稱為“×殿”“××殿”,如《遼史·地理志》載:“太祖陵鑿山為殿,曰明殿。殿南嶺有膳堂,以備時祭。”此處所言之“明殿”即是祖陵之陵前宗廟,建在墓前,鑿山而建。祖陵首創遼陵前宗廟之先河,阿保機后之遼代諸帝,均建有陵前宗廟,懷陵的宗廟稱“崇元殿”,顯、乾二陵稱“凝神殿”,穆宗附葬懷陵,其宗廟稱“鳳凰殿”,圣、興、道3帝的陵廟分別稱為“望仙殿”“望圣殿”和“神儀殿”,這些殿址的具體位置均無從考證。從2008年對祖陵陵區內甲組建筑基址的J1和J2的發掘情況來看,調查者認為其分屬與祭祀有關的陵寢建筑遺址和供祭祀人員臨時下榻之所,這也成為遼代宗廟位于陵區之內的又一佐證。
除廟前祭祀外,遼陵內另一重要祭祀活動發生在遼代皇陵的寢宮,又稱下宮,即安放皇帝“御容”像和供在位皇帝及臣僚祭祀用的殿堂,一般位于奉陵邑的內城。《遼史·地理志》載,祖州“西北隅有內城。殿曰‘兩明,奉安祖考御容;曰‘二儀,以白金鑄太祖像;曰‘黑龍,曰‘清秘,各有太祖微時兵杖器物及服御皮毛之類,存之以示后嗣,使勿忘本”。此處所論述的4殿,即為遼陵的寢宮所在之處。從祖州、懷州和慶州城址的形制來看,3城的內城皆有祭祀性質建筑構件出土,由此得出“遼陵下宮位于奉陵邑的內城之內”的結論,當無大謬。
關于遼陵的下宮,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指出:“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于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如事生。”[30]認為遼陵的下宮為“明殿”,筆者以為有誤。首先,從“明殿”的位置來看,“太祖陵鑿山為殿,曰明殿”,作為“下宮”的明殿位于祖陵地宮不遠,這與中國古代帝陵下宮設置的通制不符;其次,從下宮的功能來看,除需“奉表起居如事生”外,作為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來的政權,列先祖服御、兵器等物以教子孫后代勿忘根本,也應成為下宮的重要功能之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地理志》所記“兩明”“二儀”“黑龍”及“清秘”4殿,因“各有太祖微時兵杖器物及服御皮毛之類”而更合乎這種要求。寢宮的類似功能,在唐陵中也能找到根源。唐陵寢宮除主要用于供奉墓主每日起居之外,還具有收藏先帝先后遺物的功能。唐代皇帝祭陵上寢宮,也有進殿省視先帝先后服御玩好之習俗。如貞觀十三年(639年),唐太宗謁獻陵,“入寢宮,執饌以薦,閱高祖及太穆后服御,悲感左右”[31]。又如“高力士于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嘆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余載,方致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32];第三,從禮制建設來看,唐代以后,寢宮之祭較之陵前祭祀活動更加受到重視,將教化子孫勿忘根本之物置于下宮,應當更合乎禮制建設的需要。由是觀之,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所指明殿即為下宮之制的說法未必有理。
四、事死如生,崇尚厚葬
厚葬是中國古代“事死如生”喪葬觀念的集中體現,在漢代被以制度的方式明確下來,主要表現為墓內隨葬的大量貴重實用物品或明器以及筑陵工程的浩大,遼陵亦是如此。
遼祖陵雖未被正式發掘,但是在陪葬墓M1中,仍清理出一些精美的隨葬品,包括金器、鎏金銀器、鎏金銅器、玻璃器、玉器、琥珀、鐵器、瓷器、陶器、石器等。遼中期厚葬之風愈烈,朝廷曾多次下令禁止厚葬,如圣宗“禁喪葬禮殺馬,及葬甲胄、金銀、器玩”[33],興宗詔“世選宰相、節度使族屬及身為節度使之家,許葬用銀器”[34]。但是遼代官僚死后,皇帝常命配給葬具儀物,乃至公主下嫁之日,就把“送終之具,至覆尸儀物”列在賞賜單中。內蒙古通遼市奈曼旗發現的陳國公主墓的3227件隨葬品中,不乏帶把玻璃杯、長頸玻璃瓶、乳釘紋玻璃盤等具有濃郁西亞風格的奢華隨葬品,由此可以想見遼代帝陵隨葬品的豐富程度。
總體上說,遼代陵寢制度在因襲唐陵舊制,借鑒宋陵卜選中的堪輿因素之外,還多有創新,一方面得益于契丹人兼容并包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也為豐富中國古代帝王陵寢制度做出了巨大貢獻,從而促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形成。
注 釋:
①關于遼代木葉山的位置,學界較有分歧,目前代表性說法有3種:傅樂煥、姜念思與馮永謙、楊樹森、韓國金在滿、日本松井等人,均著文認為遼代木葉山在潢河(今西拉木倫河)與土河(今老哈河)交匯處,《中國歷史地圖集》亦將木葉山定至西拉木倫河與老哈河交匯處,此為“兩河說”;張柏忠認為阿魯科爾沁旗天山鎮即為木葉山所在之處,此為“天山說”;趙評春、陳永志認為祖陵所在之漫其嘎山即為木葉山,此為“祖陵所在之山說”。筆者根據各文論述情況,認為“祖陵說”以考古學研究成果為主要依據,較有說服力,故取之。
參考文獻:
〔1〕〔3〕劉毅.中國古代陵墓[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
〔2〕〔4〕〔12〕〔13〕〔14〕〔15〕〔16〕〔33〕〔34〕脫脫.遼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1445,373,24,444,839,103,1211,142, 229.
〔5〕劉向陽.唐代帝王陵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6〕田廣林.說契丹黑山[J].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1985,(1).
〔7〕鳥居龍藏.契丹黑山黑嶺考[J].燕京學報,1940,(12).
〔8〕脫脫.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820.
〔9〕劉毅.明朝“陵山之祭”述論[J].故宮博物院院刊,1997,(2).
〔10〕明世宗實錄[M].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11〕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17〕〔18〕向南,張國慶,李宇峰.遼代石刻文續編[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0.
〔19〕向南.遼代石刻文編[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20〕〔21〕〔22〕葉隆禮.契丹國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91,195,73.
〔23〕武玉環.論契丹民族華夷同風的社會觀[J].史學集刊,1998,(1).
〔24〕楊忠謙.遼代的拜日風俗及文化解讀[J].民族文化論壇,2005,(2).
〔25〕彭善國.遼代契丹貴族喪葬習俗的考古學觀察[J].邊疆考古研究,2003,(1).
〔26〕董新林.遼代祖陵考古發掘取得重要收獲[N].中國文物報,2007-11-28.
〔2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第二工作隊,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代祖陵陵園黑龍門址和四號建筑基址[J].考古,2011,(1).
〔28〕李逸友.遼耶律琮墓石刻及神道碑銘.東北考古與歷史:第一輯[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29〕王燁.平泉縣石羊石虎古墓群調查[J].文物春秋,2006,(3).
〔30〕歐陽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898.
〔31〕歐陽修.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362.
〔32〕袁宏道點評,屠隆點閱.虞初志[M].北京:中國書店,1986.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