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也稱其為“知識所屬權”,指“權利人對其所創作的智力勞動成果所享有的財產權利”,一般只在有限時間期內有效。隨著經濟的發展,跨國知識產權也是知識產權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本文是一篇陜西論文發表范文,主要論述了跨國知識產權協議管轄問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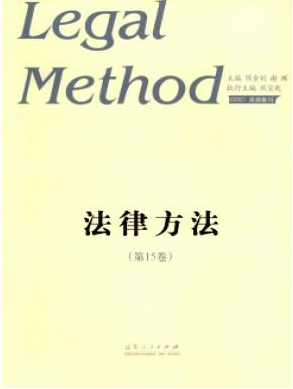
摘要:目前,中國就跨國知識產權協議管轄問題沒有專門立法,相關規定散見于《民訴法》及各類司法解釋中,沒有形成系統的立法體系,且內容上遠遠落后于世界水平。未來可以考慮出臺專門的司法解釋或在《民訴法》中專章規定,從形式、內容、具體要求等方面規制。此外立法時應注意公共政策原則的適用,為協議管轄戴上“緊箍咒”。
關鍵詞:跨國知識產權,協議管轄,中國立法,公共政策
目前國際上對于跨國知識產權協議管轄問題的研究已經相對較為成熟:美國法學會2007年制定并通過的《知識產權:跨國糾紛管轄權、法律選擇和判決原則》(簡稱《ALI原則》)、2010年日韓起草并通過的《知識產權國際私法原則》以及2011年歐洲馬克思朗普克知識產權沖突法小組公布的《知識產權沖突法原則》(簡稱《CLIP原則》)、1968年《民商事管轄權與外國判決執行公約》。相比而言,目前我國的研究多數是結合三大成果,提出一些籠統的建議,不利于實踐發展。本文將在目前已有成果的基礎上,著重探討我國相應制度建設的具體問題,進行針對性思考。
一、是否允許協議管轄
協議管轄有許多優點:當爭議發生時,當事人往往更傾向于本國法院進行管轄,如果立法允許協議管轄,至少給當事人一個自由選擇的空間。對此有學者認為,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之發達國家而言較弱,允許協議管轄可能會導致我國法院喪失很多管轄權。但筆者認為,這是一種典型的“受害者心態”,且不說中國未來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會有較大進步;單就當事人自身而言,中國也不乏可以利用自身談判能力和交易實力,確立有利于自身的管轄權規則的當事人;即使不能確定本國法院管轄,經過協商選擇一個相對中立的法院也并非難事;其可以提高確定性和可預見性,尤其是和協議確定法律適用結合在一起時,這種優點將更加明顯;另外,協議管轄也可以避免管轄權沖突、平行訴訟等較為棘手的問題。雖然阻力重重,但相對其具備的優點,協議管轄還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二、協議管轄的適用范圍
對于知識產權跨國糾紛,現實中主要包括兩大類:合同糾紛和侵權糾紛。即使我國承認協議管轄,也應僅限于合同糾紛。合同領域適用意思自治原則,目前基本上已達成非常廣泛的共識,鑒于其本身就是用來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利益,雙方當事人可以在簽訂知識產權合同時,約定相應的管轄權,這既符合目前的國際趨勢,又具有現實可操作性。但在侵權領域,由于侵權行為往往是單方面的,故事先很難達成“合意”;另外對比合同糾紛,侵權具有社會危害性,部分侵權行為甚至會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允許意思自治不利于公權力發揮作用,故在侵權領域不應規定協議管轄。
三、協議管轄的具體要求
對此我國可以參考三大原則的相關規定,在實質要件、形式要件、具體內容、默示協議等方面,進行統一規范。當然,這一切必須在本國強行規范允許的范圍內。
1.協議的形式。《民訴法》規定,管轄協議在形式上必須是書面的,其合理性、必要性都值得商榷:在1999年《合同法》施行前,我國立法與司法實踐均要求合同為書面,但《合同法》修改后,將其擴展到口頭或其他形式。而管轄協議,無論是單獨的文本,還是單一條款,其本質上都符合《合同法》第2條對“合同”的定義,故理應遵循新的《合同法》;更何況目前《民訴法》對于國內默示推定管轄的效力已經予以承認,為了避免國際社會誤解中國“寬內嚴外”,也不應強求涉外管轄協議必須采用書面形式。2005年6月30日,海牙國際私法會議通過的《選擇法院協議公約》明確規定:排他性選擇法院協議必須以書面或其他可以證明的形式訂立。這也反映了國際社會的態度。
2.約定的法院。對于約定的具體法院,現行立法要求“有實際聯系”,但究竟什么叫有“實際聯系”,立法卻未做明確說明,只是以簡單列舉的方式進行闡釋,然而有限列舉畢竟無法窮盡現實生活的各種情況。在具體認定上,是由當事人自行判定?還是由法院判定?亦或是根據《民訴法》第259條規定認為其規定不明而適用國內法規定?以上問題現行立法沒有加以說明,實踐中,往往由法官自由裁量。但不論如何裁量,法官都需本著保護當事人利益和維護國家主權和公共利益這一基本準則,既不能限制太多違背意思自治精神,又不能限制太少導致挑選法院。如何公允判斷、靈活裁量,是對法官自身素質和能力的考驗。從當代國際通行做法看,多數國家都不要求協議管轄的法院必須與爭議有實際聯系,1965年《海牙協議選擇法院公約》第15條規定:“任何締約國得保留對選擇法院協議不予承認的權利,如果爭端與所選擇法院并無聯系,或在具體情況下,由所選擇法院處理該爭端實屬嚴重不便。”由此可見,公約也進行了比較寬松的規定。
3.公共政策的約束。在允許協議管轄的同時,我們不能忘記給其上一個“緊箍咒”,即公共政策。在Bremenv.ZapataOff-shoreCo.(1972)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指出:“在聯邦海事訴訟中,選擇法院條款表面上應為有效,除非持反對意見的當事人能夠證明該條款不合理。”而在CarnivalCruisesLinesv.Shute(1991)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更是進一步確定選擇法院條款的例外——“違反公共政策”。
3.1公共政策的具體含義。在各國立法、國際條約中,公共政策的概念隨處可見,但若真要為其下一個準確的定義,卻極為困難。《布萊克法律詞典》中將其定義為:“是指不能有對公眾產生損害的趨勢或者違背公共利益的法律原則。在這一法律原則下,合同或者私的交易的自由要受到保護社會利益的法律的限制。‘政策’這個詞,當它用于法律、法規、法治、行為的過程等類似方面時,是指它可能的結果、趨勢目標必須要同時考慮到一國的社會或者政治利益。因此,除了違反法律和違反道德以外,當法律以其有危害傾向并且損害國家利益等理由拒絕承認與執行時,某些層面的行為就被認為是‘違反公共政策’。”通過這個表述,我們不難發現,這個所謂的“定義”是從其本身的特性出發進行闡釋,是對其功能的描述,而不是一個精準的定義。其實“公共政策”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靈活性,各國也往往利用其定義和理解上的模糊性,創造排除他國管轄權的空間,以保護自身的利益。
3.2公共政策在美國的應用。依據美國沖突法理論和實踐要求,“公共政策”主要體現在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具體而言: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必須滿足“充分可替代法院要件”,即案件至少存在一個完全可替代的法院。通常美國法院傾向于認定可替代的外國法院是“充分”的,即只要“被告能夠遵從另一法域的訴訟程序,則該外國法院即為充分可替代的法院”。但這一原則的適用,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外因素——公共政策。在美國,公共政策雖然沒有被明確列為不方便法院原則適用的排除因素,但實踐中,較低級別的法院在審理反托拉斯法、證券法、環境保護法以及勞工法案件時,往往會加以適用。因此,美國的當事人在確立協議管轄時,必須充分注意因公共政策而導致選擇的法院成為不方便法院的風險。
3.3我國應該如何借鑒。鑒于公共政策本身就是一個較為模糊的含義,因此我國法院在適用時,可以根據自身的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自由裁量,靈活適用,必要時可以適當借鑒國內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則,把公共政策例外作為“兜底條款”,一旦當事人惡意選擇外國法院進行管轄,損害我國重大公共利益,這個“緊箍咒”就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陜西法律類論文投稿期刊推薦:《法律方法》是山東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山東大學法律方法論研究中心”主辦,2002年由陳金釗、謝暉教授創辦的法律方法專業研究集刊。《法律方法》本刊迄今已經出版了11卷,在學界法律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重要影響,本刊論文已經在人大復印資料轉載近10篇,2007年入選CSSCI集刊。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