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家論”是一種將作家特點(diǎn)和個(gè)人經(jīng)歷與時(shí)代背景相結(jié)合,對作家心理進(jìn)行分析的文學(xué)批評方式。但以往的研究多為主觀的文學(xué)評論或話語分析,依賴于研究者的評定。因此本文提出利用生態(tài)化識別方法,預(yù)測金庸小說中人物的人格分?jǐn)?shù),進(jìn)行比較分析。按照文學(xué)界統(tǒng)一的分類將金庸小說分為俠階段,非俠階段和反俠階段。結(jié)果顯示:不同階段小說人物的盡責(zé)性和開放性存在顯著差異,非俠階段人物盡責(zé)性最低,反俠階段人物開放性最高,其他維度不存在顯著差異。研究結(jié)果發(fā)現(xiàn)了金庸在不同創(chuàng)作階段文風(fēng)和文學(xué)意圖的變化,驗(yàn)證了金學(xué)家提出的“金庸小說一致體現(xiàn)了樂觀開朗的俠義精神”的觀點(diǎn)。
關(guān)鍵詞 作家論;金庸;人格;生態(tài)化識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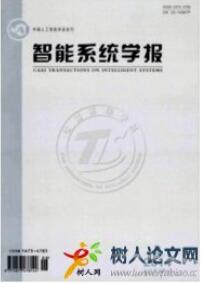
1 引言
文學(xué)作品不僅能夠反映作者的寫作風(fēng)格,同時(shí)其內(nèi)容也折射出作者的心理狀態(tài)(楊吉力,1997)。基于此,茅盾先生提出了“作家論”的文學(xué)批評方式,即通過將作家特點(diǎn)和經(jīng)歷(吳浪平,別睿, 2010)與時(shí)代背景相結(jié)合的方法,對作家創(chuàng)作心理進(jìn)行分析。利用“作家論”的視角來批評分析文學(xué)作品,可以推斷出作家的風(fēng)格特點(diǎn)、情感矛盾,以及他們對現(xiàn)實(shí)生活的解讀(楊健民,1983)。例如,茅盾(1993)在閱讀魯迅的文集(《吶喊》《彷徨》《華蓋集》)之后,對這個(gè)從未謀面的文學(xué)巨匠產(chǎn)生了“老孩子”的印象。也正是因?yàn)轸斞冈趯懽鲿r(shí)不由自主地將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表露在小說人物的經(jīng)歷和對白中,才賦予了阿Q、祥林嫂、閏土等小說人物生命力,從而成為經(jīng)典的藝術(shù)形象。“作家論”這一文學(xué)批評方式的出現(xiàn),使得利用小說人物的性格來窺探作家的風(fēng)格偏好和文學(xué)目的成為文藝研究的重要主題。
目前學(xué)界對小說人物的性格分析主要有兩個(gè)思路:定性研究和話語分析。定性研究,即依據(jù)研究者的人文素養(yǎng)和對小說文本的閱讀體驗(yàn),從微觀方面將小說中的一個(gè)或多個(gè)人物的性格概括為主要的幾個(gè)方面,然后對這幾個(gè)方面的性格特點(diǎn)用文本中的有關(guān)描寫進(jìn)行佐證,在宏觀層面進(jìn)一步歸納同一作者筆下小說人物的性格特點(diǎn)(包桂英, 2013),這同時(shí)也是文藝界主流的分析思路。如曹正文(1995),馮其庸(2014),嚴(yán)家炎(1991)和陳墨(2014)對《書劍恩仇錄》《笑傲江湖》等金庸作品中的小說人物進(jìn)行了人格和性格分析,并結(jié)合金庸小說中的歷史背景和金庸先生所生活的時(shí)代特征,進(jìn)一步剖析了小說人物的形象,印證了金庸的文學(xué)意圖和理想情操,展現(xiàn)了金庸先生在中華歷史、文化、民俗等研究方向的深厚功底,充實(shí)了讀者對于小說人物和金庸本人的理解認(rèn)識。
話語分析不同于定性研究,其思路是從語言學(xué)的角度出發(fā),通過選取若干段小說中的對話進(jìn)行語用原則、話輪轉(zhuǎn)換或其他會話分析(郭麗, 2014)。另外,還可以通過語料庫對人物語言用詞進(jìn)行統(tǒng)計(jì)(隋曉蕾, 2007),得出頻率較高的詞作為關(guān)鍵詞,以關(guān)鍵詞分析人物性格。
但是歸根結(jié)底,批評家對作品的藝術(shù)體驗(yàn)都是相對來說比較主觀的,容易受到個(gè)人主觀經(jīng)驗(yàn)的影響,從而造成個(gè)體差異。與此同時(shí),將主觀體驗(yàn)文字化后得到的批評作品,其客觀性也有待商榷。更重要的是,相比于描述繁雜的性格而言,人格作為一種穩(wěn)定的心理特征(McAdams, & Pals, 2006)能夠更好地描述并傳達(dá)小說人物的心理狀態(tài)(吳育鋒,吳勝濤,朱廷劭,劉洪飛,焦冬冬, 2018),為分析作家心理提供可靠依據(jù)。
基于此,本文提出利用人工智能中生態(tài)化識別(Liu,Xue,Zhao,Wang,Jiao, & Zhu, 2018)的方法,計(jì)算出金庸15部小說中人物的人格分?jǐn)?shù),研究小說人物心理特征的差異,以及金庸的寫作風(fēng)格、文學(xué)意圖、心理活動等與時(shí)間變遷的關(guān)系。該方法通過對小說人物進(jìn)行客觀量化的心理分析,實(shí)現(xiàn)對作家創(chuàng)作心理的研究,充分發(fā)揚(yáng)作家論批評方法的指導(dǎo)思想,為文學(xué)批評技術(shù)提供新的思路。
2 方法
2.1 人物選取
本研究選取金庸的15部小說:《白馬嘯西風(fēng)》、《碧血劍》、《飛狐外傳》、《連城訣》、《鹿鼎記》、《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書劍恩仇錄》、《天龍八部》、《俠客行》、《笑傲江湖》、《雪山飛狐》、《倚天屠龍記》、《鴛鴦刀》和《越女劍》作為實(shí)驗(yàn)材料,這15部小說包含1427位小說人物,共8756864字。
為了避免篇幅過短對小說人物人格差異的潛在影響,本研究將金庸短篇小說中的人物從數(shù)據(jù)庫中移除,其中包括:《雪山飛狐》、《白馬嘯西風(fēng)》、《鴛鴦刀》和《越女劍》。此后,統(tǒng)計(jì)剩下小說中全部人物的對話句數(shù),并進(jìn)行降序處理,選取參與對話數(shù)目多于或等于50句的小說人物,保證數(shù)據(jù)分析的充足性,最終,115位小說人物,共計(jì)18611句對白成為了最終的實(shí)驗(yàn)樣本。
根據(jù)金庸小說創(chuàng)作的三個(gè)典型階段:俠階段,非俠階段和反俠階段(陳墨, 2014; 高慶, 2014; 胡錦江, 2013; 劉洋, 2015; 嚴(yán)家炎, 1998),將115位人物劃分為三組,如表1所示。
2.2 文本分析及心理特征預(yù)測
本研究采用由中國科學(xué)院心理研究所計(jì)算網(wǎng)絡(luò)心理實(shí)驗(yàn)室研發(fā)的“文心”中文心理分析系統(tǒng)(Text Mind)進(jìn)行對話分析和人格預(yù)測。該系統(tǒng)分成三個(gè)部分,即中文分詞工具、心理分析詞典和人格預(yù)測模型。
中文分詞工具是基于哈爾濱工業(yè)大學(xué)研發(fā)的“語言技術(shù)平臺”(LTP)的軟件(Liu et al, 2018),利用切分詞序列等技術(shù)使得計(jì)算機(jī)能夠分析自然語言。心理分析詞典是中國科學(xué)院心理研究所參照“語言探索與字詞計(jì)數(shù)”詞典(LIWC)開發(fā)的“簡體中文LIWC詞典” (Zhao,Jiao, Bai, & Zhu, 2016),能夠量化分析心理學(xué)類的詞語。人格測驗(yàn)預(yù)測模型是中國科學(xué)院心理研究所計(jì)算網(wǎng)絡(luò)心理實(shí)驗(yàn)室基于新媒體大數(shù)據(jù)和深度學(xué)習(xí)技術(shù)為進(jìn)行網(wǎng)絡(luò)心理的研究而研發(fā)的工具(Li,Li,Hao,Guan, & Zhu, 2014; Liu et al, 2018)。
“文心”中文心理分析系統(tǒng)(Text Mind)工作流程:首先,利用中文分詞工具將115位小說人物的對話語句分割為獨(dú)立的、有語言學(xué)標(biāo)注(例如:動詞、名詞、狀語、賓語等)的詞語 (Liu,Che, & Li, 2011)。然后,利用簡體中文LIWC詞典(Zhao,Jiao, Bai, & Zhu, 2016)進(jìn)行特征提取。最后,將每個(gè)小說人物提取得到的特征送往大五人格預(yù)測模型進(jìn)行計(jì)算,從而完成將語言詞匯量化為大五人格分?jǐn)?shù)的過程。
3 結(jié)果
本研究采用 “大五人格”模型,其中包括宜人性、盡責(zé)性、外向性、開放性和情緒性五個(gè)人格傾向。
利用文心系統(tǒng)計(jì)算小說人物的大五人格預(yù)測分?jǐn)?shù),該分?jǐn)?shù)為標(biāo)準(zhǔn)化的分?jǐn)?shù),每個(gè)維度的分?jǐn)?shù)范圍為1~100,越接近兩端代表某個(gè)角色在某個(gè)維度上的傾向越高或越低。以金庸小說創(chuàng)作的階段作為分組變量,對大五人格進(jìn)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jié)果如表2所示。
結(jié)果顯示,三個(gè)階段在盡責(zé)性(F(2,112)=7.73,p<0.05)和開放性(F(2,112)=7.44,p<0.05)上存在顯著差異,在宜人性,外向性和情緒性上均不存在顯著差異。
利用LSD多重比較對盡責(zé)性進(jìn)行事后檢驗(yàn),結(jié)果顯示,非俠階段的盡責(zé)性(M=39.14)顯著低于俠階段(M=46.27,p<0.05)和反俠階段(M=44.79,p<0.05),即相較于俠階段和反俠階段,非俠階段的小說人物可能更多地表現(xiàn)出缺乏條理等低盡責(zé)性的特征。
利用LSD多重比較對開放性進(jìn)行事后檢驗(yàn),結(jié)果顯示,反俠階段的開放性(M=71.06)顯著高于俠階段(M=60.34,p<0.05)和非俠階段(M=65.34,p<0.05),即相較于俠階段和非俠階段,反俠階段的小說人物更具有獨(dú)創(chuàng)性,易于接受新的思想,對不同的事物保持好奇。
4 討論
本研究采用學(xué)術(shù)界廣泛應(yīng)用的“大五人格”模型,其中包括宜人性、盡責(zé)性、外向性、開放性和情緒性五個(gè)人格傾向(Goldberg,1993)。研究表明大五人格模型具有較高的可靠性和拓展性(Hahn,Gottschling, & Spinath, 2012)。更重要的是,大五人格模型建立在語言學(xué)的基礎(chǔ)上 (Goldberg,1993; McAdams,& Pals, 2006),為研究利用分類詞語從而給出大五人格分?jǐn)?shù)的人工智能技術(shù)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
利用生態(tài)化識別得到金庸不同階段小說中人物的大五人格分?jǐn)?shù),進(jìn)行方差分析發(fā)現(xiàn):不同創(chuàng)作階段小說人物的盡責(zé)性和開放性存在顯著差異,非俠階段小說人物的盡責(zé)性最低,反俠階段小說人物的開放性最高;在宜人性、外向性和情緒性維度不存在顯著差異。
隨著創(chuàng)作階段的推進(jìn),非俠階段小說人物的盡責(zé)性顯著低于俠階段和反俠階段,也就是說非俠階段的小說人物表現(xiàn)出不守陳規(guī)且計(jì)劃性、責(zé)任性不強(qiáng)的特點(diǎn)(DeYoung,Quilty, & Peterson, 2007),俠階段和反俠階段人物都表現(xiàn)出了相對來說較高的盡責(zé)性。研究表明,非俠階段是金庸文學(xué)生涯的分水嶺和多產(chǎn)期,在描繪重要小說人物時(shí),其文學(xué)風(fēng)格、意圖和思想感情等與在俠階段和反俠階段的小說人物有突出的不同點(diǎn)。具體而言,金庸在非俠階段的寫作風(fēng)格著重突出了追求自由、實(shí)現(xiàn)自我的道家思想。俠階段的英雄人物普遍歸為儒家之俠,以此歌頌他們?yōu)閲鵀槊瘛⒉黄埶嚼膫b義品質(zhì),而非俠階段的英雄人物,如楊過、胡斐等被譽(yù)為道家之俠,突出他們追求自由、實(shí)現(xiàn)自我的性格特點(diǎn)。在反俠階段,盡管金庸著力將韋小寶描寫為一個(gè)小人形象,卻同時(shí)突出了康熙、茅十八、陳近南等為國為民的儒俠形象,這也是反俠階段小說人物盡責(zé)性更高的原因。這些小說人物人格變化,在無形中體現(xiàn)了金庸試圖革新武俠小說的文學(xué)意圖(陳墨, 2014)。其在俠階段和反俠階段創(chuàng)作遵循傳統(tǒng)武俠小說套路,將許多小說人物設(shè)定為儒俠,描繪了他們?yōu)閲鵀槊竦拿褡逵⑿蹥飧牛@是一種傳統(tǒng)的武俠形象,沿襲了五四文化運(yùn)動新興的寫實(shí)主義風(fēng)格。基于此,金庸在不同時(shí)期都創(chuàng)作出了真實(shí)可敬的大俠形象,使他躋身于優(yōu)秀武俠小說家行列。
除此以外,不同階段小說人物的開放性也存在顯著差異,反俠階段的開放性顯著高于俠階段和非俠階段。在大五人格中,開放性與創(chuàng)新能力、熱愛自然和藝術(shù)審美聯(lián)系在一起。結(jié)合時(shí)代背景,以1969年創(chuàng)作的《鹿鼎記》為例,主人公韋小寶作為一個(gè)“真小人”,以他那一套流氓潑皮的生存邏輯,在儒家傳統(tǒng)公認(rèn)的盛世里飛黃騰達(dá)、創(chuàng)造歷史,他可以給顧炎武、黃宗羲等文人雅士出主意,敢在洪教主、陳近南、九難等武功卓絕的人面前信口開河,能幫索額圖、 康親王甚至康熙皇帝排憂解難、屢立奇功,使諸多武林好漢、碩學(xué)鴻儒相形見絀(羅麒, 2009)。結(jié)合創(chuàng)作時(shí)期可知,由于當(dāng)時(shí)正值文化大革命,受到多種文化潮流,以及時(shí)代大背景下破“舊”迎“新”的思潮影響,作者將革新創(chuàng)造的力量和優(yōu)良的藝術(shù)審美特性展現(xiàn)在了小說人物的身上。
除了盡責(zé)性和開放性之外,外向性、宜人性和情緒性的大五人格得分在不同階段不存在顯著差異。這一研究結(jié)果支持了陳墨(2014)和馮其庸(2014)提出的金庸小說人物形象的統(tǒng)一性,即書中正派俠客甚至是反派角色表現(xiàn)的俠義、仁愛、正義感、保衛(wèi)弱者的核心人格特點(diǎn)貫穿了三個(gè)創(chuàng)作階段,這是金庸武俠小說的創(chuàng)作基礎(chǔ),同時(shí)也是其小說備受追捧,深受好評的重要因素。
除此以外,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選取的115位小說人物中,83位為男性人物,32位為女性人物,這從某個(gè)方面也反映了金庸小說男性本位的特點(diǎn),值得在后續(xù)研究中繼續(xù)進(jìn)行深入探索。
總體而言,本研究發(fā)現(xiàn)金庸在俠階段的文學(xué)風(fēng)格是古典武俠文學(xué)和五四寫實(shí)主義的有機(jī)結(jié)合,這一特點(diǎn)為其贏得了忠實(shí)的簇?fù)碚撸蛊湓谖鋫b小說界占有一席之地。在非俠階段,金庸革新武俠小說文體,加入西方游俠文學(xué)推崇的自我實(shí)現(xiàn)、追求自由的俠客精神,側(cè)重點(diǎn)從“儒俠”轉(zhuǎn)為“道俠”,從實(shí)現(xiàn)民族大義轉(zhuǎn)為關(guān)注自身的個(gè)性發(fā)展,這一寫作風(fēng)格將金庸的作品從文體和內(nèi)容上與其他武俠小說作品區(qū)分開來,奠定了其武俠巨匠不可撼動的文學(xué)地位。在反俠階段,受到新思潮的影響,金庸對藝術(shù)審美和自然感受的要求提高,以明末清初作為歷史背景,用諷刺寫實(shí)主義的手法描繪了一個(gè)小人物在眾強(qiáng)權(quán)勢力中求生存的故事,不僅折射了大俠的為國為民、可歌可泣,也拓展了其作品的文學(xué)體裁,使金庸成為了真正意義的文學(xué)大師,而不僅僅是武俠小說巨匠。至此,我們也對金庸作品可以活躍在每個(gè)時(shí)期的原因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即金庸先生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的不斷革新與小說中各類充滿俠義精神的人物是受讀者歡迎的根本。
推薦閱讀:《智能系統(tǒng)學(xué)報(bào)》已于2006年3月正式出刊,雙月刊。是由中國人工智能學(xué)會和哈爾濱工程大學(xué)聯(lián)合主辦,是中國人工智能學(xué)會會刊之一。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