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具身認(rèn)知緣起于哲學(xué)界對“身心二元論”的批判反思,隨著梅洛龐蒂將其具身認(rèn)知思想發(fā)展為知覺現(xiàn)象學(xué),標(biāo)志著系統(tǒng)化的具身認(rèn)知理論體系最終形成。文章在梅洛龐蒂的具身認(rèn)知思想指導(dǎo)下,探討了具身認(rèn)知的知識觀、學(xué)習(xí)觀與教學(xué)觀,以期為具身教學(xué)的開展提供一些參考。研究發(fā)現(xiàn):知識是在認(rèn)知主體與認(rèn)知對象、環(huán)境之間互動的過程中逐漸建構(gòu)形成的,具有鮮明的涉身性、情境性與生成性特征;學(xué)習(xí)是學(xué)習(xí)者充分整合所處的自然環(huán)境與機體內(nèi)部的生理資源,促進知識建構(gòu)發(fā)生的過程。學(xué)習(xí)的發(fā)生,需要重視身體對知識學(xué)習(xí)的作用,提供知識學(xué)習(xí)所需要的環(huán)境并促使知識整體性學(xué)習(xí)的發(fā)生;理想的教學(xué)是具身的,具有感官參與、心身統(tǒng)一與身體力行等特征,是教師為了促使學(xué)習(xí)者進行有效學(xué)習(xí)而開展的一系列行為組合。教學(xué)的有效開展,需要解放學(xué)生身體與構(gòu)建多模態(tài)的教學(xué)環(huán)境,加強教學(xué)干預(yù)并選擇趣味化的教學(xué)內(nèi)容,強調(diào)身體體驗和采用做中學(xué)的教學(xué)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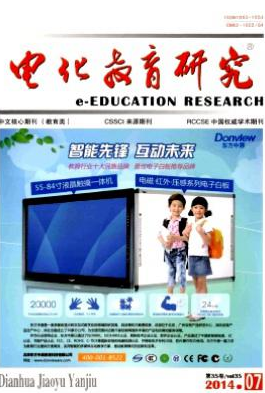
本文源自電化教育研究,2020,41(07):21-27+34.《電化教育研究》創(chuàng)刊于1980年,讀者遍及英、美、日、荷蘭、韓、加拿大等國家和香港、臺灣等地區(qū),是我國教育與電教界的學(xué)術(shù)理論園地和權(quán)威性刊物,素有“中國電化教育理論研究基地”之稱譽,倍受國內(nèi)外數(shù)萬讀者的傾心和愛戴。
一、引言
恩格斯指出:“認(rèn)識論的核心問題是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探索的是人類知識的起源、基礎(chǔ)與真理性[1]”。認(rèn)知科學(xué)是認(rèn)識論在當(dāng)代的延續(xù)和擴展[2]。雖然傳統(tǒng)(第一代)認(rèn)知科學(xué)對課堂教學(xué)的發(fā)展功不可沒,但是其所信奉的“身心二元論”將心靈和肉體、意識和身體、精神和物質(zhì)完全對立起來,不僅無法使身心統(tǒng)一,消解不了身心二元的哲學(xué)難題,而且也無法解釋身體與心靈是如何互相作用與影響的[3]。這不僅嚴(yán)重影響了教育教學(xué)的有效實施,而且還無法實現(xiàn)促進人全面發(fā)展的美好愿望[4]。
自19世紀(jì)以來,胡塞爾、海德格爾與梅洛龐蒂等哲學(xué)家們相繼就“身心二元論”的固有缺陷展開了深刻的反思與批判,逐漸確立了身體在哲學(xué)中絕對優(yōu)先的地位。在身體復(fù)歸的背景下,“具身認(rèn)知”這種新興的認(rèn)知理論順勢而生。隨著具身認(rèn)知思想的成熟,具身認(rèn)知被引入心理學(xué)領(lǐng)域,在得到認(rèn)知神經(jīng)科學(xué)和實驗心理學(xué)的進一步確證后又開始進入教育學(xué)領(lǐng)域[5]。近年來,具身認(rèn)知對教育學(xué)的影響日益增大,教學(xué)已呈現(xiàn)出較為明顯的具身取向。然而,當(dāng)前關(guān)于具身教學(xué)應(yīng)如何有效實施、注意哪些問題等基礎(chǔ)性理論還十分薄弱。實際上,諸如此類的教育問題,歸根結(jié)底都是哲學(xué)的問題,因為哲學(xué)的思考觸及教育的根本、整體及其與整個生活的關(guān)聯(lián)。因此,具身認(rèn)知的哲學(xué)思想無疑是指導(dǎo)具身教學(xué)有效開展的重要理論資源。鑒于此,本研究擬從具身認(rèn)知的上游思想淵源出發(fā),在哲學(xué)思想的關(guān)照下,對具身認(rèn)知的知識觀、學(xué)習(xí)觀及教學(xué)觀進行較為系統(tǒng)的探討,以期為具身教學(xué)的開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參考。
二、具身認(rèn)知思想的淵源與發(fā)展
(一)胡塞爾對肉身的關(guān)注
胡塞爾對笛卡爾“身心二元論”的反思,初步顯露了具身認(rèn)知的思想。胡塞爾雖然肯定了笛卡爾把“我思”作為形而上學(xué)的基石,也認(rèn)可笛卡爾從“我”引申出人的存在及外部世界的觀點,但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的論斷及基于此建立的“身心二元論”體系都還沒有擺脫心理主義,不是純粹的意識主體,因為在笛卡爾那里,擁有無限自由意志和有限理智的主體還不能作為知識的最終根據(jù),還需要無限性的上帝來保證知識的可靠性。笛卡爾之后,關(guān)于認(rèn)識論的思考,呈唯理論與經(jīng)驗論并列的格局。康德認(rèn)為二者都是有失偏頗的,必須從主體的角度思考知識問題。他融合了二者,提出了“先驗論”。胡塞爾雖然認(rèn)同康德的思路,但康德的知識存在無法從根本上突破經(jīng)驗層面的缺陷。于是,胡塞爾在繼承康德先驗哲學(xué)的立場上,認(rèn)為必須繼續(xù)追問主體性,回到先驗主體性(現(xiàn)象學(xué)還原),因為一個在純粹意識中構(gòu)造世界和他人的人如果失去了其存在的肉身性和感受性,也就喪失了與世界的原始聯(lián)系[6]。胡塞爾正是通過這種肉身感覺來獲取相關(guān)事實性知識,實現(xiàn)了對笛卡爾“我思”的超越,使“思”不再是空洞的行為內(nèi)容,而是以肉身事件為基礎(chǔ),并能夠得到實體性以及因果性的聯(lián)系與關(guān)照[7]。胡塞爾以此為基礎(chǔ)開辟的現(xiàn)象學(xué)不僅重視肉身(身體),而且還強調(diào)生命形式和觸覺經(jīng)驗,倡導(dǎo)哲學(xué)理論的肉身轉(zhuǎn)向。但遺憾的是,胡塞爾并沒有將其肉身轉(zhuǎn)向的觀點進一步發(fā)展成肉身現(xiàn)象學(xué)。
(二)海德格爾對身體的重視
繼胡塞爾之后,海德格爾從存在論的高度對笛卡爾“身心二元論”進行了反思。海德格爾指出:“笛卡爾將‘我思故我在’視為哲學(xué)可靠的新根基,但是他并沒有規(guī)定清楚‘我在’的存在意義[8]。”為了追索存在,海德格爾的運思是現(xiàn)象學(xué)的。這里所言的現(xiàn)象學(xué),雖然是貫徹胡塞爾所提“面向?qū)嵤卤旧?rdquo;原則的現(xiàn)象學(xué),但并不是完全胡塞爾意義上的意識現(xiàn)象學(xué)。在海德格爾看來,純粹理論的知識態(tài)度并不具有優(yōu)先性,以純粹理論態(tài)度是無法把握器具或物的真正存在。于是,海德格爾將存在本身作為出發(fā)點加以思考,認(rèn)為終極的來源應(yīng)是“存在”本身,可用“存在”超越二元世界的劃分。那么,應(yīng)如何逼近“存在”呢?對此,海德格爾認(rèn)為,物的存在首先在于人對物的使用,在于物與人的關(guān)聯(lián)狀態(tài),是“為我們的”存在。此意味著,人與存在是密不可分的,存在需要人,人也需要存在。緣于此,海德格爾將“人”視為存在研究的出發(fā)點,主張應(yīng)從存在者之存在角度來思存在者本身。沿著這一思路,海德格爾進一步指出人的身體應(yīng)是一種存在方式,因為身體化雖然決定著此在在世界中的存在,但與此同時身體化也由此在在世界中的存在所決定[9]。簡而言之,在海德格爾看來,人對世界的認(rèn)識是通過我們的身體與世界其他物體的互動實現(xiàn)的[10]。雖然此觀點對推動具身認(rèn)知思想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由于海德格爾并未對身體問題展開深入的探討,使得他也未能將其具身認(rèn)知的思想發(fā)展成為與存在問題相互適應(yīng)的存在理論。
(三)梅洛龐蒂的身體理論
梅洛龐蒂也對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展開了猛烈的批判,認(rèn)為二元論是一切傳統(tǒng)哲學(xué)各種問題的癥結(jié)所在。他指出,在笛卡爾的二元論中,主體是內(nèi)在的,客體是外在的,二者是彼此隔絕且相互排斥的,那么“內(nèi)在主體何以認(rèn)識與它完全隔絕的客體”這一問題成了經(jīng)驗主義者與理性主義者都無法擺脫的難題,由此導(dǎo)致了各種懷疑論和不可知論的泛濫[11]。為了實現(xiàn)對二元論的超越,梅洛龐蒂致力于建立一種既不是唯心主義,也不是唯物主義的“模糊哲學(xué)”。這里的“模糊”實際上是相對于主客“二元論”而言的“一元論”。
梅洛龐蒂通過論述知覺(現(xiàn)象)世界主客體的同一性問題,闡述了他建立中性“一元論”的觀點。在梅洛龐蒂看來,作為現(xiàn)象世界的知覺世界或知覺,既不是單純客觀的,也不是單純主觀的,而是主客體不可分割的同一存在。他的理由是,雖然知覺世界的經(jīng)驗材料是客觀的,但是需要在主體能動性的作用下,才能將或然的經(jīng)驗材料整理成有序的整體。因此,不論是缺少客觀的經(jīng)驗材料,還是缺少主體的能動性作用,都不可能有知覺或知覺世界。也就是說,經(jīng)驗世界是主客體不可分割的同一,不論是缺少主體,還是缺少客體,都將導(dǎo)致作為現(xiàn)象的“知覺世界”不復(fù)存在。在梅洛龐蒂的知覺世界里,不存在主體與客體的對立,他所說的知覺世界主體客體不可分的同一,實際上就是經(jīng)驗世界與自我不可分的同一。梅洛龐蒂正是透過“知覺世界”找到了一種關(guān)于存在的“一元論”。
在“一元論”的基礎(chǔ)上,梅洛龐蒂對海德格爾未深入分析的身體問題作了系統(tǒng)的處理。他從身體經(jīng)驗出發(fā),關(guān)注知覺與被知覺世界的關(guān)系,不僅賦予了身體在哲學(xué)中絕對優(yōu)先的地位,而且還將其具身認(rèn)知思想發(fā)展為知覺現(xiàn)象學(xué)(或稱為身體現(xiàn)象學(xué))[12]。梅洛龐蒂的知覺現(xiàn)象學(xué)徹底打破了身體與意識二元對立的觀點,認(rèn)為身體與意識是統(tǒng)一的,并且主體對世界的認(rèn)識是通過身體才得以實現(xiàn)的[13]。由此將人們從純思認(rèn)識轉(zhuǎn)向?qū)ι眢w的體知認(rèn)識,使現(xiàn)代哲學(xué)開啟了超越離身理論樣式的新紀(jì)元[14]。本文對具身認(rèn)知的知識觀、學(xué)習(xí)觀及教學(xué)觀的探討,即擬在梅洛龐蒂具身認(rèn)知哲學(xué)思想的關(guān)照下進行。
三、具身認(rèn)知的知識觀
知識觀是一個哲學(xué)范疇,涉及知識的本質(zhì)、來源及其與認(rèn)識對象、認(rèn)識主體的關(guān)系等問題的觀點[15]。為了能更加全面地把握具身認(rèn)知的知識觀,本部分?jǐn)M從梅洛龐蒂對知識本質(zhì)的解讀開始討論。
(一)知識的本質(zhì)
梅洛龐蒂為了建立調(diào)和“主體主義”與“客體主義”的中性“一元論”,認(rèn)為必須徹底貫徹胡塞爾的“回到實事本身”的口號。在對認(rèn)知行為分析時,梅洛龐蒂與胡塞爾雖然都談及意識,但是他們所說的“意識”并不相同。胡塞爾的“意識”是“先驗”的,而梅洛龐蒂的“意識”是“知覺”的。在梅洛龐蒂看來,知覺是身體和心靈的相匯之處,知覺經(jīng)驗才是最原始的經(jīng)驗[16]。梅洛龐蒂所說的“回到實事本身”其實質(zhì)就是要回到“原始經(jīng)驗”本身,也就是“知覺”或“知覺世界”本身。故此,梅洛龐蒂將知覺視為知識的源泉。
就“知覺意識如何構(gòu)成其對象特殊方式”這一問題,梅洛龐蒂認(rèn)為應(yīng)回到現(xiàn)象世界,從知覺體驗出發(fā)來分析。典型如,我們之所以能看到白紙上的紅點,是因為有白紙的背景襯托。白紙上的紅點是我們獲得最簡單的感覺材料,并且白紙與紅點所形成的“物體(圖形)—背景”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是不可再進行還原的整體了[17]。在梅洛龐蒂知覺的“物體—背景”結(jié)構(gòu)中,被知覺的物體只有在背景的映襯下才能得以顯現(xiàn)。由于知識與知覺主體是融為一體的,因而“物體—背景”這一整體的結(jié)構(gòu)是在我們的知覺中才是如此的。也就是說,“物體—背景”結(jié)構(gòu)是在人“身體”的共同參與下才有意義。這種加入身體所形成的“物體—背景—身體”結(jié)構(gòu),就是所謂的知覺場(現(xiàn)象場)。
在梅洛龐蒂看來,所有的感知活動都必須在對應(yīng)的知覺場中才能完成,知覺體驗是某人(一種匿名的、前人稱的身體狀態(tài))在我之中的感知,并不是我在感知。被感知的事物并不是一種純粹的存在,我所看到的事物,是我個人經(jīng)歷的一個因素,因為感覺實際上是一種重構(gòu),是以我身上的一種預(yù)先形成的沉淀為前提[17]。也就是說,在梅洛龐蒂看來,知識是主體基于已有知識經(jīng)驗基礎(chǔ)之上建構(gòu)來的,是在認(rèn)知(知覺)主體的身體與認(rèn)知對象、環(huán)境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完成建構(gòu)的。
與感知一樣,知覺場中也存在“內(nèi)在性與超越性的悖論”。梅洛龐蒂認(rèn)為,知覺場的內(nèi)在性與超越性是辯證的關(guān)系。辯證關(guān)系意味著知覺場不可能是靜止不變的,而是處于持續(xù)不斷的流動變化之中。這種流動變化主要體現(xiàn)在我們總是從一個現(xiàn)象(或事物)過渡到另一個,并且這種過渡是永無止境。但現(xiàn)象的過渡與轉(zhuǎn)換并不會導(dǎo)致無序與混亂,因為前后不同現(xiàn)象是環(huán)環(huán)相扣,存在一定的內(nèi)在聯(lián)系的。也即是說,有一種存在的理由會為現(xiàn)象的流動指引方向,被引起的現(xiàn)象不僅可以闡明和解釋引起的現(xiàn)象,而且還能引起現(xiàn)象的后繼。因此,被引起的現(xiàn)象恰似預(yù)先存在于其動機中一般。由此看來,知識的建構(gòu)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認(rèn)知主體與認(rèn)知對象及環(huán)境之間互動的過程中逐漸生成的。
(二)知識與對象及主體的關(guān)系
分析完了“知識”的本質(zhì),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具身認(rèn)知主張的是一種什么樣的知識觀呢?對這一問題的討論至少涉及兩個方面:一個是知識與認(rèn)知對象及主體的關(guān)系如何?另一個是這種知識觀有何獨特之處?
關(guān)于知識與認(rèn)知對象及主體的關(guān)系,可以從梅洛龐蒂“物體—背景—身體”的整體結(jié)構(gòu)出發(fā)加以理解。根據(jù)梅洛龐蒂“物體—背景—身體”的整體結(jié)構(gòu),知識來源于知覺主體與知覺對象及環(huán)境之間發(fā)生的創(chuàng)造性與生成性的互動。因此,知識總是與特定的物體、背景及知覺的身體相關(guān)聯(lián),離開了物體、背景及知覺主體就沒有知識。也就是說,知識與認(rèn)知對象、知覺主體及環(huán)境都是緊密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的,只有認(rèn)知對象、知覺主體及環(huán)境三者發(fā)生有效的互動,才能形成新的知識。反之,不論是缺少了認(rèn)知對象,還是脫離了認(rèn)知主體及其參與性的實踐與行為,抑或是缺少特定的背景,都不可能形成新的知識。
從知識與認(rèn)知對象及主體的關(guān)系來看,具身認(rèn)知并不強調(diào)知識的真理性、客觀性與確定性,也不將知識看成是對對象的真實反映,而是強調(diào)知識的“涉身性”“豐富性”與“差異性”,此即具身認(rèn)知視域下知識觀的獨特之處。其中,知識的“涉身性”強調(diào)知識與認(rèn)知主體的身體聯(lián)系,認(rèn)為知識是涉身的。這種涉身性不僅僅表現(xiàn)在知識的生成需要認(rèn)知主體身體的各種構(gòu)造、感官、運動系統(tǒng)及神經(jīng)結(jié)構(gòu)等支持,而且還表現(xiàn)在其需要基于身體的體驗、感受和經(jīng)歷等經(jīng)驗層面的嵌入[18];知識的“豐富性”主要通過知識與物體的關(guān)系加以體現(xiàn)。由于人類世界里充斥著不計其數(shù)的客觀物體,且基于每一種物體都可以形成與其相對應(yīng)的知識,因此我們很難用數(shù)字來說明知識的豐富程度。莊子所云的“學(xué)也無涯”,正是對知識的豐富性最好的佐證;知識的“差異性”主要通過知識與背景及身體的關(guān)系加以體現(xiàn)。根據(jù)“物體—背景—身體”的整體結(jié)構(gòu)來看,知識是內(nèi)嵌于環(huán)境之中,是認(rèn)知主體與對象、環(huán)境相互作用的結(jié)果。對于同一物體而言,在不同的背景與不同主體中形成的知識結(jié)果是不盡相同的,存在一定的差異性。例如,相同的一個紅色圓點,在白色的背景下與在紅色背景下所呈現(xiàn)出來的結(jié)果就截然不同。
四、具身認(rèn)知的學(xué)習(xí)觀
學(xué)習(xí)觀主要是關(guān)于學(xué)習(xí)者應(yīng)如何學(xué)習(xí)知識的觀點。因此,我們需要先把握在具身認(rèn)知視域下學(xué)習(xí)是如何發(fā)生的,才能夠進一步回答應(yīng)如何組織有效的知識學(xué)習(xí)這一問題。
(一)具身認(rèn)知的認(rèn)知主張
在梅洛龐蒂的具身認(rèn)知視域下,探討學(xué)習(xí)是如何發(fā)生的,還需要從他的“行為”概念開始說起。受格式塔心理學(xué)的影響,梅洛龐蒂將“行為”看成是一種“形式”或“結(jié)構(gòu)”,并將“行為”劃分為混沌形式、可變動形式和象征形式三種不同的形式。雖然混沌形式、可變動形式和象征形式這三種不同的形式有低級與高級之分,但是對人來說是可以同時兼具這三個層次行為的。
混沌形式與“刺激—反應(yīng)”模式較為相近,三種形式中屬它最低級。在混沌形式中,人的機體與環(huán)境構(gòu)成是一種類似于“圖形—背景”的結(jié)構(gòu),因而人的機體并不是獨立的,人的行為完全囿于其所處的環(huán)境[16]。因此,對于以混沌形式進行活動的主體而言,學(xué)習(xí)是無法有效進行的。因為有效學(xué)習(xí)的發(fā)生意味著要將在特定情境中掌握的知識遷移與應(yīng)用到其他的情境中,而混沌形式中的主體不能脫離其所處的情境而生存。
可變動形式是一種信號行為,該形式與混沌形式最大的不同是人的機體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在可變動形式中,行為是以相對獨立于它們在其中得以實現(xiàn)的那些質(zhì)料的結(jié)構(gòu)為基礎(chǔ)的,機體一旦把握了這種結(jié)構(gòu),不僅能夠賦予這種整體結(jié)構(gòu)以意義,而且還能夠把它運用到類似的情境中去[19]。由此可見,可變動形式為學(xué)習(xí)的發(fā)生提供了可能性。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盡管可變動形式比混沌形式高級,但是二者都必須緊密依附于具體的情境,表現(xiàn)出人的某種短促而笨拙的生存方式。
象征形式是一種與符號活動有關(guān)的人類特有的行為,彰顯了一種自由與超越的精神,是三種形式中最高級的形式。如果說可變動形式使學(xué)習(xí)變成了可能,那么象征形式則是學(xué)習(xí)發(fā)生的理想狀態(tài)。在象征形式中,人的機體可以不再黏附于特定的具體情境,不僅可以將習(xí)得的情境結(jié)構(gòu)遷移應(yīng)用到其他類型的情境問題中,而且還有可能在已把握的結(jié)構(gòu)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出新的結(jié)構(gòu)[20]。之所以說象征形式的行為是人類特有的,是因為人不僅具有從不同視角觀察同一物體的能力,而且還具有反身能力,能將自己的身體視為目標(biāo)或?qū)ο蟆4送猓鼮橹匾氖侨四茉趯嶋H空間與現(xiàn)象空間中自如地穿梭,具有一種象征化的能力,可以將自己引導(dǎo)到與可能、與間接相關(guān),而不是囿于某種特定的情境。
梅洛龐蒂在混沌形式、可變動形式和象征形式這三種不同形式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提出了三種由低到高的結(jié)構(gòu)存在樣式:物理秩序、生命秩序和人類秩序。這三種秩序的等級雖有高低之別,但又是互相依存的。高級秩序的建立需要以低級秩序為基礎(chǔ),但高級秩序的形成也會反過來賦予低級秩序新的意義。此即是說,人類秩序(精神場,包含整個文化世界)的形成是建立在統(tǒng)整物理(物理場,所處的自然環(huán)境)和生命秩序(生理場,機體的生理身體與先天的生理機制)基礎(chǔ)之上的,即人的行為只有以具體環(huán)境和身體為基礎(chǔ),才能創(chuàng)造出新的場所與意義[21]。由此來看,并不存在脫離具體環(huán)境與生理機制的人類行為,因為人類行為作為一種結(jié)構(gòu)總是與機體所處的環(huán)境條件及機體內(nèi)部的生理資源密切相關(guān)。因此,學(xué)習(xí)既不是認(rèn)知主體對信息進行簡單的心智加工,也不是認(rèn)知主體所處的自然環(huán)境對機體行為的機械作用,而是認(rèn)知主體充分整合所處的自然環(huán)境與機體內(nèi)部的生理資源,促進知識建構(gòu)發(fā)生的過程,即促使身體與認(rèn)知對象、環(huán)境發(fā)生有效的互動并達到動態(tài)平衡的過程。
(二)具身認(rèn)知視野中的知識學(xué)習(xí)
基于上述對學(xué)習(xí)的解讀,應(yīng)如何組織有效的知識學(xué)習(xí)呢?要回答這一問題,需要從學(xué)習(xí)發(fā)生的前提條件開始討論。根據(jù)梅洛龐蒂的觀點,學(xué)習(xí)是具身的,學(xué)習(xí)的發(fā)生需要認(rèn)知主體在充分整合環(huán)境與機體內(nèi)部生理資源的基礎(chǔ)前提下,才有可能促進身體與認(rèn)知對象、環(huán)境發(fā)生充分的相互作用。據(jù)此來看,要想組織有效的知識學(xué)習(xí),應(yīng)重點做好以下幾點工作:
1. 重視身體對知識學(xué)習(xí)的作用
具身認(rèn)知認(rèn)為人的認(rèn)知與學(xué)習(xí)都是具身的,強調(diào)身體之于知識學(xué)習(xí)的重要作用[22]。在梅洛龐蒂看來,我們的身體首先是生理學(xué)意義上的身體,其與生俱來的生理結(jié)構(gòu)是我們對知識進行加工與處理的重要保障;其次,我們的身體也是運動的身體,知識的有效學(xué)習(xí)是在身體運動的基礎(chǔ)上完成的;最后,我們的身體還是復(fù)演的身體,我們能夠通過大腦與身體的感知與運動系統(tǒng)等通道模擬他人的感受,這種心理狀態(tài)的“復(fù)演”是我們對概念進行加工的基礎(chǔ)[23]。由此可見,知識的學(xué)習(xí)是基于身體的,身體塑造了知識的認(rèn)知。因此,在教學(xué)中,不僅要充分調(diào)動學(xué)習(xí)者的身體感官,還要誘發(fā)學(xué)習(xí)者身體發(fā)生“運動”與“復(fù)演”。
2. 提供知識學(xué)習(xí)所需要的環(huán)境
根據(jù)梅洛龐蒂的觀點,知識的學(xué)習(xí)不僅是具身的,而且也不能脫離具體的環(huán)境。從知識與學(xué)習(xí)發(fā)生的視角來看,知識產(chǎn)生于身體與認(rèn)知對象及環(huán)境間的互動,知識的有效學(xué)習(xí)是認(rèn)知主體充分整合環(huán)境與身體的生理資源,促使身體與認(rèn)知對象及其所處環(huán)境發(fā)生互動并達到動態(tài)平衡的過程。也就是說,知識的形成需要環(huán)境的襯托,有效的知識學(xué)習(xí)需要在適當(dāng)?shù)沫h(huán)境中才能完成。脫離了環(huán)境,知識將無法形成,認(rèn)知主體的學(xué)習(xí)也就無法順利進行了。因此,為了促使學(xué)習(xí)者有效知識學(xué)習(xí)的發(fā)生,應(yīng)重視情境化因素之于知識學(xué)習(xí)的重要作用,提供有利于學(xué)習(xí)者知識學(xué)習(xí)的學(xué)習(xí)環(huán)境。
3. 促使知識整體性學(xué)習(xí)的發(fā)生
上述內(nèi)容雖然分別強調(diào)了身體與環(huán)境之于知識學(xué)習(xí)的重要作用,但是從學(xué)習(xí)發(fā)生的本質(zhì)來看,僅僅只有身體參與,或者僅提供必要的學(xué)習(xí)環(huán)境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學(xué)習(xí)是認(rèn)知主體的身體、對象與環(huán)境交織在一起的整體性實踐活動[24]。也就是說,在具身認(rèn)知的視域下,知識的學(xué)習(xí)應(yīng)是一種整體性的學(xué)習(xí),知識學(xué)習(xí)的實質(zhì)就是認(rèn)知主體的身體與認(rèn)知對象及其所處環(huán)境發(fā)生有效互動的過程。因此,我們不僅要重視身體之于知識學(xué)習(xí)的重要作用,提供知識學(xué)習(xí)所需要的學(xué)習(xí)環(huán)境,更為重要的是要致力于促進認(rèn)知主體的身體與認(rèn)知對象、學(xué)習(xí)環(huán)境之間發(fā)生有效的互動。
五、具身認(rèn)知的教學(xué)觀
具身認(rèn)知的教學(xué)觀部分主要探討與知識觀、學(xué)習(xí)觀相一致的教學(xué)實踐方式,勾勒一幅具身認(rèn)知視域下的應(yīng)然性教學(xué)圖景。
(一)具身認(rèn)知的教學(xué)追求
在現(xiàn)代教育學(xué)中,教學(xué)承擔(dān)著知識文化傳授的任務(wù),教師“教”的旨趣主要在于促進學(xué)習(xí)者有效“學(xué)”的發(fā)生。基于前述的分析可知,知識的學(xué)習(xí)是認(rèn)知主體充分整合所處的環(huán)境與機體內(nèi)部的生理資源,促使身體與認(rèn)知對象、環(huán)境發(fā)生有效的互動并達到動態(tài)平衡的過程。據(jù)此而言,具身認(rèn)知下的有效教學(xué)就是教師圍繞特定的教學(xué)目標(biāo),有目的、有計劃地引導(dǎo)并促使學(xué)習(xí)者的身體與認(rèn)知對象、環(huán)境發(fā)生有效互動并達到動態(tài)平衡的行為組合。由此看來,教學(xué)成功的關(guān)鍵,在于引導(dǎo)認(rèn)知主體的身體與認(rèn)知對象及其所處環(huán)境發(fā)生有效的互動,如若身體缺席,有效教學(xué)將不可能發(fā)生。也就是說,在具身認(rèn)知觀的視域下,或者說基于具身認(rèn)知對知識及學(xué)習(xí)的理解,具身認(rèn)知的教學(xué)追求是具身的。
接踵而至的問題是,這種教學(xué)的具身具體是如何實現(xiàn)的,又有何特征呢?對于此問題,還需要從梅洛龐蒂的身體概念開始說起。梅洛龐蒂的“身體”并不是簡單的“肉身”,而是多層次的統(tǒng)一身體,這個統(tǒng)一包含了生理諸官能的統(tǒng)一、心身統(tǒng)一以及與世界的統(tǒng)一等三個不同層面。也就是說,教學(xué)的這種具身,實際上是由這三種不同層面的身體共同參與一起實現(xiàn)的。關(guān)于教學(xué)追求的具身是什么樣的,有何特征,本文主要從身體的三個層面出發(fā)展開論述。
1. 感官參與
在梅洛龐蒂看來,身體首先應(yīng)是諸官能統(tǒng)一的身體。諸官能的統(tǒng)一意味著我們身體的各個部分并不是分離的,而是互相包含的。也即是說,我們的身體并不是多個器官的簡單疊加,而是全息的統(tǒng)一體,因為身體的各個感官都是相通的。但是,感官的統(tǒng)一性并不否認(rèn)不同感官間的差異存在。因為從本質(zhì)上來說,每種不同的感官都有其區(qū)別于其他感官的顯著特征,都帶著一種不能完全轉(zhuǎn)換的存在結(jié)構(gòu)[17]。如果我們單獨使用某種感官去接觸某個特定的物體,所得到的感覺是不同的。只不過這種感官間差異,并不會破壞諸官能的統(tǒng)一性。因為我們的身體圖式會統(tǒng)合不同感官的結(jié)果,促成感覺間的統(tǒng)一性,從而使我們對物體的認(rèn)知更加豐滿。從這個意義上看,學(xué)習(xí)者的感官參與是意義建構(gòu)的基礎(chǔ)和提前,因而理想的教學(xué)是感官參與的,并且越多感官參與越好。
2. 心身統(tǒng)一
其次,身體也是心身統(tǒng)一的身體。在梅洛龐蒂看來,人的心靈和身體并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統(tǒng)一的。為了說明觀點的合理性,梅洛龐蒂進行了論證。他指出,人類同時兼具物理、生命和心理這三種不同的辯證法,正常人的行為和身體適用的是心理辯證法[16]。心理辯證法中主要討論的是生理與心理的關(guān)系,當(dāng)二者的關(guān)系是和諧的整合關(guān)系時,生理—心理結(jié)構(gòu)會呈現(xiàn)出新的意義———心靈。由于呈現(xiàn)出心靈的生理—心理結(jié)構(gòu)是統(tǒng)一于身體的,因此,心靈與身體是統(tǒng)一的,心靈不能脫離身體而獨立存在,身體也離不開心靈的支持。如果心靈離開了身體,生理—心理結(jié)構(gòu)就處于一種無序的分裂狀態(tài),引發(fā)行為場的紊亂,導(dǎo)致知識的建構(gòu)無法順利進行。從這個意義上看,理想教學(xué)中的學(xué)習(xí)者也應(yīng)是心身統(tǒng)一的。因為只有學(xué)習(xí)者是心身一致的,才有可能進行有效的學(xué)習(xí)。
3. 身體力行
最后,身體還是與世界統(tǒng)一的身體。梅洛龐蒂所說的“世界”指的是全部可知覺物的總體和所有物的物。在他看來,人是置身于世界之中的,并且人對世界是存在某種意向關(guān)系的。因為不論是自然世界還是社會世界,都屬于被感知的世界。因此,身體與世界是統(tǒng)一的,既不存在自在的世界,也不存在脫離世界的身體。置身于世界的身體,會將“看”到的種種景象進行整合,最終融入一個共同世界中,從而完成對世界的意義建構(gòu)。因而,身體是我們擁有一個世界的一般方式,身體的每一次震顫都在揭示著世界的性質(zhì)[17]。這意味著,只有認(rèn)知主體的身體處于不斷的運動狀態(tài),不斷地與世界接觸,才可以更好地認(rèn)識世界。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理想的教學(xué)還應(yīng)是身體力行的,學(xué)習(xí)者的身體不僅是被充分激活的,運動的,而且是能通過具體的實踐活動與認(rèn)知對象、環(huán)境發(fā)生有效互動的。
(二)具身認(rèn)知視野中的教學(xué)實踐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在具身認(rèn)知視域下,教學(xué)應(yīng)如何開展?本文基于教學(xué)的感官參與、心身統(tǒng)一與身體力行的特征,參照知識的本質(zhì)與學(xué)習(xí)的關(guān)鍵,給出了幾點建議以供參考:
1. 解放學(xué)生身體,構(gòu)建多模態(tài)的教學(xué)環(huán)境
感官體驗是一切科學(xué)和知識的基礎(chǔ)。教學(xué)的感官參與特征提醒我們,必須要深刻認(rèn)識到身體的感官體驗是學(xué)習(xí)者高級認(rèn)知發(fā)展的基石,因為有效學(xué)習(xí)的發(fā)生,是建立在認(rèn)知主體充分整合所處的自然環(huán)境與機體內(nèi)部的生理資源基礎(chǔ)之上的。也就是說,教師在教學(xué)中應(yīng)努力促使學(xué)習(xí)者的身體與認(rèn)知對象、環(huán)境發(fā)生有效的互動。要實現(xiàn)這一目標(biāo),教師首先要在教學(xué)中解放學(xué)習(xí)者的身體,使學(xué)習(xí)者的身體感官有與外界事物發(fā)生互動的可能。此外,還應(yīng)構(gòu)建多模態(tài)的教學(xué)環(huán)境,典型如面向我們?nèi)祟惖淖匀恢X構(gòu)建而成的混合現(xiàn)實學(xué)習(xí)環(huán)境[25],為學(xué)習(xí)者身體與認(rèn)知對象、環(huán)境的深度互動創(chuàng)造條件。
2. 加強教學(xué)干預(yù),選擇趣味化的教學(xué)內(nèi)容
心靈與身體的統(tǒng)一,是意義建構(gòu)的重要保障。教學(xué)的心身統(tǒng)一特征要求教師在開展具身教學(xué)時,要設(shè)法讓學(xué)習(xí)者的心靈與身體都切實地參與到教學(xué)活動中。為此,教師首先應(yīng)加強教學(xué)干預(yù)。當(dāng)學(xué)習(xí)者出現(xiàn)心不在焉、聽而不動等心身分離的現(xiàn)象時,教師應(yīng)及時干預(yù),使學(xué)習(xí)者心身及時統(tǒng)合,保障知識建構(gòu)活動得以繼續(xù)。除了必要的教學(xué)干預(yù),教師還應(yīng)盡量選擇趣味化的教學(xué)內(nèi)容,來激發(fā)學(xué)習(xí)者的學(xué)習(xí)興趣,促使學(xué)習(xí)者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當(dāng)然,不少教學(xué)內(nèi)容本身的趣味性可能并不高。在開展此類教學(xué)內(nèi)容的教學(xué)時,教師可通過創(chuàng)設(shè)趣味化的課堂導(dǎo)入、構(gòu)建生活化的情境或真實世界的情境等方式來吸引學(xué)習(xí)者的注意。
3. 強調(diào)身體體驗,采用做中學(xué)的教學(xué)方式
促進學(xué)習(xí)者身體與認(rèn)知對象、環(huán)境發(fā)生有效的互動,是具身教學(xué)成功的關(guān)鍵。教學(xué)的身體力行特征強調(diào)學(xué)習(xí)者的身體實踐,認(rèn)為身體是擁有世界的一般方式,知識建構(gòu)是基于身體與認(rèn)知對象、環(huán)境的互動完成的。那么,在教學(xué)中要如何教學(xué)才有利于促使學(xué)習(xí)者的身體與認(rèn)知對象、環(huán)境發(fā)生互動呢?由于學(xué)習(xí)者的身體只有在“動”起來的過程中,才有機會與認(rèn)知對象、環(huán)境發(fā)生相互作用。因此,教學(xué)的開展宜采用“做中學(xué)”的方式。教師可以通過組織基于項目或基于問題等以“做”為主的學(xué)習(xí)活動,讓學(xué)習(xí)者的身體活躍起來,促使學(xué)習(xí)者的身體不斷地與認(rèn)知對象、環(huán)境發(fā)生有效的互動,幫助學(xué)習(xí)者更好地完成知識建構(gòu)。
六、結(jié)語
本文首先梳理了具身認(rèn)知的發(fā)展脈絡(luò),指出具身認(rèn)知的哲學(xué)思想成熟于梅洛龐蒂的知覺現(xiàn)象學(xué),接著在梅洛龐蒂知覺現(xiàn)象學(xué)的具身認(rèn)知思想指導(dǎo)下,借助演繹的基本邏輯完成了對具身認(rèn)知的知識觀、學(xué)習(xí)觀及教學(xué)觀的討論。具體而言,本文通過嚴(yán)格的分析,對具身認(rèn)知視域下知識的本質(zhì)及其與對象及主體的關(guān)系、知識學(xué)習(xí)的認(rèn)知主張與如何進行有效的知識學(xué)習(xí)、教學(xué)追求與特征及如何開展教學(xué)等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tǒng)的闡發(fā)。由于這些問題都是開展具身教學(xué)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因而本研究不僅有利于豐富具身教學(xué)的學(xué)理基礎(chǔ),而且對指導(dǎo)具身教學(xué)的落地與實踐也具有較為重要的指導(dǎo)意義與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7.
[2]張積家,馬利軍.馬克思?恩格斯的具身認(rèn)知思想及其價值[J].華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3(5):93-105,208.
[3]王曼.笛卡爾身心二元論及其對英美心靈哲學(xué)的影響[J].唯實,2010(12):43-46.
[4]馬蕾.“技術(shù)熱”背景下學(xué)習(xí)共同體的哲學(xué)反思與本真意蘊[J].重慶高教研究,2020(2):62-71.
[5]宋嶺,張華.具身化課程的核心特征及其故事性建構(gòu)[J].課程·教材·教法,2019(2):37-43.
[6]黃首晶.教育改革的認(rèn)識論基礎(chǔ)反思[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7:39-45.
[7]羅克汀.從現(xiàn)象學(xué)到存在主義的演變---現(xiàn)象學(xué)縱向研究[M].廣州:廣州文化出版社,1990:41.
[8]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M].陳小文,孫周興,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9:70.
[9]王建輝.動態(tài)的身體:身體-身體化---海德格爾《澤利康講座》中的身體現(xiàn)象學(xué)[J].世界哲學(xué),2016(4):19-25,160.
[10]葉浩生.西方心理學(xué)史[M].北京:開明出版社,2012:210.
[11]夏基松.簡明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44.
[12]徐獻軍.具身認(rèn)知論---現(xiàn)象學(xué)在認(rèn)知科學(xué)研究范式轉(zhuǎn)型中的作用[M].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09:49.
[13]曹繼東.伊德技術(shù)哲學(xué)解析[M].沈陽:東北大學(xué)出版社,2013:125-127.
[14]方環(huán)非,鄭祥福.當(dāng)代西方哲學(xué)思潮[M].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13:152.
[15]周險峰.教育基本問題研究:回顧與反思[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xué)出版社,2016:83-84.
[17]梅洛龐蒂.知覺現(xiàn)象學(xué)[M].姜志輝,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1:24-46,276,288,194.
[18]張良.具身認(rèn)知理論視域中課程知識觀的重建[J].課程·教材·教法,2016(3):65-70.
[19]韓桂玲.吉爾·德勒茲身體創(chuàng)造學(xué)研究[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1:53.
[20]高宣揚.法蘭西思想評論(第5卷)[M].上海:同濟大學(xué)出版社,2010:118-119.
[21]張堯均.隱喻的身體---梅洛龐蒂的身體現(xiàn)象學(xué)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xué),2004.
[22]鄭旭東,王美倩,饒景陽.論具身學(xué)習(xí)及其設(shè)計:基于具身認(rèn)知的視角[J].電化教育研究,2019(1):25-32.
[23]潘旭東,吳漢榮,張飛霞,金偉民.教學(xué)轉(zhuǎn)型的學(xué)科實踐[M].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15:3-4.
[24]陳樂樂.具身研究的興起及其教育學(xué)意義[J].蘇州大學(xué)學(xué)報(教育科學(xué)版),2016(3):49-58.
[25]范文翔,趙瑞斌.數(shù)字學(xué)習(xí)環(huán)境新進展:混合現(xiàn)實學(xué)習(xí)環(huán)境的興起與應(yīng)用[J].電化教育研究,2019(10):40-46,60.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