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年來,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推動(dòng)了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大發(fā)展:研究成果增長迅猛,研究隊(duì)伍擴(kuò)充迅速,研究主題多樣化趨勢基本形成,研究方法多元化格局初現(xiàn)端倪。但高等教育大眾化并未從根本上推動(dòng)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全面轉(zhuǎn)型升級(jí):學(xué)科建設(shè)停滯不前,制度建設(shè)喜憂參半,能力建設(shè)差強(qiáng)人意,其根源在于作為政府行為的高等教育大眾化難以形成推動(dòng)高等教育研究變革的建構(gòu)性力量,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對于突如其來的高等教育大眾化準(zhǔn)備不足,其后的相關(guān)建設(shè)也沒有跟上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節(jié)奏。未來,中國高等教育研究要轉(zhuǎn)向以“內(nèi)涵式發(fā)展”為主的道路,以期為普及化時(shí)代中國高等教育強(qiáng)國建設(shè)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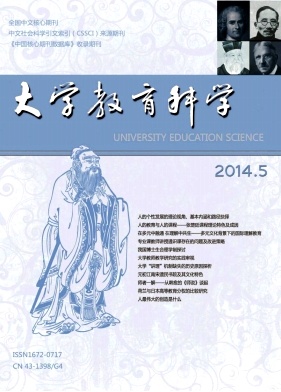
本文源自大學(xué)教育科學(xué) 2020年6期《大學(xué)教育科學(xué)》是經(jīng)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新出版(2002)936號(hào)]文件批準(zhǔn),由原1984年創(chuàng)刊的《機(jī)械工業(yè)高教研究》更名的高等教育類學(xué)術(shù)研究期刊,現(xiàn)已成為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會(huì)科學(xué)索引目錄(CSSCI)來源期刊(2014-2015年),也是《中國學(xué)術(shù)期刊(光盤版)》和《中國期刊網(wǎng)》的期刊源,曾榮獲首屆《CAJ-CD規(guī)范》執(zhí)行優(yōu)秀期刊獎(jiǎng)。她還是《中國核心期刊數(shù)據(jù)庫》收錄期刊,在"萬方數(shù)據(jù)—數(shù)字化期刊群"全文上網(wǎng)。《大學(xué)教育科學(xué)》堅(jiān)持理論探討與應(yīng)用研究相結(jié)合,為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fā)展服務(wù),為教育科學(xué)的繁榮服務(wù)。
關(guān)鍵詞:高等教育大眾化;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成就;缺憾;反思
一、引言
起步于世紀(jì)之交的高等教育大眾化是“我國高等教育的歷史性跨越”,是“中國教育發(fā)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20年來,伴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進(jìn)程,中國高等教育事業(yè)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高等教育規(guī)模躍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發(fā)展與改革各項(xiàng)成就舉世矚目。
馬丁·特羅認(rèn)為,當(dāng)高等教育的毛入學(xué)率達(dá)到15%這個(gè)區(qū)間的時(shí)候,“高等教育的全部活動(dòng)都要發(fā)生變化”[2]。他還就高等教育觀念、功能、管理、課程等10個(gè)方面所發(fā)生的質(zhì)的變化進(jìn)行了專門闡述。這10個(gè)方面并沒有涉及到高等教育研究[3]。馬丁·特羅的“疏忽”,為我們探討高等教育大眾化與高等教育研究的關(guān)系提供了機(jī)會(huì)。
作為一個(gè)具有鮮明實(shí)踐性、應(yīng)用性特征的研究領(lǐng)域,高等教育研究與高等教育事業(yè)理應(yīng)呈現(xiàn)同頻共振的關(guān)系。然而,我們至今并沒有看到關(guān)于高等教育大眾化影響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相關(guān)文獻(xiàn),兩者的關(guān)系似乎不言自明,但實(shí)際情況或許比我們想象的更復(fù)雜。本文結(jié)合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歷史及相關(guān)數(shù)據(jù)的梳理,系統(tǒng)分析和反思高等教育大眾化對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影響,以期加深學(xué)術(shù)界對這一論題的認(rèn)識(shí)。
二、成就
20世紀(jì)70年代末,中國高等教育研究伴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應(yīng)運(yùn)而生。1984年,高等教育學(xué)科正式創(chuàng)建。此后,中國高等教育研究進(jìn)入快速發(fā)展的軌道,呈現(xiàn)出蓬勃發(fā)展的勢頭。到90年代中期,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規(guī)模(研究機(jī)構(gòu)、人員、刊物、成果等)攀升至世界第一,中國因此被國外高等教育研究界譽(yù)為“高等教育研究大國”。
世紀(jì)之交的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進(jìn)一步推動(dòng)了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大發(fā)展,延續(xù)了自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快速擴(kuò)張態(tài)勢。
(一)研究成果增長迅猛
規(guī)模和數(shù)量擴(kuò)張是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顯著特征,也是大眾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研究的顯著特征。從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看,20年來無論是論文數(shù)還是課題數(shù)都得到了極為迅猛的增長。
我們通過中國知網(wǎng)的檢索發(fā)現(xiàn)①,1980~1999年,收入社會(huì)科學(xué)II輯——高等教育的論文總數(shù)為35.1萬篇,年均1.8萬篇。而2000~2019年,這一數(shù)據(jù)達(dá)到219.9萬篇,年均達(dá)到11萬篇,增幅超過526.5%。如果把近20年再細(xì)分為兩個(gè)十年的話,則發(fā)現(xiàn)高等教育論文數(shù)繼續(xù)呈現(xiàn)急速增長的態(tài)勢。2000~2009年為68.5萬篇,而2010~2019年達(dá)到151.4萬篇,增幅達(dá)到121.0%。
通過中國知網(wǎng)對“高等教育”“高等學(xué)校”“大學(xué)”“大學(xué)生”四個(gè)詞進(jìn)行“篇名”檢索,也能看到高等教育論文的迅速增長。為了檢索的準(zhǔn)確性,我們?nèi)匀话褭z索范圍限定在社會(huì)科學(xué)II輯——高等教育類。經(jīng)過檢索,我們發(fā)現(xiàn)包含上述四詞篇名的論文,1980~1999年分別為1 0277、3 780、34 536、11 159篇,2000~2019年分別達(dá)到54 533、12 520、445 057、221 375篇,增幅分別達(dá)到430.6%、231.2%、1188.7%、1183.8%。
如果從代表高等教育研究專業(yè)水平的角度看,大眾化后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也呈現(xiàn)顯著的增幅。為此,我們又選擇了兩個(gè)觀測指標(biāo)。
一是核心期刊高等教育研究發(fā)文數(shù)量。我們通過中國知網(wǎng)的檢索發(fā)現(xiàn):1980~1999年,全國中文核心期刊高等教育論文為2.1萬篇;2000~2019年,這一數(shù)據(jù)達(dá)到20.7萬篇,增幅為885.7%。
二是全國教育科學(xué)規(guī)劃課題中高等教育課題的數(shù)量。據(jù)統(tǒng)計(jì),全國教育科學(xué)“六五”規(guī)劃課題中,高等教育課題還只有11項(xiàng),后來才逐步增加。高等教育大眾化前的“六五”至“九五”規(guī)劃課題中,高等教育課題總數(shù)為308項(xiàng),而大眾化后的“十五”至“十三五”規(guī)劃課題中,高等教育課題總數(shù)已經(jīng)達(dá)到3 257項(xiàng),增幅達(dá)到957.5%。
(二)研究隊(duì)伍擴(kuò)充迅速
1998年,中國高等教育學(xué)學(xué)科創(chuàng)始人潘懋元發(fā)文列舉了當(dāng)時(shí)全國的高等教育研究機(jī)構(gòu)和隊(duì)伍的數(shù)據(jù):“高等教育研究機(jī)構(gòu),僅就全日制普通高等學(xué)校所設(shè)的,不完全統(tǒng)計(jì)約700所,加上成人高等學(xué)校和各省、各行業(yè)所設(shè)的,約800所。”“高等教育專職研究人員約3 000名,兼職研究人員數(shù)以萬計(jì)。”[4]從21世紀(jì)開始,高等教育大眾化推動(dòng)了高等學(xué)校的大幅增加,高等學(xué)校的數(shù)量從1999年的1 942所增長到2019年的2 688所,其中相當(dāng)一部分新建高校都設(shè)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機(jī)構(gòu),使高等教育研究人員數(shù)量有了較大增加。我們通過知網(wǎng)對高等教育論文作者的單位進(jìn)行模糊檢索(檢索詞分別是高等教育、高教、教育學(xué)院、教育科學(xué)、教育研究),剔除重復(fù)以及有關(guān)學(xué)校、專業(yè)、學(xué)科介紹的論文后,發(fā)現(xiàn)1999年發(fā)表高等教育論文的專職研究人員(包括研究生)為993人,兼職研究人員30 568人;而2019年,這一數(shù)據(jù)分別達(dá)到5 371人、162 194人,增幅分別達(dá)到440.9%、430.6%。研究隊(duì)伍的增幅與研究成果的增幅呈現(xiàn)正相關(guān),這在很大程度上證明這樣的一個(gè)邏輯:高等教育規(guī)模的擴(kuò)大,導(dǎo)致了高等教育研究隊(duì)伍數(shù)量的擴(kuò)充,進(jìn)而推動(dòng)了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數(shù)量的擴(kuò)充。
這里值得一說的是,大眾化后高等教育學(xué)研究生教育的快速發(fā)展。據(jù)統(tǒng)計(jì),1998年全國高等教育學(xué)僅有博士點(diǎn)4個(gè)、碩士點(diǎn)23個(gè),在校生不足200人。21世紀(jì)以來,高等教育大眾化推動(dòng)了研究生教育的大發(fā)展,高等教育學(xué)的博士點(diǎn)和碩士點(diǎn)在各地不斷創(chuàng)建。到2003年底,全國高等教育學(xué)博士點(diǎn)就達(dá)到10個(gè),在讀博士生達(dá)到170多人;全國高等教育學(xué)碩士點(diǎn)達(dá)到56個(gè),在讀碩士生超過1 000人[5](p295-300)。到2015年,全國高等教育研究機(jī)構(gòu)設(shè)博士點(diǎn)35個(gè)、碩士點(diǎn)103個(gè)[6]。通過中國知網(wǎng)碩博論文數(shù)據(jù)庫,我們可以看到大眾化后高等教育學(xué)研究生教育的發(fā)展:2000~2019年,被收入該庫的高等教育學(xué)學(xué)位論文達(dá)到7 135篇。一大批經(jīng)過高等教育學(xué)專門訓(xùn)練的博士、碩士成為高等教育學(xué)科建設(shè)的新生力量,為高等教育專業(yè)研究提供源源不斷的動(dòng)力。
(三)研究主題多樣化趨勢基本形成
為了觀測大眾化前后中國高等教育研究主題的變化,我們利用中國知網(wǎng)的高級(jí)檢索功能對“高等教育”“高等學(xué)校”“大學(xué)”“大學(xué)生”四個(gè)關(guān)鍵詞進(jìn)行“篇名”檢索(檢索范圍限定在社會(huì)科學(xué)II輯——高等教育類),通過文獻(xiàn)可視化處理發(fā)現(xiàn),1980~1999年,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界的熱點(diǎn)主題是:市場經(jīng)濟(jì)(13.9%)、社會(huì)主義(10.0%)、當(dāng)代大學(xué)生(8.9%)、大學(xué)畢業(yè)生(7.62%)、高等教育改革(5.8%)、思想政治工作(4.5%)、知識(shí)經(jīng)濟(jì)(4.6%)、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3.2%)、高等教育事業(yè)(3.0%)、素質(zhì)教育(2.76%)等。2000~2019年,伴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進(jìn)程,高等教育研究的熱點(diǎn)發(fā)生了明顯變化,思想政治教育(25.6%)位居第一,當(dāng)代大學(xué)生(10.9%)、大學(xué)畢業(yè)生(6.3%)、素質(zhì)教育(2.1%)等主題的比例也相應(yīng)地發(fā)生了變化,并增加了大學(xué)生就業(yè)(5.5%)、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3.0%)、大學(xué)生創(chuàng)業(yè)(2.8%)、創(chuàng)業(yè)教育(2.6%)、人才培養(yǎng)(2.3%)、教學(xué)改革(2.2%)、創(chuàng)新能力(2.0%)等多個(gè)新的研究主題。
如果從代表高等教育研究專業(yè)水平的角度看,大眾化后的高等教育研究領(lǐng)域也有明顯變化。高等教育大眾化前,高校教學(xué)與管理等相對微觀層面的研究占據(jù)高等教育研究的主導(dǎo)地位。根據(jù)陳學(xué)飛主編的《中國高教研究50年(1949~1999)》一書中對1978~1998年高等教育研究領(lǐng)域著作數(shù)量的統(tǒng)計(jì)發(fā)現(xiàn),有關(guān)高等學(xué)校課程與教學(xué)、德育、管理等涉及高等教育微觀領(lǐng)域的著作比例高達(dá)83%,而有關(guān)高等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經(jīng)濟(jì)與財(cái)政等宏觀領(lǐng)域的著作比例僅為27%[5](p309)。高等教育大眾化后,高等教育體制、機(jī)制、結(jié)構(gòu)等宏觀問題受到更多學(xué)者的重視,高等教育研究呈現(xiàn)宏觀與微觀研究并舉的局面。
我們利用1980~2019年《高等教育研究》的大樣本數(shù)據(jù)來進(jìn)行分析發(fā)現(xiàn):高等教育大眾化前,高等教育研究中課程與教學(xué)(23%)、高校內(nèi)部管理(12%)等微觀研究領(lǐng)域所占比較大,而高等教育體制與結(jié)構(gòu)(9.5%)、高等教育基本理論(10%)等宏觀問題比例較小;高等教育大眾化后,高等教育研究的重點(diǎn)發(fā)生了顯著變化,主要圍繞高等教育體制與結(jié)構(gòu)(23%)、高等教育基本理論(13%)、課程與教學(xué)(13%)、國際與比較高等教育(13%)、高校內(nèi)部管理(13%)等多個(gè)主題進(jìn)行探究,高等教育研究已不再偏重某些研究領(lǐng)域,而是致力于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雙翼齊飛。
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大眾化催生了一系列與大眾化直接相關(guān)的課題研究,高等教育質(zhì)量保障、大學(xué)生就業(yè)、現(xiàn)代大學(xué)治理、高等教育運(yùn)行機(jī)制等課題日益受到關(guān)注,極大地?cái)U(kuò)展了高等教育研究領(lǐng)域。以大學(xué)生就業(yè)為例,在中國知網(wǎng)通過“大學(xué)生”和“就業(yè)”兩個(gè)篇名進(jìn)行復(fù)合檢索發(fā)現(xiàn),1980~1999年的相關(guān)論文為134篇,而2000~2019年的相關(guān)論文達(dá)到23 597篇,增幅達(dá)到175.1倍。
(四)研究方法多元化格局初現(xiàn)端倪
涂爾干指出:“一門學(xué)科如欲發(fā)展成一個(gè)合乎科學(xué)的學(xué)術(shù),必須有科學(xué)的研究方法。”[7]同樣,一門學(xué)科的進(jìn)步集中地反映在該學(xué)科的方法變化上。眾所周知,思辨方法長期占據(jù)著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主導(dǎo)地位,而我們采取的思辨還主要是基于個(gè)人經(jīng)驗(yàn)的感悟性思辨,不能構(gòu)成嚴(yán)格意義的科學(xué)方法。高等教育大眾化后,高等教育系統(tǒng)不斷擴(kuò)大,高等教育制度和結(jié)構(gòu)趨于復(fù)雜和多元,高等教育與其他社會(huì)子系統(tǒng)關(guān)系更為密切,高等教育問題往往需要通過多個(gè)維度、多種方法、多種范式進(jìn)行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這直接推動(dòng)了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界“方法意識(shí)”的覺醒,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多元化格局初現(xiàn)端倪。
一是多學(xué)科研究方法受到廣泛倡導(dǎo)。從國際經(jīng)驗(yàn)看,高等教育多學(xué)科研究方法的形成正是受到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推動(dòng)。二十世紀(jì)五六十年代,由于高等教育規(guī)模的擴(kuò)張,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界發(fā)現(xiàn)“高等教育各方面的問題是如此之多,又如此多樣化,任何一位作者都難以孤軍作戰(zhàn)”[8]。于是,西方高等教育研究者們開始求助于多學(xué)科的理論與方法,由此掀起了一股多學(xué)科研究的浪潮。21世紀(jì)以來,多學(xué)科研究方法在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界的廣泛倡導(dǎo),不僅受到西方研究范式的啟發(fā),更是受到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推動(dòng)。2001年,潘懋元在他主編的《多學(xué)科觀點(diǎn)的高等教育研究》一書中就明確地提出:“多學(xué)科研究方法可能就是高等教育學(xué)的獨(dú)特方法。”[9]
本文第一作者曾對1980~2012年《高等教育研究》論文的引文進(jìn)行定量分析,發(fā)現(xiàn)21世紀(jì)以來高等教育研究論文的引文中普通教育學(xué)的比例從20世紀(jì)90年代的30%下降到22%,而“隨著多學(xué)科研究范式受到重視,教育學(xué)之外的其他學(xué)科的知識(shí)和方法受到更多高等教育研究學(xué)者的青睞,社會(huì)學(xué)和哲學(xué)的比例分別達(dá)到7.79%和7.09%,經(jīng)濟(jì)學(xué)、歷史學(xué)、政治學(xué)、管理學(xué)等學(xué)科的比例也比90年代有了提高”[10](p109-114)。
不過,多學(xué)科研究目前還處于倡導(dǎo)階段,“不同的學(xué)科只是針對自己關(guān)注的高等教育問題各自進(jìn)行研究,缺乏多學(xué)科的協(xié)同研究”[10](p122),特別是對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論的改造效果還有待觀察。
二是實(shí)證研究方法受到空前重視。自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啟動(dòng)以來,實(shí)證研究方法開始受到越來越多學(xué)者的重視,運(yùn)用實(shí)證研究的成果不斷增加,實(shí)證方法的使用也趨于規(guī)范。2017年1月,《教育實(shí)證研究華東師范大學(xué)行動(dòng)宣言》的發(fā)布,更是將實(shí)證研究的意義推向一個(gè)新的高度。
為了探討大眾化前后中國高等教育實(shí)證研究的應(yīng)用狀況,我們以《高等教育研究》1980~2019年所刊發(fā)的論文為樣本,對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分析:大眾化前,《高等教育研究》刊發(fā)的2 009篇文章中,僅有88篇為實(shí)證性文章,占比僅4.4%,思辨研究則高達(dá)95.6%,并且,根據(jù)SPASS卡方檢驗(yàn)的結(jié)果表明,1980~1999年之間《高等教育研究》發(fā)表的學(xué)術(shù)論文所采用的實(shí)證方法沒有顯著差異(χ2=20.73,P=0.29);大眾化后,《高等教育研究》刊發(fā)的3 602篇中,有743篇為實(shí)證論文,占比達(dá)20.6%,思辨研究比例為79.4%,同樣,卡方檢驗(yàn)結(jié)果顯示,2000~2019年之間《高等教育研究》發(fā)表的學(xué)術(shù)論文所采用的實(shí)證方法發(fā)生了顯著變化(χ2=148.50,P=0.00)。
同時(shí),高等教育大眾化后,實(shí)證研究方法的層次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大眾化前,《高等教育研究》發(fā)表的定量研究論文中采用描述性統(tǒng)計(jì)分析、方差分析、相關(guān)分析等初階統(tǒng)計(jì)方法的比例都較高,比例為83.0%,而采用回歸分析、路徑分析、結(jié)構(gòu)方程模型、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分析、分層線性模型等中高階統(tǒng)計(jì)方法的比例比較低,分別為15.3%和1.7%;大眾化后,中高階統(tǒng)計(jì)方法的比例顯著提升,二者合計(jì)為57.3%,超過了初階統(tǒng)計(jì)方法42.7%的比例。
三是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被引入高等教育研究領(lǐng)域。高等教育大眾化前,高等教育研究一般采用文獻(xiàn)法、調(diào)查法、比較法、統(tǒng)計(jì)法等常規(guī)教育研究方法。但我們通過知網(wǎng)的檢索發(fā)現(xiàn),大眾化后的2000~2019年間,行動(dòng)研究法(668篇)、內(nèi)容分析法(405篇)、人種志研究法(318篇)、文本分析法(199篇)、田野調(diào)查法(176篇)、案例分析法(160篇)、話語分析法(122篇)、德爾菲法(68篇)、引文分析法(62篇)、解釋結(jié)構(gòu)模型法(39篇)等幾十種過去不常用的研究方法受到中國高等教育研究者的重視。
三、缺憾
從上述論述看,高等教育大眾化推動(dòng)了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大發(fā)展,特別是隨著高等教育研究規(guī)模急劇擴(kuò)大,中國成了名副其實(shí)的高等教育研究大國。但從20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發(fā)展的總體情況看,除了研究方法的變革外,高等教育研究的發(fā)展更多是量的擴(kuò)充,而不是質(zhì)的改變。毋庸諱言,高等教育大眾化并未從根本上推動(dòng)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全面轉(zhuǎn)型升級(jí)。
(一)學(xué)科建設(shè)停滯不前
雖然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起步晚于西方,但中國創(chuàng)建了“高等教育學(xué)”,從而使得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有了鮮明的學(xué)科指向。從二十世紀(jì)八九十年代的情況看,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沿著學(xué)科建設(shè)和問題研究兩條軌道蓬勃展開,形成了兩條軌道相互促進(jìn)、相得益彰的繁榮局面。特別是1993年成立了以高等教育理論研究和學(xué)科建設(shè)為主要任務(wù)的“全國高等教育學(xué)研究會(huì)”,該研究會(huì)的前三屆年會(huì)都以高等教育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為主題,取得了豐碩成果。
然而,這一局面在21世紀(jì)后未能得到延續(xù),高等教育大眾化使高等教育各類新問題層出不窮,高等教育問題研究受到一邊倒的關(guān)注,高等教育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自然就被冷落了,原來的“雙軌運(yùn)行”幾乎變成了問題研究的“單軌獨(dú)行”。
從作為主干學(xué)科的高等教育學(xué)看,我們今天熟悉的高等教育學(xué)著作,如潘懋元主編的中國第一部《高等教育學(xué)》、鄭啟明和薛天祥主編的《高等教育學(xué)》、田建國編寫的《高等教育學(xué)》、胡建華等合著的《高等教育學(xué)新論》、潘懋元主編的《新編高等教育學(xué)》都是二十世紀(jì)八九十年代的成果。21世紀(jì)后,除了薛天祥和王偉廉2001年分別主編的兩部《高等教育學(xué)》在學(xué)科體系上有所創(chuàng)新外,其后新出版的高等教育學(xué)著作在理論和體系上鮮有特別的貢獻(xiàn)。
從高等教育學(xué)分支學(xué)科看,絕大多數(shù)分支學(xué)科是二十世紀(jì)八九十年代創(chuàng)建的,如創(chuàng)建于80年代的高等教育管理學(xué)、高等教育史、比較高等教育、大學(xué)教學(xué)論、大學(xué)德育論等學(xué)科,創(chuàng)建于90年代的大學(xué)課程論、高等教育社會(huì)學(xué)、高等教育政治學(xué)、高等專科教育學(xué)等。這些分支學(xué)科在當(dāng)時(shí)都出版了專門論著,但到了21世紀(jì),很少聽說有新的分支學(xué)科誕生,原有分支學(xué)科新出版的專著也不多見。
從高等教育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的相關(guān)研究看,二十世紀(jì)八九十年代高等教育研究界就圍繞高等教育學(xué)的學(xué)科性質(zhì)、對象、體系、方法等進(jìn)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和觀點(diǎn)。21世紀(jì)后,這方面的研究明顯處于沉寂狀態(tài),除了研究方法外,其他學(xué)科建設(shè)的新成果不多。鄔大光等人對1994~2014年高等教育學(xué)科(研究)有關(guān)文獻(xiàn)進(jìn)行統(tǒng)計(jì)發(fā)現(xiàn),“高等教育學(xué)科(研究)類文獻(xiàn)有相對萎縮的跡象”[11]。我們通過中國知網(wǎng)的檢索發(fā)現(xiàn),2000~2019年以“高等教育學(xué)”為篇名的論文只有388篇,以“高等教育研究”為篇名的論文952篇,兩項(xiàng)合計(jì)1 340篇,占同期高等教育論文總數(shù)的5.8%,可謂真正的“小眾”和“冷門”。
(二)制度建設(shè)喜憂參半
研究制度“是規(guī)范特定學(xué)科研究的行為準(zhǔn)則體系和支撐學(xué)科發(fā)展、完善的基礎(chǔ)結(jié)構(gòu)體系”[12]。一般意義上,一個(gè)學(xué)科或研究領(lǐng)域的研究制度包含專業(yè)研究人員、研究機(jī)構(gòu)與組織、研究刊物、研究成果、研究基金、學(xué)位點(diǎn)等。從前文的論述中看,這些研究制度的主要指標(biāo)在高等教育大眾化后呈現(xiàn)不同程度的增長,這是令人欣喜的一面,但越過數(shù)據(jù)探討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就會(huì)發(fā)現(xiàn),20年來,高等教育研究制度建設(shè)中也出現(xiàn)了一些令人憂慮的問題和現(xiàn)象。
一是高等教育專業(yè)研究機(jī)構(gòu)的異化現(xiàn)象。雖然有統(tǒng)計(jì)表明,“全國現(xiàn)有1 300多所高等教育研究機(jī)構(gòu)”[13],比高等教育大眾化前的800所增長不少,但大批的高等教育研究機(jī)構(gòu)已經(jīng)不再稱“高等教育研究所”(簡稱“高教所”),其中一批有較高專業(yè)水平的高教所改名“教育學(xué)院”。據(jù)了解,全國在二十世紀(jì)八九十年代就已經(jīng)取得高等教育學(xué)碩士點(diǎn)和博士點(diǎn)的老牌高教所,目前還未被改為教育學(xué)院或教育研究院的已寥寥無幾。表面看,“所改院”屬于做大做強(qiáng),實(shí)際上,“所改院”后的很多研究院,其研究領(lǐng)域已經(jīng)從高等教育拓展到包括基礎(chǔ)教育在內(nèi)的大教育,高等教育研究資源和力量實(shí)際被稀釋或弱化了。同時(shí),有更大一部分高教所被并入學(xué)校其他學(xué)院或機(jī)構(gòu),失去了相對獨(dú)立的建制和地位,有的高教所就只剩下一個(gè)門牌。
二是高等教育學(xué)學(xué)位點(diǎn)的矮化現(xiàn)象。“矮化”一詞或許有所不當(dāng),但描繪這些年高等教育學(xué)學(xué)科點(diǎn)的地位變化比較形象。大眾化前,高等教育學(xué)碩士點(diǎn)和博士點(diǎn)雖然數(shù)量不多,但都是相對獨(dú)立的二級(jí)學(xué)科,即在招生和培養(yǎng)的各環(huán)節(jié)都獨(dú)立于教育學(xué)一級(jí)學(xué)科之外。大眾化后,雖然高等教育學(xué)碩士點(diǎn)和博士點(diǎn)成倍增加,但隨著學(xué)位與研究生教育的改革,目前絕大多數(shù)高等教育學(xué)的碩士點(diǎn)和博士點(diǎn)都淪為教育學(xué)一級(jí)學(xué)科點(diǎn)的一個(gè)“方向”,失去了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的相對獨(dú)立性,不僅高等教育學(xué)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的質(zhì)量受到影響,而且培養(yǎng)特色也面臨喪失的危險(xiǎn)。
三是高等教育研究刊物的泛化現(xiàn)象。學(xué)術(shù)刊物是研究的“學(xué)術(shù)脊梁”,是研究成果發(fā)表最重要的專業(yè)平臺(tái)。大眾化后,雖然高等教育專業(yè)刊物的總體數(shù)量變化不大,但某些刊物的高等教育研究屬性發(fā)生了變化,有的高等教育專業(yè)刊物選題的面擴(kuò)大到整個(gè)教育領(lǐng)域,有的甚至干脆把刊名中的“高等”兩字拿掉。如《上海高教研究》改名為《教育發(fā)展研究》,《遼寧高等教育研究》改名為《現(xiàn)代教育管理》,《高等師范教育研究》改名為《教師教育研究》,這些刊物改名后都把研究領(lǐng)域擴(kuò)大到教育的各個(gè)層次。
(三)能力建設(shè)差強(qiáng)人意
大眾化后,高等教育事業(yè)的大發(fā)展對高等教育研究的需要更為迫切,高等教育研究也為加強(qiáng)服務(wù)能力進(jìn)行了不懈努力,包括前文所論的各項(xiàng)成就,其出發(fā)點(diǎn)之一都是為了提升自身解決問題、服務(wù)實(shí)踐的水平和能力。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為大眾化時(shí)代的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xiàn)。
但從實(shí)際情況和效果看,高等教育大眾化并沒有把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服務(wù)能力建設(shè)推向一個(gè)新的高度和層次,高等教育研究在國家高等教育決策中的影響力并沒有實(shí)質(zhì)性的增強(qiáng)。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巖甚至認(rèn)為,這些年高等教育研究學(xué)者“參與的力度和對決策施加的影響力越來越弱了”[14]。
一是應(yīng)答性研究多,前瞻性研究少。理論研究服務(wù)實(shí)踐,并不僅僅是理論跟著實(shí)踐跑,實(shí)踐需要什么,理論就解決什么,而是理論要主動(dòng)啟發(fā)實(shí)踐、引領(lǐng)實(shí)踐,對實(shí)踐有所預(yù)警、有所前瞻。正如德國著名高等教育研究專家泰希勒所言:“不管社會(huì)預(yù)測的已知風(fēng)險(xiǎn)和劣勢如何,社會(huì)科學(xué)都必須應(yīng)對未來,因?yàn)樗鼈兊膶?shí)際意義在于塑造未來的條件。”[15]高等教育研究的前瞻性也尤為必要。例如在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智庫的高級(jí)目標(biāo)就是預(yù)測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fā)展趨勢、可預(yù)見的問題及改進(jìn)策略”[16]。從總體情況看,大眾化后中國高等教育研究之于實(shí)踐和決策的前瞻性、引領(lǐng)性并沒有得到有效改觀,高等教育研究滯后于高等教育決策的情況仍屬常態(tài),多數(shù)的研究還只是基于現(xiàn)實(shí)問題的應(yīng)答性研究和政策頒布后的“馬后炮”研究。如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提出“加快建設(shè)一流大學(xué)和一流學(xué)科”,這是一個(gè)對近十年中國高等教育發(fā)展影響深遠(yuǎn)的改革舉措。我們通過知網(wǎng)選擇“一流大學(xué)”和“一流學(xué)科”兩個(gè)詞進(jìn)行主題復(fù)合檢索發(fā)現(xiàn),《規(guī)劃綱要》頒布前的2000~2009年相關(guān)論文只有78篇,而《規(guī)劃綱要》頒布后的2010~2019年此類論文達(dá)到1 607篇。另據(jù)我們對全國教育科學(xué)“十五”至“十三五”規(guī)劃高等教育課題的分析發(fā)現(xiàn),大體屬于前瞻性的課題只有315項(xiàng),占比10.0%。
二是詮釋性研究多,批判性研究少。高等教育研究界對“研究服務(wù)實(shí)踐”的職能存在誤讀,“很多人根本想不到批判也是服務(wù)實(shí)踐的一種重要形式,甚至認(rèn)為批判與服務(wù)是對立的,導(dǎo)致‘研究服務(wù)實(shí)踐實(shí)際變成為現(xiàn)行政策做詮釋、為領(lǐng)導(dǎo)意見做注腳的‘御用研究”[17]。長期以來,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中的批判性研究比例很小。我們以《高等教育研究》1980~2019年所刊發(fā)的論文為樣本,對其批判性論文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分析發(fā)現(xiàn):在大眾化前的1980~1999年,《高等教育研究》刊發(fā)的2 009篇文章中,僅有60篇大體屬于批判性論文,占比3.0%;大眾化后的2000~2019年,《高等教育研究》刊發(fā)的3 602篇中,有116篇大體屬于批判性論文,占比3.2%,比例幾乎沒有增加。
三是淺表性研究多,深層次研究少。大眾化后,雖然高等教育研究服務(wù)實(shí)踐的意識(shí)有很大提升,結(jié)合實(shí)踐需要的應(yīng)用型課題和成果也有顯著增加,以全國教育科學(xué)規(guī)劃課題為例,“十五”至“十三五”規(guī)劃中高等教育類應(yīng)用型課題達(dá)到2 417項(xiàng),占比達(dá)到76.8%。但從總體情況看,大眾化后高等教育研究服務(wù)實(shí)踐的力度和有效性仍然不足,無論是在政府的高等教育決策,還是在高校內(nèi)部決策中,高等教育研究者往往處于“缺位”狀態(tài),其關(guān)鍵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研究與實(shí)踐的結(jié)合不深入、不具體,浮于表面,相當(dāng)一部分研究成果的宏大敘事特征仍然十分明顯,存在脫離實(shí)際的弊病。正如米爾斯所言:“宏大理論的根本原因是一開始就選擇了特別一般化的思考層次,導(dǎo)致其踐行者邏輯無法下降到觀察層次,如此缺乏對于真切問題的真實(shí)把握,又會(huì)加劇他們行文當(dāng)中顯露無遺的那種不切實(shí)際。”[18]即便這些年開始流行的實(shí)證研究也未能促進(jìn)高等教育研究的深入,一些學(xué)者篤信“統(tǒng)計(jì)主義”[19],為統(tǒng)計(jì)而統(tǒng)計(jì),為數(shù)據(jù)而數(shù)據(jù),看起來紛繁復(fù)雜的統(tǒng)計(jì)模型并沒有找到問題的癥結(jié),更沒有揭示真正的原理,對問題解決和決策參考的意義不大。
四、反思
總而言之,高等教育大眾化推動(dòng)了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大發(fā)展,但并未推動(dòng)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全面轉(zhuǎn)型升級(jí)。
前者的原因比較清晰,大眾化后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大發(fā)展,其動(dòng)力機(jī)制也在于高等教育的大發(fā)展。大眾化后的連續(xù)擴(kuò)招,促使中國迅速成為世界上高等教育規(guī)模最大的國家,高等教育事業(yè)發(fā)展對高等教育研究的需求空前旺盛,高等教育研究也進(jìn)而得到了一系列擴(kuò)張和變革。這一點(diǎn)與西方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后高等教育研究發(fā)展趨勢基本是一致的。“自1950年后,美國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層出不窮,與高等教育研究密切相關(guān)的學(xué)術(shù)期刊、經(jīng)典著作、研究學(xué)會(huì)都呈現(xiàn)專業(yè)化的趨勢。”[20]高等教育大眾化使美國不僅成為世界高等教育大國,更成為高等教育研究強(qiáng)國。二十世紀(jì)六七十年代,歐美其他發(fā)達(dá)國家紛紛邁開了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步伐,高等教育研究組織和機(jī)構(gòu)在歐美國家得到廣泛建立,高等教育研究人員和成果迅速增加,高等教育研究領(lǐng)域和主題得到快速擴(kuò)展,多學(xué)科研究方法得到廣泛應(yīng)用。
從某種意義看,高等教育大眾化既推動(dòng)了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量變,也推動(dòng)了高等教育研究的質(zhì)變,是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真正進(jìn)入專業(yè)化、制度化發(fā)展新階段的重要推動(dòng)力。相比而言,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更多是推動(dòng)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量變而非質(zhì)變,其中的原因耐人尋味。從表面看,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專業(yè)化、制度化進(jìn)程,在二十世紀(jì)八九十年代的精英教育時(shí)代就已經(jīng)基本完成,大眾化僅僅起到了錦上添花的作用,但從深層次原因看,作為政府行為的高等教育大眾化難以形成推動(dòng)高等教育研究變革的建構(gòu)性力量。
我們知道,中西方高等教育大眾化動(dòng)因和背景不同。潘懋元認(rèn)為,中國高等教育“從精英走向大眾, 首先并不是高等教育自身發(fā)展的主動(dòng)選擇, 而是社會(huì)發(fā)展推動(dòng)的結(jié)果”[21]。而所謂“社會(huì)發(fā)展推動(dòng)”在20世紀(jì)90年代中后期亞洲金融危機(jī)、國企改革、擴(kuò)大內(nèi)需等特殊歷史背景下,又彰顯出政府強(qiáng)力主導(dǎo)與推動(dòng)的顯著特征。因此,“西方國家的高等教育大眾化基本上是一個(gè)自然的過程”,“而我國的高等教育大眾化在總體上表現(xiàn)為一種國家的發(fā)展戰(zhàn)略和政府的行為”,“影響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進(jìn)程有許多因素,均取決于政府的制度性安排和政策調(diào)整”[22]。
政府強(qiáng)勢主導(dǎo)下的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過程,強(qiáng)調(diào)“國家對發(fā)展的責(zé)任意識(shí),以追求經(jīng)濟(jì)績效為起始目標(biāo),以國家能力對資源和組織的集中動(dòng)員為主要手段,以規(guī)模快速擴(kuò)大的外延式發(fā)展方式作為趕超的必然選擇”[23]。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制度性安排對高等教育發(fā)展起到了主導(dǎo)性、決定性的作用,而包含高等教育研究在內(nèi)的研究力量和學(xué)術(shù)力量在大眾化進(jìn)程中的作用相對薄弱。事實(shí)上,雖然遭遇百年不遇的高等教育大發(fā)展與大變革,中國高等教育研究仍難以從政府和大學(xué)層面得到更有力度、更具實(shí)質(zhì)性意義的重視和支持。同時(shí),政府主導(dǎo)下的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外延式發(fā)展方式對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發(fā)展方式也產(chǎn)生了直接影響。高等教育大眾化啟動(dòng)后,高等教育研究熱情被進(jìn)一步激活,由于高等教育研究選擇了外延式發(fā)展方式,高等教育研究論文數(shù)量雖然成倍增長,但包括制度建設(shè)、學(xué)科建設(shè)在內(nèi)的內(nèi)涵建設(shè)受到忽視,高等教育研究的地位、能力和品質(zhì)并沒有因?yàn)榇蟊娀玫劫|(zhì)的提升。
同時(shí),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對于突如其來的高等教育大眾化也準(zhǔn)備不足,其后的相關(guān)建設(shè)也沒有跟上大眾化的節(jié)奏。1999年國家擴(kuò)招政策出臺(tái)前,雖然高等教育研究界對于中國高等教育發(fā)展速度和規(guī)模有長達(dá)十多年的爭論,但無論是“控制發(fā)展論”還是“適度發(fā)展論”,都不支持高等教育大眾化。如果把1999年作為擴(kuò)招元年,往前看3年,即1996~1998年,中國知網(wǎng)上以“高等教育大眾化”為篇名的中文論文只有12篇,多數(shù)是介紹西方國家的大眾化情況,還有一篇是明確反對在中國推行高等教育大眾化,這從一個(gè)角度說明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對于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準(zhǔn)備不足。
二十年,彈指一揮間。在中國即將邁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時(shí)代的背景下,探討大眾化時(shí)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得與失、成就與缺憾,對于我們更好地探討和規(guī)劃普及化時(shí)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發(fā)展具有積極意義。
我們認(rèn)為,經(jīng)過40多年的連續(xù)擴(kuò)張,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量”已經(jīng)不是發(fā)展的主要矛盾。未來中國高等教育研究要從“外延式發(fā)展”轉(zhuǎn)向以“內(nèi)涵式發(fā)展”為主的道路,更加重視“質(zhì)”的建設(shè)與變革:一是加強(qiáng)學(xué)科建設(shè)力度,不斷完善高等教育學(xué)科的理論體系、方法體系及知識(shí)體系,用更加科學(xué)的理論指導(dǎo)日趨復(fù)雜的高等教育問題;二是要加大制度建設(shè)的力度,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研究學(xué)派,形成制度化、專業(yè)化的高等教育研究學(xué)術(shù)共同體;三是要加強(qiáng)能力建設(shè)的力度,強(qiáng)化“智庫”意識(shí),探索高等教育研究服務(wù)實(shí)踐的有效機(jī)制、長效機(jī)制,從大眾化時(shí)期的“跟跑”轉(zhuǎn)向普及化時(shí)代的“領(lǐng)跑”,增強(qiáng)高等教育研究的解釋力與前瞻性。簡言之,中國高等教育研究要充分吸收大眾化時(shí)期的經(jīng)驗(yàn)與教訓(xùn),主動(dòng)適應(yīng)普及化時(shí)代高等教育的變革需要,彰顯高等教育研究價(jià)值,為普及化時(shí)代中國高等教育強(qiáng)國建設(shè)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參考文獻(xiàn)
[1] 李均.中國高等教育政策史(1949~2009)[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306.
[2] 鄔大光.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的內(nèi)涵與價(jià)值——與馬丁·特羅教授的對話[J].高等教育研究,2003(06):6-9.
[3] [美]馬丁·特羅.從精英向大眾高等教育轉(zhuǎn)變中的問題[J].王香麗,譯.外國高等教育資料,1999(01):1-22.
[4] 潘懋元.潘懋元文集(卷二·理論研究上)[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82-183.
[5] 李均.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史[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6] 瞿振元.發(fā)揮群眾性學(xué)術(shù)社團(tuán)優(yōu)勢 在推進(jìn)高等教育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建功立業(yè)——中國高等教育學(xué)會(huì)第六屆理事會(huì)工作報(bào)告[J].中國高教研究,2017(08):3-9.
[7] 譚光鼎,王麗云.教育社會(huì)學(xué):人物與思想[J].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9:37.
[8] [美]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xué)[M].王承緒,等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38.
[9] 潘懋元.多學(xué)科觀點(diǎn)的高等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4.
[10] 李均.元高等教育學(xué)論稿[M].北京: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20.
[11] 鄔大光,王旭輝.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研究若干問題述評[J].教育研究,2015(05):73-88+113.
[12] 方文.社會(huì)心理學(xué)的演化:一種學(xué)科制度視角[J].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2001(06):126-136+207.
[13] 瞿振元.在2015年高等教育研究機(jī)構(gòu)協(xié)作組會(huì)暨第四屆全國優(yōu)秀高等教育研究機(jī)構(gòu)表彰會(huì)上的講話[EB/OL].(2015-5-17)[2020-07-22].http://www.hie.edu.cn/news_12577/20150507/t20150507_993206.shtml.
[14] 吳巖.建設(shè)高等教育智庫聯(lián)盟 推動(dòng)高等教育改革實(shí)踐[J].高等教育研究,2017(11):1-10.
[15] Teichler U.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J].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2003(03):171-185.
[16] 袁琳,王瑩.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智庫:職能、特點(diǎn)與啟示[J].現(xiàn)代教育管理,2014(04):13-18.
[17] 李均,陳露.重建批判之維[J].大學(xué)教育科學(xué),2014(02):16-21.
[18] [美]C.賴特·米爾斯.社會(huì)學(xué)的想象力[M].李康,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7:46.
[19] 李均.教育實(shí)證研究不可陷入“統(tǒng)計(jì)主義”窠臼[J].高等教育研究,2018(11):64-70.
[20] [美]萊斯特·古德柴爾德.在美國作為一個(gè)研究領(lǐng)域的高等教育:歷史、學(xué)位項(xiàng)目與知識(shí)基礎(chǔ)[J].北京大學(xué)教育評論,2011(04):10-40+182.
[21] 潘懋元,肖海濤.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結(jié)構(gòu)與體系變革[J].高等教育研究,2008(05):26-31.
[22] 鄔大光.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問題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4.
[23] 梁彤,賈永堂.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道路的歷史考察——基于發(fā)展型政府理論的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9(04):14-22.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