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濫用職權是行政法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其審查標準也一直是學界爭議的焦點問題。但立法的模糊、學說的多元以及濫用職權本身語義上的不明晰共同導致了實踐中界定濫用職權審判標準的困境。在現有學術觀點的基礎上對最高院的審判案例進行整理分析,得出“主觀目的不正當”這一審查標準。并結合全國高院的實踐判決,針對審判過程中出現的并用、該用不用以及擴大適用等問題,提出依靠原則性審查技術的適用鼓勵法官大膽進行說理,及時規范指導案例以防止司法審查恣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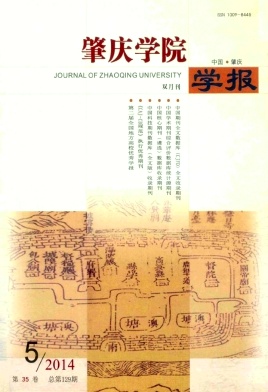
于中慧, 肇慶學院學報 發表時間:2021-07-19
關鍵詞:濫用職權;主觀目的;原則性審查
為監督經濟生活中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以權謀私的違法行為,向被侵犯合法權益的公民提供救濟手段,“濫用職權”這一條款寫入了1989 年制定的《行政訴訟法》中[1] 。人民法院可以通過這一條款審查行政機關的裁量權,通過撤銷的方式對其作出一定限制,以保護公民的權利。2014年行政訴訟法修改時增加“明顯不當”這一條款,使其與 “濫用職權”并列,作為人民法院判決撤銷具體行政行為的一種情形。不過,我國行政訴訟法僅是粗略地規定了這兩個條款,將其與“主要證據不足、超越職權”等四種情形并列,并未進一步明確二者所對應的行政裁量之司法審查標準,這便構成了我國 “濫用職權”審查的模糊性立法。同時,學界針對 “濫用職權”的說法多元化,并未形成一個較為統一的標準。2014年《行政訴訟法》修改后,厘清濫用職權的內涵與外延,規范司法實踐中的審判標準顯得尤為重要。因此,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書為研究對象,結合相關學術理論對其進行評析,探索司法審查中行政訴訟濫用職權的裁判標準。
一、最高院案例選取與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書是本文所選取的研究對象,為了盡可能全面完善地搜集整理研究樣本,筆者在北大法寶上以“濫用職權”為關鍵詞,搜索最高人民法院所做的相關行政判決書,至2020年底,共檢索到44篇。筆者認為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公報案例以及最高院行政庭整理編纂的中國行政審判案例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最高法院在“濫用職權”案件中的態度,在實踐中具有很強的指導性、代表性[2] 。因此筆者也將其納入研究范圍,經過逐一研讀,剔除掉其中僅在訴訟請求中提到濫用職權以及未對“濫用職權”進行實質性說理的案件,整理后共剩下12篇典型案例。將其按照時間順序進行排列,具體見表1。
(一)違背法律授權目的,具有非法意圖
案例一中,原告謝培新主張被告永和鄉人民政府違反法律及地方性法規的規定,超出國家規定的標準,強行性向農民征收社會以及生產性的服務費用,故而向法院請求撤銷被告發出的不合理的負擔通知。樂至縣人民法院審查后認為:根據《國務院條例》以及《四川省條例》的相關規定,農民每年度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上交的集體提留以及相關費用的總額,不得高于上一年農民人均凈收入的5%。依此標準,原告 1992 年人均應負擔 18.90 元。而根據實際中原告所收到的負擔通知單所列費用,人均負擔費用達到38.41元,占上一年人均純收入的 10%,遠高于國家所規定負擔的一倍。由此,法院認為被告永和鄉人民政府向原告謝培新收取的相關費用,違反了法律及地方性法規規定的取之有度、總額控制、定項限額的原則,具有任意性和隨意性。其行為符合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2、4、5目所規定的適用法律、法規錯誤,超越職權和濫用職權,依法應予以撤銷。
在案例七中,1997 年 8 月 26 日,上訴人潘龍泉等人因聚眾打麻將等涉嫌賭博行為被新沂市公安局發現,因潘龍泉屬新沂市公安局民警,執法人員于當日僅對其他兩名參加打麻將人員作出了治安處罰。之后,被上訴人新沂市公安局于2007年1月 31日對上訴人潘龍泉再次作出被訴的治安處罰決定。徐州市中院審理后認為,被訴的治安處罰行為既不符合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中所規定的公安機關辦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要求,也違背了我國《行政處罰法》的立法精神。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作出的公安行政處罰決定不僅違反了法定程序,也屬于濫用職權,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3目、第5目之規定,應予撤銷。
在上述兩個案件中,法院在論證行政機關“濫用職權”時,均將違背法律授權目的作為審查裁判的基礎。在案例一中,法律法規明確規定了取之有度的原則。在案例七中,法律法規缺少對行政機關未在法定期限內作出處罰法律后果的規定。但行政機關在無正當理由的情況下,超過法定追究時限進行處罰,損害了時效制度所維護的社會安定性,同樣也被法院判定屬于濫用職權的情形。
案例一與案例七中所體現的法院說理邏輯與 “違反授權目的說”相似。該說提出于1989年我國《行政訴訟法》頒行不久之時,認為濫用職權是指行政機關所實施的具體行政行為雖在權限范圍內,但卻違背法律法規所設定的目的與精神[3] 。此種定義的提出與當時學界流行的行政訴訟審查標準有關,即行政訴訟包含兩種審查標準:合法性審查與合理性審查。該說認為1989年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款中,前四項屬于合法性審查標準,而濫用職權適用于合理性審查標準。這一說法的提出雖具有一定的開創性意義,但卻難于邏輯上的自洽,即同一條款下的五項要求竟不屬于同一審查標準,同時與該法第五條所規定的“合法性審查”相矛盾。
(二)以合法形式實現非法意圖
在案例二中,一審法院經審理查明后認為,黃石市公安局以刑事偵查為名,對與案件無關且明知是相對人的合法財產予以扣押,其行為違反我國刑事訴訟法。同時,湖北省黃石市公安局在扣押鋼材期間,向黃梅縣振華建材物資總公司施加壓力,并在其辦公地點主持振華建材物資總公司與并無經濟合同關系的浙江瑞安生產資料服務公司簽訂違背真實意愿的合同,強迫振華建材物資總公司用其合法財產償還他人所欠的債務。該行為明顯具有非法干預民事主體間經濟活動的意圖。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撤銷被告市公安局扣押原告振華公司鋼材的行為。最高人民法院維持原判。在案例三中,原審法院審查后認為平度市公安局扣押日照金融市場銀行承兌匯票解訖通知原件的行為是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而非刑事審查中的調取證據行為,平度市公安局以刑事偵查為名,扣押日照金融市場的合法財產,屬濫用職權,該種具體行政行為應當予以撤銷。最高人民法院維持該項判決。
案例二中,法院判定行政機關“濫用職權”的思路可以歸納為行政機關假借刑事偵查權,故意扣押黃梅振華公司合法財產,以刑事偵查權為由介入至民事主體之間的糾紛中。案例三中也是以同樣的刑事調查取證行為為名,實現自身之非法目的。兩個案件中行政機關均是以合法形式實現非法意圖,行政機關的主觀故意是法院審查的重點內容。
上述兩個案例中所體現法院論證邏輯與“主觀故意說”相似,該說認為濫用職權的審查標準必須是行政機關主觀上的故意[4] 。根據此種學說,法院在審查判斷行政機關是否濫用職權時不僅應了解立法精神,更應著重探究行政機關的主觀意圖,當行政機關存在主觀上故意實施違背立法目的的行政行為時便構成濫用職權。該說重視對行政機關主觀層面的考察,具有一定的進步性,但卻忽視了對行政機關主觀過失的定義,使得該理論存在邏輯漏洞,無法涵蓋完全。
如在案例九中,寧夏中衛市金利工程運輸有限公司虛報注冊公司資本,中衛市工商局對其作出 “責令改正,罰款 45 萬元”的 33 號行政處罰。在該處罰決定送達生效后,金利公司依照相關規定補齊了注冊資本并及時繳納了足額的罰款。但在中衛市工商局組織專人對此案進行重新審查后又作出 80號《關于撤銷衛工商處字(2009)第33號的決定》(以下簡稱80號決定),對金利公司加重處罰。
法院經審查后認為中衛市工商局于后來所作的 80 號決定未考慮 33 號決定的合法性及合理性,且并未考慮到金利公司已主動履行相關義務等事實,實屬反復無常,雖不屬于主觀故意,但確存在主觀上的過失。同時,其行為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屬于不利于相對人的改變,無助于法律的安定性以及行政管理秩序的穩定性,被訴行政行為構成權力濫用,存在明顯不當。依照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2、5目之規定,應予以撤銷。
(三)濫用行政裁量權
在案例五中,原告王麗萍駕駛3臺農用小拖拉機運送31頭生豬。行駛途中,被告河南省中牟縣交通局的工作人員以王麗萍的3臺拖拉機未交養路費為由,對車輛進行扣押。因天氣酷熱,王麗萍提出先行將生豬卸下車后再對車輛進行扣押,但被告的工作人員卻置之不理,強行摘下拖斗后駕車離去。這一行為致使拖斗內的生豬因自然擠壓和氣候炎熱中暑,共致死15頭。
中牟縣人民法院判決認為,“行政機關在自由裁量領域合理的使用裁量權也應當屬于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考察內容。”該案中,憑借一般人的生活經驗便應當知道在高溫的天氣狀況下,運輸途中的生豬不宜受到擠壓,更不宜在路上久留。然而,在原告已經提出請求的情況下,縣交通局工作人員不僅未對相對人的請求作出及時回應,甚至忽略該財產的安全,將兩輪拖斗卸下后就駕主車離去,給相對人造成了經濟損害。縣交通局工作人員在執行暫扣車輛決定時的此種行政行為,與合理、適當性的要求相悖,屬于濫用職權。
該案中,法院首先將暫扣之后進一步處理車輛的行為歸入行政機關的行政裁量①。其次將明顯違背常識即明顯不合理的使用裁量權認定為“濫用職權”。在說理中,法院首次提出只要行政機關在行使裁量權時存在主觀過錯,即明顯不合理行使裁量權便同樣可以構成濫用職權[5]55。明顯不合理在該案中具體指行政機關在扣押車輛的過程中不考慮財產安全以及相對人合理的請求,違背常識性因素,強行實施行政行為。
上述案例中所體現的法院論證邏輯與“濫用裁量權說”相似,此說也是目前學界的通說。這種說法認為濫用職權即濫用裁量權[6-10] 。是對行政機關權限范圍內裁量權行使的評價。此觀點在全國人大法工委編寫的著作中也得到支持,書中將行政權限范圍內的具體行政行為作為“濫用職權”的適用對象[11] 。不可否認濫用裁量權的觀點非常具有吸引力,但卻仍然存在一些理論爭議,從上文選取的最高院案例中便可窺知一二。
1.是否適用存疑。案例八中,法院認為行政復議機關未通知利害關系人作為第三人參加行政復議,在未聽取利害關系人陳述的情況下即做出對其不利的復議決定,違背程序正當原則,依法應予撤銷。法院判定濫用職權的思路為:正當程序與法定程序是一種并列關系,若法律未對相關程序作出規定,理論上便進入到行政裁量的范疇,因此該案中行政機關違背正當程序的行為構成濫用職權[12] 。
該案中法院通過對行政裁量權的審查判定了濫用職權,但此舉是否正確?在法律規范沒有明確規定行政機關未通知利害關系人作為第三人參加行政復議是否違法的情況下,法院能否直接以正當程序原則直接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①?如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該種行為是否真的屬于濫用職權?在“張成銀訴徐州市政府房屋登記案”中,針對與案例八相似的情況,法院卻判定屬于“嚴重違反行政程序”②。由此可以看出濫用職權在此種案件中的適用仍處于有待進一步論證的狀態。
2.適用數量不足。除上述情形外,在現實的判決書中,很少有法官直接通過行政裁量來對濫用職權進行直接論證,而是通過諸如比例原則來進行說理。比例原則主要包括適當性、必要性以及均衡性這三個次級原則。適當性原則主要從“行為目的” 來對行政行為進行規范,強調手段與目的的一致性;必要性原則主要從“法律后果”對其進行規范,強調行政主體在實施行政行為時,應當選擇對相對人權利影響最小的方式進行;均衡性原則主要從 “價值取向”上對其進行規范,強調方法與目的之間的權衡。相對于合法性原則,比例原則屬于合理性原則的范疇[13] 。其有助于司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裁量權進行審查。
在案例六中,原告鄭某所有的一間獨立產權房屋遭拆遷后,行政機關以產權調換的方式對其作出補償,但因調換補償的房屋為某片區A幢一層商場按比例享有的共有權,鄭某未與行政機關達成一致意見,故在行政裁決后不服提起訴訟。法院認為,莆田市建設局在以產權調換的方式作出拆遷裁決的時候,應盡可能不改變產權性質及占有方式,以保護被拆遷人的最大權益。但在該案中,在未能充分舉證說明沒有更好的調換方案情況下,被告莆田市建設局將被拆遷人的原專有所有權調換為沒有具體產權方位的財產共有份額,損害了被拆遷人的權益,內容明顯不當,應依照1989年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1、3、5目的規定,撤銷被告莆田市建設局作出的房屋拆遷糾紛裁決書并責令被告莆田市建設局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
該案中,法院認為裁量內容明顯不當是“濫用職權”,而不符合比例原則便是明顯的不合理。法院運用比例原則進行論證的具體思路如下:第一,論證案件中莆田市建設局的行政行為缺乏適當性,其僅注意到產權調換是為了實現拆遷安置的行政目的,卻忽略了拆遷過程中保障被拆遷人權益這一潛藏目的。第二,論證該行政行為欠缺必要性,莆田市建設局在拆遷過程中未能將相對人的損失保持在最小范圍內,將專有所有權的房屋調換為按份共有所有權的房屋,對相對人利益造成較大損害。
除上述案件之外,案例十與十一的法院也同樣是運用比例原則進行說理。在案例十中,最高院判定縣政府對城東公司的撤證決定屬濫用職權,理由為該公司持有的《國有土地使用證》雖未填寫土地用途,但并非城東公司的原因所致,且該種錯誤本可以補正方式解決,縣政府卻使用了“撤銷”這一對相對人權益損害更大的方式。這種行為明顯欠缺必要性,屬于濫用職權。在案例十一中,行政機關在行使行政裁量權時,應當盡可能選擇對相對人合法權益侵害最小的方式進行。本案中,晉源交警一大隊在認定涉案車輛涉嫌套牌但持續扣留卻主要證據不足時,晉源交警一大隊既不返還機動車,又不及時主動調查核實車輛相關來歷證明,也未及時要求相對人劉某提供相應擔保并解除扣留措施。在該車輛能夠返回維修站整改或返回原登記的車輛管理所,在相應部位重新打刻號碼并履行相應手續的情況下,并未選擇該種對相對人權益侵害較小的方式進行,而是反復要求劉某提供客觀上已無法提供的其他合法來歷證明。交警部門應為而不為,不應為而為的行為,致使車輛最終報廢,嚴重損害了相對人的權益,違背比例原則中的必要性,也完全背離了當初立法中要求打刻號碼制度的目的,濫用了法律法規賦予的職權[14] 。
至此,通過對最高院判例的整理分析,我們在了解最高院論證邏輯的同時完成了對現有三種學說的批判。回觀這些案例,發現最高院對“濫用職權”的裁判并沒有一個較為明晰統一的確定標準,但這并不意味著其全然無跡可尋。仔細思索,便可發現違背法律授權目的、以合法形式實現非法意圖以及濫用裁量權中的案例均包含司法機關對行政機關在實施行政行為時主觀目的的考察。前兩種具有非法意圖的自不必說,在第三種法院通過比例原則來對濫用職權進行論述時,比例原則中包含的首要原則便是適當性,即對行政機關主觀目的的考量。由此,筆者認為最高院在對“濫用職權”進行判定時,“主觀目的不正當”是其考察的核心。這種不正當涵蓋的范圍較廣,既包括違背立法精神(案例一、七)、立法原則(案例六、十、十一、十二① )等客觀目的的不正當,也包括違背相關常識性因素(案例五)、主觀目的(案例二、三、九)的不正當。
在得到上述論點之后,不難發現在整理完成的十二個案例中,除了上文已經解釋過的案例八,仍舊剩余一個案件,即案例四。
在案例四中,靖遠縣服裝刺繡廠破產后,原告路世偉以36萬元的價格買下該廠,并同時購買了西街廠區的財產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此事經清算小組請示被告甘肅省靖遠縣人民政府,被告也曾以靖政發(1997)134 號文件批復同意。但是,當原告付清款項,辦好手續準備開張營業時,被告要求原告退回西街廠區。遭拒后,被告則下發新的(1999) 172號文文件,撤銷當初批準同意的文件,收回了原告的國有土地使用權。
甘肅省高院審查后認為:依據最高院《關于審理企業破產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的相關規定,清算組關于破產財產處理的方案經人民法院裁定予以認可后,便可立即執行,無須向行政機關請示。人民法院依職權組建的清算小組是有權負責集體企業破產財產的保管、清理、估價、處理和分配工作的主體,縣政府無權進行干預。但在該案中,縣政府接到清算組的違法請示之后,并未以不屬于自身職權范圍為由拒絕受理,而是通過下發文件對此事批復同意,其行為超越了職權。同時,縣政府在批復同意的文件存在違法事實認定不清的情況下,又以錯誤的理由再次下發新的(1999)172號決定撤銷了自己之前作出的134號批復。該案中,縣政府以于法無據的行為為他人設定新的權利義務,妨礙了他人的合法權益。這些具體行政行為不僅超越職權,更屬于濫用職權。
在該案中,法院將“濫用職權”的判斷標準置于行政機關行使職權時有無法律依據,若行政機關缺乏法律依據而去為他人設定新的權利義務,妨礙他人合法權益的,屬于濫用職權。這種判斷標準在未確認行政機關是否存在不正當目的的情況下,法院便以“無職權”為由,判定構成濫用職權。這一情況顯然與上述“主觀目的不正當”的說理邏輯不同,但僅此一例許是最高院為了個案的解決而做出的判斷說理,尚不能動搖本文中由更多案例總結提煉出的“主觀目的不正當”這一觀點。
二、全國高級人民法院的適用情況
介紹完最高人民法院的經典案例,我們對其審判濫用職權的標準有了較為清晰的了解,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判決中形成的這些觀點是否為下級法院所接受適用,可以真實有效的成為下級法院判決時參考適用的標準?帶著這個疑問,筆者將進一步探究最高院確立的“濫用職權”標準在各高級人民法院的適用情況②。通過在北大法寶上以“本院認為”“濫用職權”為關鍵詞,搜索高級人民法院的行政判決書,共得到251份結果。去除其中僅在當事人訴訟請求、行政機關答辯中提到的,列舉相關法條時涉及到的以及未進行實質性說理的案件,僅剩下為數不多的17個案例。
(一)遵循適用“主觀目的不正當”標準的情況
在這 17 個案件中,有 11 個案件法院是明確以目的具有不正當性作出的濫用職權判決。其中,在 “余艷軍與武漢市蔡甸區城市管理執法局”一案中①,法院雖然未采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但在分析時卻提到“有濫用職權的嚴重主觀過錯”,反向證明了判定濫用職權所需的主觀目的不正當要素。
(二)回避說理的情況
在高院的判決文書中,除了參照適用最高院所確立的精神原則,也存在部分案件轉移爭議焦點、回避說理的情形。
在平樂縣青龍鄉豆地村民委員會新民村村民小組等行政裁決二審行政判決書中②,雖然法院將案件爭議的焦點認定為考察被上訴人平樂縣人民政府、桂林市人民政府是否存在違反程序、超越或濫用職權行為。但在具體分析時卻僅對程序是否違法、適用法律法規是否正確進行了論證,回避了對濫用職權所需要進行的相關說理。
在寧夏平羅縣會元錳鋼廠與縣政府土地行政裁決糾紛上訴案中③。法院雖認定被上訴人平羅縣人民政府作出的處理決定在未撤銷平政發(2003) 131號文件的情況下將已經注銷的國有土地使用證再次注銷,是濫用職權、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但并未進行相關實質性的闡釋。
除此之外,曾慶華等訴漢壽縣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處理案以及白銀市公安局與朱偉、白銀市人民政府行政處罰及復議案件中也存在上述模糊甚至未曾說理的情況④。這種情況的出現說明了高級人民法院對“濫用職權”標準的猶疑態度。
(三)對“濫用職權”標準做出限制的情況
在之前的案件中,大家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尋找行政機關不正當目的的存在與否,卻忽視了“不正當”程度的要求。下面介紹的這兩個案件便從另一個角度提醒我們“濫用職權”并非沒有門檻,即便是行政機關主觀目的不正當導致的結果也必須達到一定的程度,具體應結合對相對人權益侵害的程度來進行綜合判定。
在杭州市江干區人民政府與徐永興房屋行政確認糾紛上訴案中⑤。法院認為原審判決僅以上訴人實際確認的建筑占地面積比杭州市規定的占地面積上限少 0.5 平方米,即認定被訴行政確認行為屬濫用職權,系適用法律不當。在衛某某與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政府信息公開糾紛案中⑥,法院認為行政機關雖超過法定30個工作日寄送答復書,但其作出答復時亦在延長期限內,故行政機關超期“告知”和“答復”的不當尚未達到濫用職權的程度。
三、濫用職權裁判標準適用現狀反思
通過上文對高級人民法院有關“濫用職權”案件的整理分析,發現最高院所確立的“主觀目的不正當”標準確實于高院中得到了適用,但并不徹底。在下級法院中仍存在對這一標準模糊其詞、該用不用的情況,這表明法院對“濫用職權”仍持有一種謹慎的態度。
下面我們將進一步追問,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是什么?結合現有學者的討論,筆者認為:首先,相較于客觀標準,行政機關的主觀目的確實不易考察。很多時候需要依靠法官自身的經驗知識來進行判斷,這便容易導致各地標準不一。其次,“濫用職權”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加上多元的學說紛爭使得統一標準更加困難。
行政法上的“濫用職權”與日常意義及其他實體法中所指的含義有混淆的可能,阻礙其在行政法中的適用。“濫用”一詞高頻次出現在日常用語中,多指“過度或者胡亂地使用”;《刑法》第397條也規定了“濫用職權罪”,根據張明楷教授的總結,該罪主要包括“超越職權、玩弄職權、任意放棄職責以及以權謀私這四種情形。”多種場合的使用,導致該詞語義相對于行政法中使用的領域有所擴大[6]9 。《行政訴訟法》中缺乏對“濫用職權”認定標準的進一步界定,行政法學界中關于“濫用職權”的內涵與外延并未形成一種較為統一的觀點。上文提到的便有“濫用裁量權說”“違反授權目的說”以及“主觀故意說” 等學術觀點。立法的模糊以及學說的多元導致了法官在判斷使用這一標準時容易將其與“主要證據不足、適用法律法規錯誤、超越職權、違反法定程序”,以及2014年修法前的“顯失公正”與修法后的 “明顯不當”等情形交叉混淆,甚至有意遁入其他更為客觀的判定標準,具體如下。
(一)并用情形
根據上述對最高院12個案例的分析,只有六個案例是僅依靠“濫用職權”做出的判決,剩余的一半案例均是與其他標準一起進行適用從而作出撤銷判決。具體來說,案例一中適用法律、法規錯誤,超越職權與濫用職權并用;案例四中超越職權與濫用職權并用;案例六中主要證據不足,違反法定程序與濫用職權并用;案例七與案例八中違反法定程序與濫用職權并用;案例九中適用法律、法規錯誤與濫用職權并用。有學者認為此種情況是各種標準相互間交叉、混亂適用的表現,根源于其在邏輯上并未遵循統一劃分的標準,是濫用職權被濫用的體現[10]99。筆者在一定程度上認同這種觀點,也正因如此,進一步厘清界定“濫用職權”的審判標準具有重要意義。(二)該
(二)該用不用情形
除了上述并用的情形外,實踐中還可能出現應當適用“濫用職權”而不適用的情形。在《行政訴訟法》修改前,最為常見的便是遁入“顯失公正”的裁判標準。背后原因多是相比于濫用職權所具有的對行政機關主觀意圖的評判色彩,顯失公正這一標準更為客觀,同時也更容易為行政機關所接受。
哈爾濱市規劃局訴匯豐實業發展有限公司行政處罰糾紛案便是典型案例①。該案中,匯豐實業發展公司在市中央大街建成將近萬平的多層商品房,但并未全部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由此,規劃局以其建設行為破壞中央大街景觀,違反《城市規劃法》《黑龍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辦法》為由,做出了罰款、拆除的決定,但被處罰人認為該處罰決定存在明顯的濫用職權和顯失公正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被上訴人匯豐公司在未全部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的情況下即在哈爾濱市中央大街建成商服用房,違反了法律法規相關規定,應予處罰,但規劃局所作的處罰決定應針對影響的程度。行政機關責令匯豐公司采取改正措施時,在保證管理目標實現的情況下也應兼顧相對人的權益。而本案中,上訴人所作的處罰決定要求拆除的面積明顯大于遮擋的面積。原審中判定該處罰決定顯失公正是正確的。
該案中,被處罰人提出規劃局的行政處罰存在濫用職權與顯失公正的問題,法官在判決說理中顯然意識到了本案屬于行政機關濫用裁量權的情形,但其在最后的判決中卻并未提到“濫用職權”,而是依靠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四)項以及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的規定,維持原判。這種回避適用濫用職權標準,傾向于適用顯失公正的情況在實踐中并不少見,《人民法院案例選》中刊載的“郭佳訴洛陽市公安局西工分局治安管理處罰案”也屬于其中一例②。
在《行政訴訟法》修改之后,原先第五十四條中的“顯失公正”款項沒有了,增加了“明顯不當”作為法院撤銷行政機關行政行為的依據。修改后的濫用職權與明顯不當二者的適用范圍雖均是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領域,但卻有各自獨立相區別的適用條件。學理上講,濫用裁量權不僅包括客觀上的濫用,也包括主觀上的濫用。明顯不當針對客觀上的濫用裁量權,濫用職權針對主觀上的濫用裁量權,二者各司其職,分工明確。
(三)擴大適用情形
與該用不用相反的一種情況是濫用職權標準的擴大適用。即在實踐中,法官用濫用職權一詞寬泛的代指行政機關的多種違法行為。可以說,此種意義上的濫用職權與“違法”同義。
在“薛誼花訴青銅峽市城鄉建設局行政賠償案”中③,被告青銅峽市城建局的工作人員到薛誼花經營的毛衣編織店收取 10 月至 12 月的衛生費,在薛誼花拒絕繳納12月份的衛生費后,雙方發生爭議沖突。執法人員不僅扣押了店中的電熨斗,還對薛誼花進行毆打致其受傷。銀南中院經審理后認為建設局的工作人員提前預收城市衛生費、強行扣押公民私有財產并且毆打他人致傷的行為屬于濫用職權。在該案中我們可以看到,法官以“濫用職權” 這一標準囊括了行政機關的各種違法行為,擴大了學理中濫用職權的范圍,將其做了泛化的理解。
除此之外,在“秦然等訴薄壁鎮政府行政賠償案”中④,村、鎮主要干部以被告薄壁鎮人民政府的名義對原告秦然的機動三輪車征收車船費。在原告秦然以其車屬于其胞弟秦小東所有為由拒絕繳納后,強行對該車輛進行扣押。即便在事后原告等人出具了完整的車船稅繳納證明材料,被告仍然拒絕歸還車輛。輝縣市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的扣押行為在原告已提交完整的車船稅繳納材料后明顯屬于缺乏事實依據的違法行為。通過對案情的簡單介紹,我們發現此案中并未涉及到行政機關的裁量領域,但該案中最后法官卻援引了“濫用職權”這一標準來判決撤銷行政行為。由此可見,法官在該案中將“濫用職權”寬泛地理解成為違法,又進一步將被告缺乏事實依據的具體行政行為帶入,從而判定應予以撤銷。
四、濫用職權裁判標準的完善建議
至此,我們依據最高院的12個裁判案例,得出濫用職權判定中“主觀目的不正當”這一標準。緊接著結合高院的實踐判決,發覺下級法院適用過程中的謹慎態度,之后在對這一現狀進行探究時發現真實審判過程中出現的并用、該用不用以及擴大適用的問題。結合這些在實證研究中發現的問題,為真正廓清濫用職權的行政法學概念,明確區分其與撤銷判決中剩余標準的界限,進一步統一司法裁判立場,提出如下建議。
(一)鼓勵“法律原則審查技術”的適用
通過法院在判決說理中模糊其詞、并用、該用不用的情況,可以看出實踐中多數法官在判決說理時縮手縮腳,盡量避開對濫用職權的判定。這種適用困境的出現某種程度上與法院過分追從法律規則的審查技術有關。法律規則的審查技術注重法律的權威,習慣將裁量問題轉化為法律或者事實問題后再做判斷,以追求司法審查的明確性。然而面對“濫用職權”這一模糊的名詞概念,這一技術的適用在現實面前難免顯得捉襟見肘。由此,應當鼓勵法律原則審查技術的適用[5]63。法律原則審查技術以法律原則為說理的載體,促使法官在判案說理時關注對不同理由、利益間的衡量。
由上文可知,對“濫用職權”的判斷需考察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行為時的主觀目的,除了明顯的非法目的外,很多主觀意圖潛藏在行政機關進行自由裁量的領域內(如最高院的案例五)。雖然在立法沒有明確規定的領域,行政機關享有行政裁量權,但行政機關的此種權力無疑存在濫用的可能,需要司法對其予以審查限制。針對這一領域的審查,法律規則幾乎無所助益,更多的是依賴于法律原則對雙方利益進行衡量之后再進行判定。然此種司法審查受限于法官自身法學素養以及相關規則的束縛,導致許多法官不敢大放拳腳,因此應當在政策上多多鼓勵“法律原則審查技術”的適用,為實踐中的應用打一針強心劑。
(二)指導案例規范化
在鼓勵法官大膽審查行政機關主觀目的時也應當注意到審判實踐中擴大適用的情形。為了防止司法機關對行政行為的審查閘門大開,需注意進行自我規制,最高院的指導案例便是十分有效的規制方式。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最高院的公報、指導案例對下級法院有著重要的影響,發布的案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官方意見。通過規范化的指導案例,為司法機關審查行政機關主觀目的不正當提供一個較為明確的范圍,以防司法恣意,忽視考察行政機關主觀目的不正當的程度,矯正過度。但現今并未出現系統化、規范化的指導審查意見。因此,統一行政訴訟中“濫用職權”的裁判標準仍在路上,需要學術界與實務界的持續共同努力。
綜上所述,濫用職權是行政法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因立法的模糊、學說的多元以及本身語義上的不明晰導致實踐中界定濫用職權審判標準的困難。本文依靠實證方法,通過搜集、整理、分析最高院、高院的真實審判案例提出一些拙見,不敢奢望重新建構行政訴訟中濫用職權的裁判標準,但求為其標準的進一步明晰規范略盡綿薄之力。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