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鄉村人居環境是農戶日常生產生活據以展開的設施及條件,基于主客觀比較視角的鄉村人居環境適配性評價是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統籌推進鄉村振興的客觀要求。論文立足江漢平原公安縣鄉村抽樣調查和訪談數據,以鄉村生活空間可及性解析環境供給水平,以居民生活條件滿意度解譯農戶需求意愿,以鄉村人居環境適配性解構供需差異,據此提出鄉村人居環境優化方向及路徑。結果顯示:2017年案例區鄉村生活空間可及性聚集分布最大值為44.75%,隸屬“中類”,以就業空間與休閑空間可及性最為薄弱;鄉村居民生活條件滿意度聚集分布最大值為0.467,隸屬“中類”,其中農村自然環境與經濟運行環境的滿意度評價最低。主觀需求與客觀供給適配性在縣域尺度和農戶個體尺度均呈“中—中”類型適配模式,但在不同尺度的不同維度表現出差異性。研究結果可為案例地區及相似地域鄉村人居環境建設與鄉村振興提供科學依據。
關 鍵 詞:鄉村人居環境;滿意度;可及性;適配性;江漢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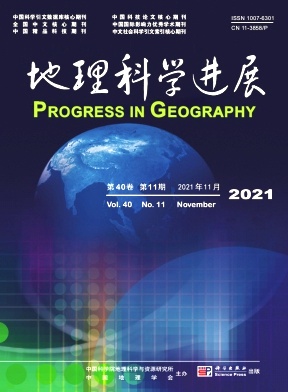
顏梅艷; 余斌; 郭新偉; 卓蓉蓉, 地理科學進展 發表時間:2021-11-28
鄉村人居環境是鄉村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物質和非物質條件的有機結合[1-2]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先后實施“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鄉村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鄉村居民日常生活條件顯著改善;另一方面,中國鄉村地域遼闊,發展條件千差萬別,鄉村人居環境建設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等問題[3-4] 。鄉村人居環境建設的本質是鄉村環境供給條件與居民生活需求意愿狀態的匹配[5-6] ,以滿足鄉村居民需求意愿為主旨、科學審視鄉村人居環境建設適配性,對精準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升鄉村建設成效和推動鄉村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伴隨著人類社會發展觀的進步,鄉村人居環境持續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國際上,因逆城市化與鄉村移居現象的出現,鄉村人居環境已從鄉村聚落發展的附屬研究對象轉變為獨立研究主體[7-8] ;由于發展階段的差異,當前國際學術研究側重關注城市遷居群體的鄉村人居環境效應[9-10] 和鄉村弱勢群體的人居環境狀況[11-12] 等。國內鄉村人居環境研究總體起步較晚,在經歷理論探索[13-14] 和綜合研究[15-16] 之后,鄉村發展的人居環境效應頗受關注,相關研究可大致歸為2個方面:① 基于環境供給的鄉村人居環境評價。如唐寧等[17] 基于統計年鑒數據構建指標體系,對重慶市鄉村人居環境質量進行綜合評判;朱彬等[18] 基于農業普查數據構建測評體系,對江蘇省人居環境質量進行綜合評述;王成等[19] 利用面板數據構建評價體系和測度模型,對鄉村人居環境可持續力進行時空演化分析等。 ② 基于主體需求的鄉村人居環境評價。如李伯華等[5] 以石首市久合垸鄉為例對鄉村人居環境的居民滿意度評價,提出應基于居民意愿與感知確定優化方向;苗紅萍等[20] 對新疆6個案例村進行調研和分析,依托人居環境滿意度低的核心問題提出優化建議;常烴等[21] 結合天津市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滿意度及支付意愿實際,探索影響因素等。前者科學揭示了不同鄉村地區關于人居環境供給的客觀狀況,后者反映了不同鄉村群體關于人居環境需求的主觀意愿,二者均能夠從不同側面為鄉村振興及其人居環境優化提供有益信息,并為鄉村人居環境的理論建設貢獻了有效智慧。盡管鄉村人居環境建設研究內容不斷豐富,已有豐碩理論與實踐成果對中國鄉村人居環境建設與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大多僅從客觀供給或主觀需求單一視角探究,缺少基于人居環境建設客觀供給水平與居民主觀需求意愿的共同關注;主客觀比較可提供單一視角不能反饋的鄉村人居環境建設超前、滯后亦或理想的供給狀態等信息,其研究成果可直接為鄉村人居環境建設提供科學指導。
鄉村人居環境建設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和長期任務,以滿足鄉村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為導向,精準識別鄉村人居環境適配性對平衡鄉村振興戰略方向、優化鄉村人居環境建設路徑具有獨特意義。據此,本文基于江漢平原公安縣實地調研數據,以鄉村生活空間可及性解析環境供給水平,以居民生活條件滿意度解譯農戶需求意愿,以鄉村人居環境適配性解構供需差異,并據此提出鄉村人居環境優化路徑,旨在為鄉村人居環境理論研究和實踐發展提供啟示。
1 方法與數據
1.1 研究思路與方法
以鄉村生活空間可及性解析環境供給水平。鄉村生活空間是鄉村居住空間、就業空間、消費空間和休閑空間迭置而成的空間聚合體[22] ;另一方面,居住、就業、消費和休閑等農戶生活空間行為又是鄉村人居環境建設供給的內生變量[23] 。借鑒公共服務研究領域的可及性概念(也有學者譯為可獲得性) [24-26] ,定義鄉村生活空間可及性為鄉村居民對鄉村居住、就業、消費和休閑等空間的實際利用狀況,以此映射鄉村人居環境建設有效供給水平。鄉村生活空間可及性是刻畫鄉村人居環境狀況的重要視角。借鑒相關研究成果[23-24,27] ,構建鄉村生活空間可及性測度指標體系(表1),以熵值法進行因子賦權、通過加權求和測算結果,并以自然斷點法將農戶生活空間可及性測算結果分為高、中、低 3 個等級,再用最大隸屬度原則對案例區所屬等級進行評定。鄉村生活空間可及性等級與鄉村人居環境供給水平呈正向關聯。
以居民生活條件滿意度解譯主體需求意愿。居民生活條件是鄉村自然生態環境、地域空間環境和人文社會環境交織而成的有機統一體[23,28] 。這里的主體需求意愿則是指鄉村居民對鄉村生活環境改善(鄉村人居環境建設)的期望程度。明顯改善居民生活條件既是鄉村人居環境建設的重要任務,又是鄉村居民對美好生活條件的期望需求[29-30] 。鄉村居民的需求意愿越能得到滿足,對生活條件建設的滿意度也越高[31] 。定義居民生活條件滿意度為鄉村居民對鄉村自然生態基礎、物質設施條件及人文社會環境的主觀期望與感知評價,以此呈現鄉村居民對鄉村人居環境的真實需求意愿,居民生活條件滿意度是描述鄉村人居環境狀況的又一重要視角。借鑒相關研究成果[5,32-33] ,本文構建居民生活條件滿意度評價指標體系,進行李克特量表打分,以熵值法進行因子賦權并測算個體居民生活條件滿意度值、以模糊綜合評價法測算案例區滿意度綜合值;為精準識別農戶對環境供給資源的需求意愿,將居民生活條件滿意度值以[0, 3)、[3, 4)、[4, 5]區間進行低、中、高3個等級分類,再依最大隸屬度原則對案例區所屬等級進行評定。具體指標體系及相關因子權重見表2。居民生活條件滿意度水平與鄉村農戶需求意愿呈負向關聯。
以鄉村人居環境建設適配性解構供需差異。鄉村生活空間可及性與居民生活條件滿意度分別從不同視角解析鄉村人居環境建設狀況,二者具有內在關聯。事實上,鄉村生活空間可及性蘊含鄉村居民生活條件和生活意愿等豐富信息,從而與居民生活條件滿意度形成對應,具體至指標層則有:居住空間可及性是鄉村聚落地理區位、經濟收入和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滿意度等作用下的結果,就業空間可及性實則是地方就業供給、就業環境保障、經濟收入管束和交通可達性預期等作用下的結果,消費空間可及性實乃經濟收入、物價水平約束及商業設施布局與服務能力提供、交通出行意愿等多因素綜合作用下的結果,休閑空間可及性則是社會文化環境發展、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拘束和休閑意志等作用下的結果,而衛生環境、自然環境及生態環境則是鄉村生活空間可及性的重要環境基底,從而實現鄉村生活空間可及性與居民生活條件的內在關聯。在很大程度上,鄉村居民生活空間可及性與居民生活條件滿意度的匹配狀況能夠揭示鄉村客觀環境條件與鄉村主體需求意愿的供需差異。據此,定義鄉村人居環境建設適配性為鄉村生活空間可及性與居民生活條件滿意度的匹配狀況與適宜程度。根據前述分級結果和最大隸屬度原則,鄉村人居環境建設適配性存在適配與失配2種模式、共計9種類型(圖 1、圖 2),不同的類型意味著不同的供需差異狀態,并具有明確的優化路徑與政策涵義。其中,“高—高”類型處于供需均衡理想狀態,人居環境建設應以維護該狀態為主;“中—中”“低—低” “低—中”和“中—低”類型處于供需均不佳狀態,人居環境建設需同時提升并兼顧供給與需求發展狀態;“低—高”“中—高”類型處于供給超前狀態,人居環境建設在維持現有供給水平的基礎上,還應基于農戶“低”“中”生活滿意度評價及時調整有效供給方向;“高—低”“高—中”類型處于供給滯后狀態,人居環境建設應加大客觀維度的有效供給。
1.2 研究區域及數據
公安縣地處江漢平原西南部,長江中游區段 (圖 3),全縣土地面積 2258 km2 ,2017 年常住人口 86.28萬人,其中鄉村人口42.97萬人、占比49.80%;同期地區生產總值248.91億元,第一產業生產總值 63.20億元(按當年價),占比25.39%。快速城鎮化對鄉村地域沖擊加劇,作為國家級農產品主產區的江漢平原典型縣域,公安縣農戶生活空間和人居環境也已呈現新的發展態勢。按“供給水平—需求意愿 —供需差異”邏輯脈絡,能夠精準定位鄉村人居環境建設的供需狀態并為該類區域鄉村振興與可持續發展提供有益信息。
研究數據為 2017 年 9 月對公安縣農戶的調研所得。在評估公安縣鄉鎮綜合發展水平梯度差異的基礎上,采用半結構訪談、分層抽樣和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法,選取公安縣5個鄉鎮50個鄉村作為抽樣點(圖3)。調研共發放862份問卷,回收與本文相關有效問卷809份,有效率93.85%。調研以問卷訪談的方式進行,訪談對象為能代表家庭決策和管理的常住戶戶主。從樣本農戶的屬性來看,公安縣農戶主呈男性偏多、年齡偏大、文化程度較低的特征,家庭屬性呈規模適中、勞動力較充足、務農為主、收入偏低的特征(表3)。運用SPSS 23.0軟件對生活條件滿意度量表問卷數據進行信度檢驗,得到 Cronbach's Alpha 系數為 0.846,大于 0.8,即問卷數據具有較高一致性,屬于高信度。
2 公安縣鄉村人居環境建設適配性分析
2.1 公安縣鄉村生活空間可及性分析
根據研究思路與方法可得表 4。就目標層而言,公安縣農戶生活空間可及性均值為 28.48,“中類”聚集傾向明顯(44.75%),“低類”次之(39.06%), “高類”較分散(16.19%)。支持層而言,不同生活空間子維度的可及性分布有差異,其中,消費空間可及性均值(92.78)最大,且傾向“中類”(44%)聚集;就業空間可及性均值(7.54)最低,且“低類”(68.48%)聚集顯著;居住與休閑空間可及性均值居中,但聚集傾向均隸屬“低類”。說明,近年來公安縣注重鄉村發展,整體鄉村生活環境供給尚好,但居住、就業與休閑空間可及性是公安縣供給較為薄弱環節,消費空間可及性也有提升空間,為公安縣鄉村人居環境建設優化提供供給方的重要信息。
2.2 公安縣鄉村居民生活條件滿意度分析
由模糊綜合評價法可得公安縣鄉村居民生活條件評價體系的目標層、支持層和分類層滿意度值、模糊聚集分布狀態及隸屬度等級(表5)。其一,從目標層來看,公安縣鄉村居民生活條件滿意度綜合值為3.511,模糊聚集分布最大值(0.467)隸屬“中類”,表明公安縣鄉村人居環境建設有成效,農戶需求意愿能夠得到較一般的滿足。其二,從支持層來看,物質設施條件滿意度最高(3.856),模糊聚集分布最大值(0.587)隸屬“中類”;自然生態基礎滿意度最低(3.360),與社會人文環境的模糊聚集分布最大值均隸屬“低類”,是鄉村人居環境建設中有待提升的2類支持層維度。其三,從分類層來看,社會保障環境滿意度最高(4.038),模糊聚集分布最大值 (0.618)卻隸屬“中類”;村落衛生環境、農業生態環境、個體居住條件、公共服務條件、基礎設施條件、文化發展環境等 6 個維度的滿意度值均低于 4,模糊聚集分布最大值均隸屬“中類”;經濟運行環境滿意度(2.998)最低,且與農村自然環境的模糊聚集分布最大值都隸屬“低類”。由此可見,農村自然環境、經濟運行環境將是未來公安縣鄉村人居環境建設供給中的重點關注領域,為公安縣鄉村人居環境建設優化提供需求方的重要信息。
2.3 公安縣鄉村人居環境適配性分析
2.3.1 鄉村人居環境適配模式
其一,從縣域尺度分析。按最大隸屬度原則,公安縣整體人居環境主觀滿意度呈“中類”聚集分布,生活空間可及性也顯“中類”聚集分布,縣域尺度適配結果為“中—中”類型的適配模式,說明公安縣整體人居環境供給水平與需求意愿大致均衡。但居住、就業、消費和休閑等4個維度適配結果卻有所差異,除消費空間可及性供給為“中—中”類型外,其余均為“中—低”類型。表明公安縣在落實 “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實踐中成效初顯,農戶生活條件主觀需求意愿能夠得到較好滿足,但就業、休閑與居住等維度的客觀供給相對于需求意愿有一定的滯后性。其二,從農戶尺度來看。將809戶農戶人居環境主觀滿意度和生活空間可及性進行適配。就模式而言(圖4),農戶滿意度與生活空間可及性失配模式(57.48%)聚集傾向明顯,且以滿意度等級高于生活空間可及性等級為主(38.44% ),而適配模式 (42.52%)相對分散;農戶主觀滿意度與居住、就業、消費和休閑等4個維度可及性的適配結果也顯示出主觀高于客觀的失配模式特征,說明農戶尺度上,公安縣鄉村人居環境供需差異明顯,且以滿意度評價高于客觀供給為特征。就類型而言(表6),農戶滿意度與生活空間供給適配結果以“中—中”類型占據優勢(35.11%),與居住、消費維度供給適配結果也呈“中—中”類型聚集,分別為29.17%、32.14%,而與就業、休閑維度供給適配則顯“中—低”類型聚集,分別為 50.56%、38.94%,“高—高”類型均不明顯。因此,農戶就業、休閑維度的供給滯后于農戶主觀滿意度評價的程度較大,鄉村環境整體供給、居住和消費維度供給滯后于農戶主觀滿意度評價的程度稍小。
2.3.2 鄉村人居環境供需適配機制
鄉村人居環境建設適配性是鄉村客觀供給條件與農戶人居環境主觀需求意愿相互作用下的結果,但二者在不同尺度與不同維度對適配模式的影響方式和影響強度都有所差異。
(1) 關聯需求意愿“中類”聚集的直接因素。整體而言,公安縣農戶滿意度綜合值為 3.511,隸屬 “中類”,農戶需求意愿得到滿足程度還未達到“高類”聚集狀態;具體而言,社會保障環境維度滿意度最高,但也僅為 4.038,農戶在經濟運行環境、村落衛生環境、農業生態環境、農村自然環境等4個分類層滿意度均低于整體滿意度綜合值,且對應的指標層中河湖污染處理(62.8%)、就業環境條件(66.4%)、經濟收入水平(70.3%)、消費物價水平(75.6%)的“低類”聚集顯著,是農戶對鄉村人居環境建設中需求意愿較高的4個方面。
(2) 識別供給水平“中類”聚集的關鍵因素。公安縣人居環境供給水平主要受制于就業空間和休閑空間的低可及性,其“低類”占比分別為68.48%和 50.80%。于就業空間可及性而言,公安縣農戶就業類型中純農戶、兼業戶及非農戶分別占 56.37%、 33.99%及9.64%,純農就業特征明晰,80.8%的常住農戶就業區位在村域范圍內,家庭收入在4萬元及以下的農戶占59.09%,導致農戶就業可及性“低類” 匯集。于休閑空間可及性而言,以電視和聊天為首要休閑方式的農戶分別占51.7%、26.9%,82%以上的常住農戶休閑在村域范圍,促成農戶休閑可及性 “低類”聚集。
(3) 各因素作用下的鄉村人居環境適配機制。其一,農戶需求意愿的適配機制。在落實鄉村振興戰略及《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等政策中,公安縣穩步推進農業農村的投資力度,通過鋪設通村道路、建設鄉鎮綜合文化站、設立村級文體活動中心、改善醫療衛生條件,鄉村基礎設施得到極大完善,相應地,農戶在交通設施、社會文化、居住條件、公共服務等領域給予較高的評價;與此同時,伴隨工業化、市場化、信息化的快速推進,農戶對生活品質、社會經濟等的認知水平和自身能力與日俱進,對自然生態、衛生環境、就業環境、收入水平及經濟發展等多方面提出更高需要,故縣域尺度的農戶需求意愿適配結果集聚于“中”類。其二,農村環境供給的適配機制。公安縣社會經濟不斷發展,農戶居住、就業、消費、休閑模式已有一定的變遷[34] ,整體生活空間可及性適配結果中均顯“中” 類。然而,與傳統農區的功能定位、低中端的產業結構相對應,公安縣非農就業供給不足,常住農戶多以純農就業為主,收入水平低,就業不充分、層次有待提高;現有休閑資源布局與享有門檻直接限制著農戶對休閑資源的利用率,致使農戶休閑仍以傳統模式為主,農戶休閑供給水平明顯偏低,因此,農戶個體尺度的適配結果中,就業與休閑維度的供給水平呈“低類”聚集。以旱廁為主的內置廁所、以磚混結構為主的老舊房屋等因素仍舊牽制著居住維度的供給水平,最終,縣域尺度適配結果的居住、就業及休閑維度呈“低類”聚集。綜上,在農戶需求意愿機制與農村環境供給機制共同作用下,主客觀適配性評價結果在不同尺度雖均為“中—中”類型適配,但在不同維度的適配結果卻有差異。
3 公安縣鄉村人居環境優化路徑
整體而言,公安縣鄉村人居環境在縣域尺度與個體尺度均未實現“高—高”理想適配類型,尚需整體提升;具體而言,客觀供給以就業和休閑維度滯后性較明顯,主觀需求以農村自然環境和經濟運行環境較顯著,形成整體提升和重點突破的雙層優化路徑。
其一,整體提升策略指引公安縣鄉村人居環境向“高—高”理想狀態發展。一方面,公安縣應繼續加大對農戶居住條件、就業機制、消費與休閑模式等的政策指導及資源投入,延展農戶生活空間可及性,促進良好人居環境秩序形成;另一方面,基于農戶知識素養與日俱增、美好生活需求意愿日益凸顯的背景,立足農戶對鄉村人居環境建設需求實際公安縣應因地制宜地提供有效供給,滿足農戶美好鄉村人居環境需求意愿。
其二,重點突破措施明確公安縣鄉村人居環境建設短板與供給方向。客觀供給方面,基于鄉村勞動力外輸主流背景,公安縣在新時代鄉村經濟動能轉換之際,適時培育新型特色產業,注重培育本土創業創新人才[35] ,提升本土內生非農就業能力,為農戶提供充分而優質的就業機會,提高經濟收入;基于農戶以傳統休閑模式為主的實際,公安縣應注重提供農戶可享有的休閑資源、降低農戶享受休閑資源門檻、提高農戶利用休閑資源便利度,促進鄉村休閑模式升級。主觀需求方面,結合農戶對自然生態基礎評價較低的實際,公安縣應抓好鄉村人居環境整治關鍵節點,以政府為主導,配置治污設施設備,尋求適合的污染防治模式,加強鄉村生態宜居建設;基于農戶對經濟運行環境評價較低的實際,公安縣應以工業反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及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等為契機,強化農戶主體地位認知,鼓勵農戶利用國家支農惠農政策,參與到農產品主產區的產品特色化、品牌化、市場化實踐中,形成國家與政府扶持、農戶積極參與、農民受益明顯的良性經濟運行環境。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1) 公安縣鄉村環境客觀供給水平呈“中類”聚集。案例研究表明:公安縣農戶生活空間可及性 “中類”特征明顯,占 44.75%,生活空間 4 個維度聚集分布有所區別,其中消費空間可及性聚集于“中類”,而居住、就業和休閑空間可及性均聚集于“低類”。農戶的生活空間資源利用區位范圍以“村域為主、鎮域為輔”。
(2) 公安縣農戶主觀需求意愿顯“中類”聚集。案例研究表明:公安縣農戶生活條件滿意度“中類” 地位凸顯(0.467),意味著農戶對其鄉村人居環境建設成效較為肯定。與此同時,農戶對鄉村人居環境建設的需求意愿得到滿足程度尚未達“高類”聚集,在農村自然環境、經濟運行環境維度的滿意度評價最低。
(3) 公安縣鄉村人居環境主客觀適配性存在尺度差異。案例研究表明:在縣域尺度和農戶個體尺度均顯“中—中”適配狀態。居住、就業、消費和休閑等4個維度適配結果在不同層次有所不同,縣域整體尺度,除消費空間可及性為“中—中”類型外,其余均為“中—低”類型;農戶個體尺度,居住與消費顯 “中—中”類型,就業與休閑則為“中—低”類型。
4.2 討論
(1) 鄉村人居環境主客觀適配性研究能夠為鄉村振興提供精準信息。基于鄉村發展已取得歷史性成就的時代背景,以鄉村生活空間可及性、居民生活條件滿意度分別解譯鄉村環境供給水平、居民生活需求意愿,以鄉村人居環境建設適配性解構供需差異;依照“供給水平—需求意愿—供需差異”的邏輯主線,提出人居環境供給與需求的2種適配模式和9種適配類型結果,利用熵值法、模糊綜合評價法、自然斷點法和最大隸屬度原則等科學方法,對江漢平原鄉村人居環境建設適配性進行評價,并依此提出相應的優化策略。相較客觀評價或主觀評價等單一視角,主客觀適配性研究能夠為平衡鄉村振興戰略方向、優化鄉村人居環境建設路徑提供精準信息。
(2) 江漢平原鄉村人居環境建設適配性具有地域特色,具有與東部沿海地區不盡相同的特征。從鄉村客觀環境供給而言,農戶生活空間可及性已有一定拓展和延伸,但仍以傳統模式為主,政府驅動供給的特征依舊顯著;從農戶主觀需求意愿而言,農戶對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及個體居住條件等滿意度評價較高,在自然環境、經濟運行環境等維度滿意度評價卻較低,農戶主體對人居環境品質需求意志日漸明晰;從適配性視角而言,整體“中—中”適配狀態,表明鄉村人居環境建設的供給力度和方向仍需加強和調整。與之相對應,東部沿海地區具有更高的人居環境建設水平。從人居軟硬環境建設看,基礎設施、衛生環境、居住條件等硬環境改善與社會文化活動等軟環境營造能為東部沿海地區鄉村發展提供直接空間載體、間接整合資源和新型經營主體;從鄉村建設效應來看,人、地、業的居業協同體正快速構建[6]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地域自然生態基底、區域主體功能定位、經濟發展基礎、市場運作機制及相關政策指引與管控等多類要素綜合作用下營造了當代中國鄉村人居環境建設成果的地域分異[36] 。
(3) 人居環境建設適配性可透視人類對鄉村地域系統作用力度和作用效應。從江漢平原鄉村人居環境建設適配性結果中可管窺農戶對居住、就業、消費和休閑迭置而成的鄉村生活空間的利用狀態(作用力度)及農戶對鄉村環境建設的整體需求意愿(作用效應);伴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鄉村人居環境建設供給與農戶環境需求亦將加快更迭,必將強化人居環境建設在鄉村振興及鄉村地域現代化建設中的能動作用。主客觀視角下的鄉村人居環境建設適配性關系鄉村地域系統內諸多要素,在多元外力和多維內力作用下,各因素作用強度與作用方向可能有所變化,進而引致不同鄉村人居環境建設成效,持續跟蹤尋跡、拓展適配性研究亦是后續研究重點。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